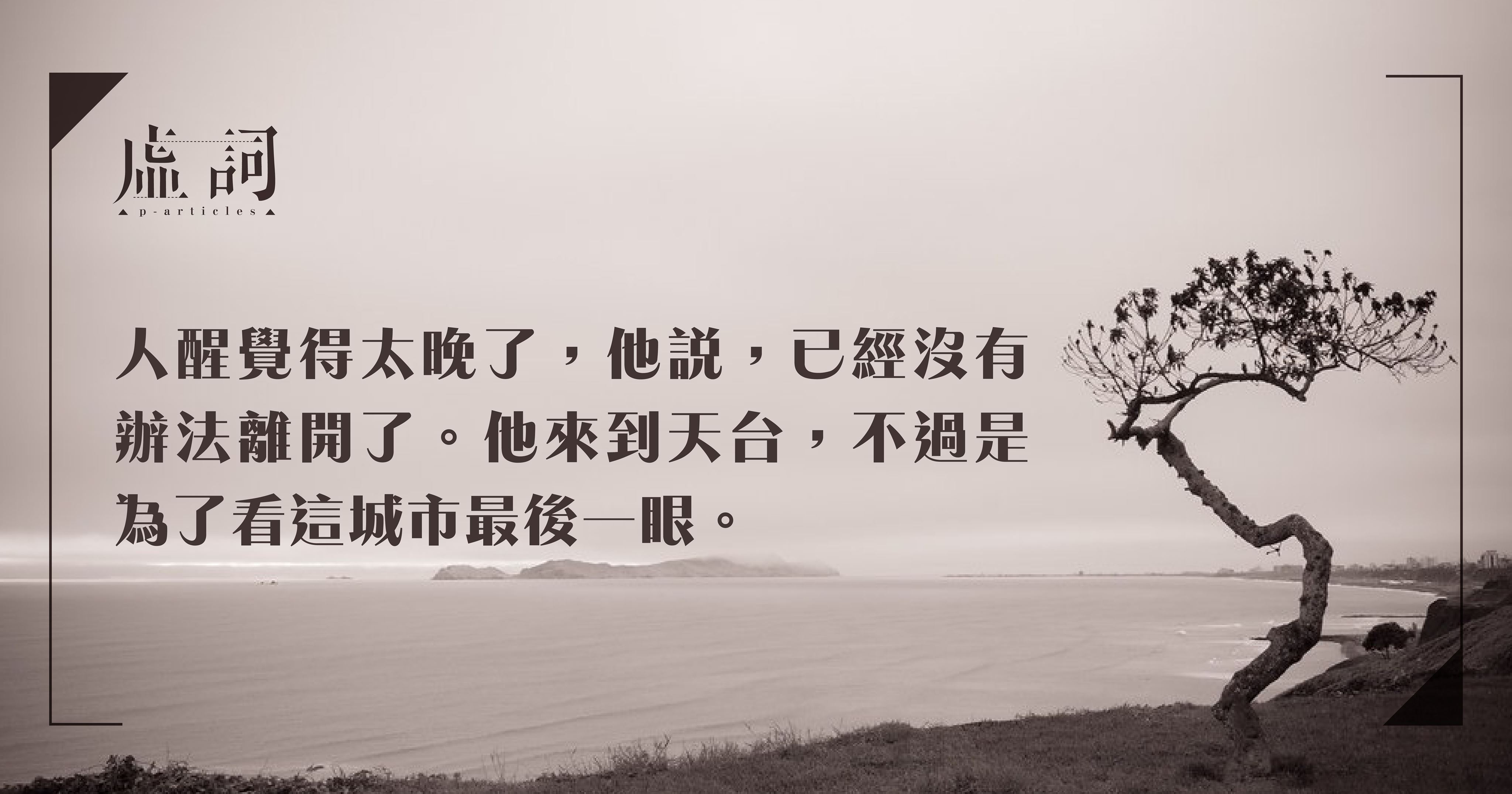【虛詞・疫症迫降】霧中島
她將外賣的殘餘和飯盒扔進後樓梯的垃圾箱後,忽然一種衝動使她沿著樓梯婉蜒而上。走了一層又一層,樓梯一直沒有盡頭,彷彿這棟大廈比她以為的暗中還多上許多層。最後當她按壓大門的手柄,推出去,發現大廈的天台竟通往一個飄浮的島嶼。
§
那天清晨,當大部分的人仍在睡夢之中,一層白霧悄然飄來,把整座山頭吞沒,把維港對岸吞沒,然後是幾百米外的大廈、高速公路、學校……汽車駛進濃霧後從此不知所蹤,遠方的運動場人影疏落,雀鳥不知不覺間在此滅絕,有些人看到飛過的影子,以為是鳥,殊不知那只是在半空飄過的塵埃。白霧自四處湧來,將城市封閉起來,切斷通訊,與外界隔絕,街上行人看不見霧的威脅,依舊成堆橫過馬路,提著紅色膠袋從街市走回家,紅燈前的車龍依舊長長的排列到上一盞紅綠燈。由於霧把城市蓋住了,外面的東西無法進來,裡面的東西也無法出去,因而城裡的聲音集結起來,聒噪地刺著人的耳朵,像是持續不斷的引擎聲、連串的救護車警號、街上的人偶爾吶喊、屋裡鍋盤碰敲的噹啷。人們說,城市一向就這麼嘈吵的啦。但並不是,以前的聲音再吵雜,也不及此刻的分貝。
午後的白霧變得愈發肆無忌憚,它把對面的大廈吞沒一半,發現一個人影打開了陽台的大門,於是它悄悄地、攝手攝腳,往這個方向漫延而來。
§
兩個多月前的她,在辦公室的間板圍城,還在一邊抱怨上頭發下做不完的工作,一邊計劃著復活節假期要跟男友到意大利旅行。忽然誰向疫病的來源地擺個笑臉,於是超市的廁紙和米被搶光了,口罩和消毒藥水頓時缺貨。
然後呢,她再張開眼時,手機傳來「特區政府訊息」,「除豁免類別外,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羣組聚集」。豁免類別是甚麼呢,她問。電視搖控說,誰說自己是就是了罷;串流平台說,跟我聊天,你就整天不用想這條難題了;手機又告訴她,是那群跟槍關係良好的人,當所有人都要與手槍探熱器交流溫度,只有他們一擺手,自稱與手槍老友多年,不用量啦,就被放行了。
背離日常的庸碌而被迫流浪的日子,所有人回歸自己的世界,才發現原來屬於自己的世界是如此局促,與熟悉的陌生人彼此擠狹對視,唯一的出口是可以窺探天氣的窗,然而它往往沾染著霧的殘垣。真正的疾病是揮之不去的倦怠,她試著將之歸咎於過份的資訊或看完一套又一套的電影。但從睜眼開始,日復一日的虛無就開始對她催眠。那麼她想,身心俱疲也許是她的先天疾病。
有時她會看到一個個臉孔浮在眼前,像是網絡教學或會議那一個個細小而並列的視窗。她覺得自己在與虛擬的人交談,彷彿下一秒,他們會一起消失或對她說: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伴裝答話,其實根本不相信他們的存在,於是利用一切沉默的機會,在真實與虛假相疊的世界裡,蜷進不存在的內心──在想像中那個軀體的內部安全地沉睡。
眼皮和思緒就在這樣的混沌中渴望投入睡眠。她感到自己好像一張紙,輕薄而空白,偽裝成一個人的模樣,在屋裡踱步或坐下。
外頭的世界始終被一塊玻璃窗隔絕。她躺在沙發上,渴望有這麼一個無人的荒島,能讓她自在地奔走,回復自由的狀態。
§
她輕輕一跨,就踏上這懸浮的島嶼。島的中央有一座山峰,大半沒入霧中,因此她不能一下子看遍整座島嶼的面貌。可是在島的外圍行走一圈,只需十分鐘。圍在島嶼周遭的,乍看起來是陰雲下的白色海浪,實際上它們就是雲本身,連同白霧時而湧上岸,沖刷島的周圍。
這個島嶼是從甚麼時候起出現在此的?或許它是隨霧而來,或許只是她從沒踏足過天台所以並不知曉。
在這個地方,她聽不見挖土機和風聲競賽的繁囂,看不見那些無視病菌而把口罩半掛在耳上的行人。四下的高樓都消失了,世界變回原初的狀態。偶爾傳來新葉的撩撥或浪潮聲,卻沒有多出的位置讓另一人踏足。有時她透過霧的空隙向下俯瞰,人變成移動的細小黑點,那裡的世界與這個島嶼互不相干。
掙脫家裡四壁、辦公室隔板、隔離病房,她對自己說,那個城啊,太局促太壓抑了,一直用盡手段要把她困起來將她同化。人的存在本不應被羈絆,難得來到這個無人之處,她再也不要回去了。
於是她脫離了城市,獨自住在半空的島上,這裡供給了她進食和生存的一切所需。偶爾有些生活在雲上的過客飛來在島上暫居,她每天的娛樂就是跟他們閒聊,聽他們唱著世界另一邊某座島嶼的謠曲。談得累了,她就躺下來賞新葉,或俯瞰地上的城市。
§
這天島上出現了另一個人。他說他是底下那棟大客的住客。他為她帶來了城市最新的消息:霧的威脅已驟然湧至。人醒覺得太晚了,他說,已經沒有辦法離開了。他來到天台,不過是為了看這城市最後一眼。
她於是往下一看,此時白霧將島嶼吞去了一半,底下的城市卻已全然消失,只剩下高聳在雲端的一小部份峰巒。她的喉嚨突如其來地乾涸,空氣壓住肺部,使她無法呼吸。引頸張大喉嚨使勁吸入氧氣,但空氣供養的氧氣無論如何都不足以供應人的需要。也許由於缺氧,她的情緒開始變得暴躁起來。別人的呼喚、遠方飄渺的稠密聲響緊緊將她擠壓。
你為甚麼要告訴我這些呢,我明明可以甚麼都不知道就逝去,她怪責那個佔據了她一部分島嶼的人。可是他回答,妳以為妳逃離了嗎?人的本質屬於虛空,這是無論怎樣也無法逃避的事實,這座島和妳腳下的城市毫無二致。
她幾乎用跑的走到島嶼的邊緣,張口吶喊卻喊不出來,只傳出沉默而崩潰的咆哮,但沒有人聽到,就算有人聽到也不會理解的。她想變成鳥從這裡跳下去,但她忘記了,底下那座城市是沒有鳥的,霧早將牠們帶去。留下的人,都是在煉獄中掙扎墮落的人。
那我怎麼辦呢,她問,我已醒覺了這事,醒覺了自己不過是處於煉獄深處。她多麼渴望能像以前那麼冷漠不聞,就跟底下城市其餘的人一樣,那她就不會知道霧已飄來,不會感受到肉體將她限制,還有有七情六慾的壓抑。怎麼辦呢。
跳下去吧。那個新來的人突然站在旁邊。妳知道的,要逃離被霧困鎖的城市,就只有放棄肉身的人才能做到。
可是你怎能確定,當我放棄肉身之後,靈魂就能因而離開那層濃霧呢?那人沒有回答,他也不確定。
於是她後退幾步,又回到島嶼上。她在體內嘶吼,嘶吼,幾乎將身軀撕毀成碎塊。
§
她在家裡醒來,想不到自己是怎麼回到這裡的。
印象中她似乎沿後樓梯到了大廈的天台,又似乎在沙發上躺了一整天,用手機用得頭皮發麻。只是當她再次睜眼時,四周忽然變回熟悉的空間。噢,她記得她原本正從窗外看出去,老遠的維多利亞港像大廈多餘的石泥擠成的一小塊畫布,佔染霧的殘垣。
霧的威脅將至。抑或,不是,霧其實一直都在。她以為自己擁有一座島,但真實的她空空如也。那座島──其實她一直踏在島的上頭,只是她忘記罷了。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