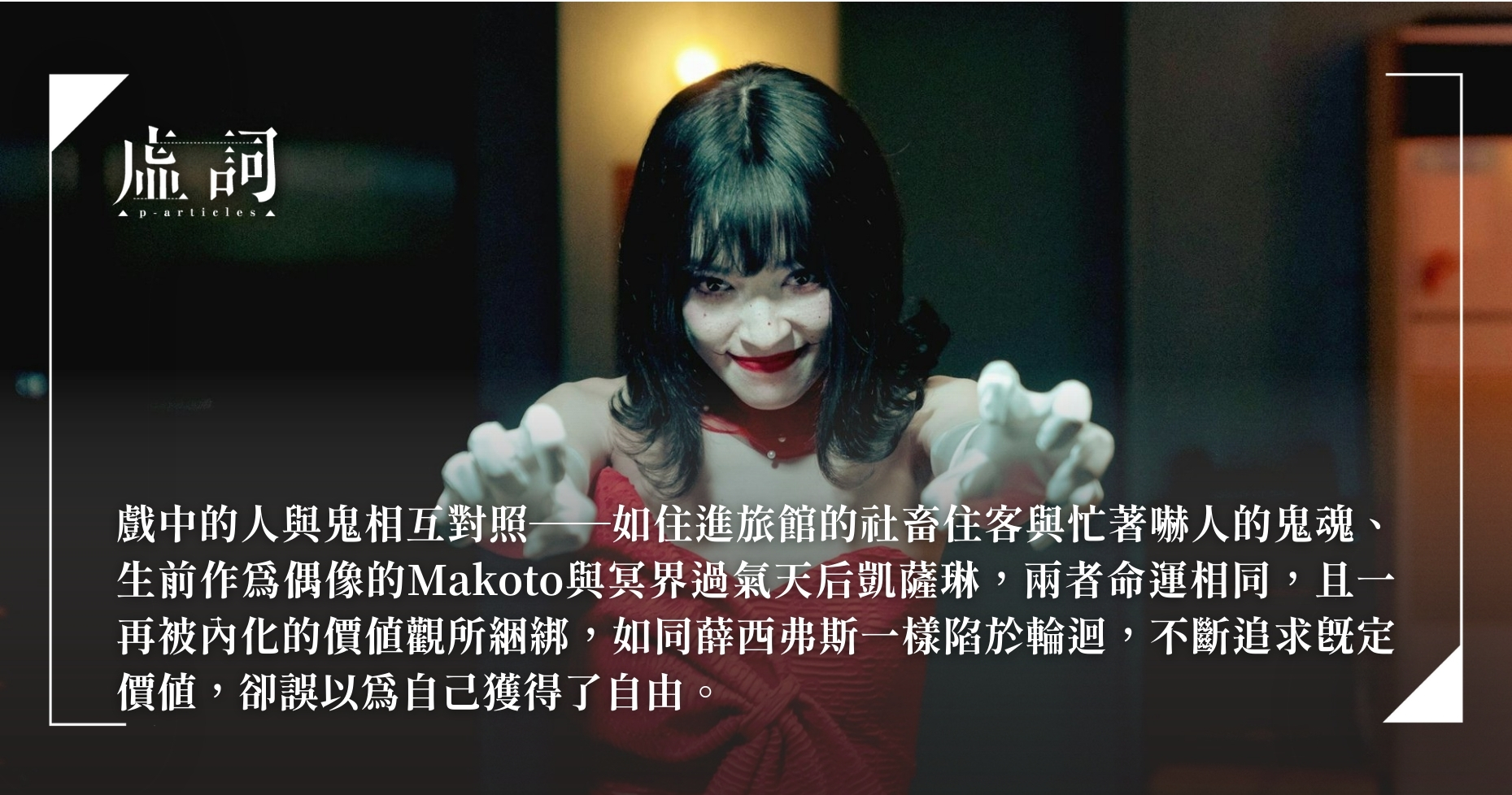《鬼才之道》的宿命輪迴 以躺平尋回生存價值
庸碌一生,以為死後得以喘息,但在徐漢強新作《鬼才之道》(下稱《鬼才》)中,鬼與人同樣疲於奔命,扭盡六壬,折腰跳樓又撞車,只為嚇人取得業績,在世上留痕,不至灰飛煙滅。做鬼比做人還累,一如電影以雙關語定題:「鬼才」之道,意味要被所有人看見才能稱作「有才華」的鬼,然而有些道理,終究要做鬼時才會知道。
《鬼才》裡,徐漢強卸下前作《返校》(2019)的陰森嚴肅,多了一抹短片作品如《請登入線實》(2005)、《匿名遊戲》(2008)中的輕鬆戲謔。電影中,生前一事無成的「同學」(王淨飾),死後同樣躺平,然而有天眼見自己行將消失,不得已加入鬼界經理人Makoto(陳柏霖飾)的團隊,在旺來大飯店中替過氣女鬼凱薩琳(張榕容飾)一起嚇人。在鬼界試圖留名之際,幾名魯蛇鬼亦逐漸尋到自身的價值。
由他者到我們
作為恐怖喜劇,《鬼才》不僅在類型上,就連空間、角色塑造上也同樣「越界」,卻因此將本應恐怖的「鬼」,塑造為命運與人類相似的共同體。
卡羅爾(Noël Carroll)點出,恐怖片與喜劇兩個看似迥然不同的戲種,其實具有共同的特性,就是它們都對現有類別、規範和概念加以挑戰、違反,甚至跨越,因而產生矛盾與混雜性。 而《鬼才》正好就利用這種「越界」進行敘事,打破人與鬼、陽界與陰間的分野,讓兩者平衡互照。
電影借凱薩琳之口提出:「當你被看見了,他們才覺得你有才華。」由此反覆強調的,是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鬼的世界充斥著電影、廣告、脫口秀、新聞與直播,一個個屏幕構成後設的視角,而電影更以「斷訊」形式來呈現魂飛魄散的狀態,對應「屏幕」所蘊含的意義:在一個講求流量的社會,無論人與鬼,不被別人看見就意味失去了存在價值。作為一種打破空間與時間的媒介,屏幕本身就代表著某種程度的「越界」,這種後設和隔了一道隔膜的敘述方式,凸顯出看與被看所造成的權力與壓抑。
卡羅爾提出的恐怖喜劇公式裡,恐怖電影往往由一種「越界」所造成的恐懼和噁心感來形成,當其中的恐懼被刪減,即觀眾不再被電影中的「怪物」所威脅,電影隨即轉化成喜劇,並足以引起笑聲。 《鬼才》去除這種威脅與恐懼的方式,是拉近人與鬼之間的差距:鬼的「生存之道」與人無異,同樣需要透過不斷的工作,展示和證明自身的價值──當觀眾意識到戲中的鬼原來與自身相似,「鬼」原有的威嚇性便不復存在,「恐懼他者(鬼)」漸而過度為人的自嘲,即由「恐懼」(horror)變為「幽默」(humor)。
《鬼才》由類型到敘述上的混雜性,均呼應著它所欲表達的主題,而這種「他者」與「我們」之間界線的打破,在敘述層面上更有另一層意義。韓炳哲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正由傅柯所言的「規訓社會」走向「功績社會」,人原本在外在統治機構的束縛下生活,如今卻在沒有外力逼迫的情況下自我剝削,過度追求績效,壓迫亦由外來轉向內化。
在卡羅爾筆下,恐怖片中「怪物」的可怖性,在於它是一種不符合科學和現實認知的存在, 它所引起的恐懼是外在的,一如規訓社會中壓抑的來源,然而《鬼才》從鬼的角度敘事,使鬼魂不再是「他者」,反而讓觀眾站在鬼的視角,認同它們,而不被這種「怪物」所嚇。此片由恐怖片到喜劇的跨越,也是一種從外至內的過度:真正的恐怖並非外來,而是源於「不被看見」的內在恐懼──無論是追不上時代的凱薩琳和Makoto、害怕消失的同學,或自覺被凱薩琳漠視的潔西卡(姚以緹飾),他們對流量的追逐、擔驚受怕,以至對自身價值的過分追求,正好呼應了功績社會的特徵。戲中的人與鬼相互對照──如住進旅館的社畜住客與忙著嚇人的鬼魂、生前作為偶像的Makoto與冥界過氣天后凱薩琳,兩者命運相同,且一再被內化的價值觀所綑綁,如同薛西弗斯一樣陷於輪迴,不斷追求既定價值,卻誤以為自己獲得了自由。
由輪迴到超脫
從電影空間來看,旺來大飯店由不斷重覆的直線和對稱空間構成,像反覆出現的無盡長廊、封閉的升降機,投映著一種潛意識的心理空間。飯店的殘舊、的士高舞廳格局,一再強調此空間與外在世界格格不入,角色們被困於其中,上演相同的戲碼:爬過同一條走廊,走一樣的流程來嚇人。昏暗和落後的空間背後,隱藏著角色們被壓抑的「本我」──生前得不到回應的感情、籍籍無名的壓力,以噴灑的鮮血、尖叫、扭曲的身體加以宣洩。一切在飯店裡產生的攻擊和恐怖行動,因而都具有一種內在性:嚇人者威嚇別人的同時,亦受制於自身渴求成名的壓力,體現了功績社會中「剝削者,同時是被剝削者」的矛盾。
如此的矛盾性亦見於同學嚇人的方式,她「沒有才華」,只能透過自毀來證明價值──站在馬路上被車撞,或從天台一躍而下,以「自殺」方式嚇人,一再對自己施以暴力,從而回應外在社會加諸在她身上的要求。這種自我束縛,延續自她生前,當其父親一再對她強調:「最重要的就是出人頭地,讓所有人都看見。」一種積極正面性就構成了同學往後的心理壓力。她由此陷入了一個要不斷證明自己、卻總是落空的輪迴,以至地震時被放滿獎杯的櫃子壓死,反映她最終無法承受父母期待所造成的重擔。
《鬼才》還充斥著不同的鏡框、照片框與證書框,隱喻著人與鬼被一個個框架所局限:出於那張父親特意製作並鑲起的「努力獎」證書,同學才會萌生一種要「被看見」的渴望,以滿足父親的期望;凱薩琳被框住的照片,則見證了她的成名時代,同時投射她重拾過往名聲的盼望。直至最後,凱薩琳放下執著,離開房間前把裝有自身照片的相框取走,結束414號房的詛咒,寧願成為別人的替身──框架的捨棄,象徵了其釋懷、不再執於「被看見」。
佛洛伊德曾提出「詭異論(The “Uncanny”)」一說,指出一種未知卻又熟悉的恐懼(unheimlich),乃是源於內心的情結。童年的情緒受壓抑後,潛藏於潛意識之中,直到成長後遇到某種刺激,才以驚悚的形式復發。 《鬼才》中厲鬼通過怨念才能現身,同學被壓抑的「怨念」,便來自父親的過度期望。
電影中,同學曾三次回家,分別代表了她面臨內在壓力的三個階段:最初她在生忌回家,看到家人以一張「努力獎」證書來紀念她。證書一被扔掉,她馬上就要想盡辦法在鬼界留名,以防魂飛魄散,證明那時她的存在,仍受到一張證書所代表的「價值」所囿,未能走出內在束縛;中段,同學在空蕩蕩的家裡想起了父親的期望,才揭露幼時被壓抑的情緒源頭,並讓她重新反思、質疑這個把她「壓死」的成名追求;與之相對,末段同學在忌日時再度回家,發現父母用以紀念她的,不再是證書,而是她跟家人相處的照片。在壓抑─尋找源頭─將之釋放的過程裡,同學最終透過「否定」以往不斷追逐的價值,重新定義生命──她向著還是嬰孩的姪子說:「你這輩子,不用成為特別的孩子,沒關係的」,彷彿跟過去的自己和解,釋放被壓抑的情緖,明白到不需要通過「被看見」才能證明自身。
帶來同學心理轉折的一個重要情節,在於網紅「超鐵齒」觸發了兩大都市傳說,讓凱薩琳、潔西卡和同學被迫化敵為隊友,一起嚇人。徐漢強在訪問中說,「我是不是讓你很失望」是這個世代的共同創傷,因此團隊很早就決定了:「最後這個比賽不能有獲勝的一方,因為如果這樣寫就表示我們在鼓勵這個價值的存在。」最終,正因為攝影機被毀、作為鬼的觀眾們紛紛離席,努力追求的一切變為鏡花水月,同學和凱薩琳才能真正做回自己,逃離流量的綑綁,不再尋求「被看」,並能走出飯店,在山路奔跑,宣洩積壓已久的壓力。
在「金鬼獎」頒獎禮中,努力嚇人的凱薩琳、潔西卡和同學,最終不敵半夜在山中散步、意外被活人看到的紅衣女鬼。電影將偶然性置於努力之上,強調的便是一種「不作為」的否定性力量,提出要從「看與被看」的輪迴中脫離,不再精疲力歇地證明自己,才能真正獲得自由。
參考資料:
1. Carroll, Noël. (1999). Horror and Humor,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7:2 Spring
2. Freud, Sigmund. (2003). The Uncanny.
3. 〈《鬼才之道》導演徐漢強、演員瘦瘦——被看到才有價值嗎?從「陰間」喜劇出發,融入這個時代的共同創傷〉,2024年8月6日,https://news.agentm.tw/297403/
4. 韓炳哲:《倦怠社會》(臺北:大塊文化,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