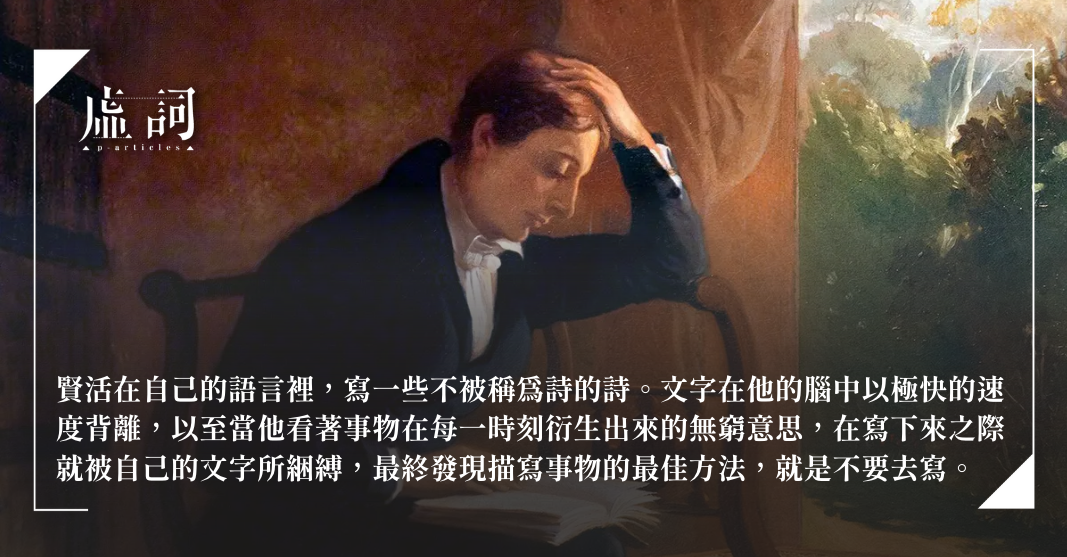【虛詞・給敬而遠詩的人】遺忘的意象
賢寫在詩裡的角色,不知怎地自行活起來了,而且走出了他所能理解的範圍。
賢已步入中年,結婚二十多年,妻子並非初戀,而是他大學畢業後做第一份文員工作時才認識的,他們同年入行,一起工作了一整年,一如別人期望的那樣,不知不覺就走在了一起。
他自覺婚姻尚算美滿,上星期,一家四口出門跟親戚吃晚餐,趕巴士時,四人在初秋的濕潤單車路上奔跑,十二歲的兒子舉起雙手,迎風大嚷,妻子和女兒都笑了。風裡,髮在躁動,笑語徘徊,彷彿正值青春。賢告訴自己,沒有甚麼比現在的生活更值得珍惜。
賢在大學教書,至今兩年,堂上費盡唇舌解釋詩的混沌,為一首詩列出五個解釋,之後又否定這五個解釋的正當性。學生似懂非懂,課後散罷,一兩個年輕學生留了下來,聚在他的講台前要提出問題。
他們之中總有個女學生,每次都穿黑色入肩背心、闊腳牛仔褲,露出肚臍,天氣冷就加件外套。別人的問題都是為了釐清詩的定義,但她從來不問這些,只執迷於一些表面上無關痛癢的字眼,談自己的感受。於是每次女學生一走近,賢都感覺一道懸崖的陰影隨之而來,讓一切語義相繼崩落。
自從大學的教職開展後,賢甚少寫詩。以前他總是創作力旺盛,吃一頓飯,搭一程巴士,一首詩就寫好了,然後寄到各文藝刊物或文獎,作品屢獲賞識,還集結成冊,從事寫作二十多年,出版了好幾本詩集。
寫作對他來說原本毫不費力,他甚至無需推敲每個字辭的意義,文字就為他所用,並與內在無聲的情感和思緒起伏如一。
只是人到中年,文字與人一道走向緘默。蜷在臉上的皺褶,全是文字離別前的吻痕。賢愈來愈難理解筆尖的走向,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含義。那些意象,原是直覺式地浮現的,但當他的寫作能力忽然褪去,而不得已動用語序邏輯上的思考,賢感覺那些文字都不屬於他,而是外於自己的理性工具。
賢再次執筆寫詩,不能不說是出於那個女學生的影響。因為那雙從黑色入肩背心露出的白晳手臂,賢才會寫出詩的第一個意象。詩從手臂開始,逐漸發展出身體的其餘部分,到後來形成了一個人。賢任由筆尖以他無法觸摸的節奏在紙上行走,年輕的靈魂生長,有時是地鐵車廂裡游走的魚,有時是渴望枯萎的植物,有時是高樓之間揮之不去的煙味,只有在小部分的時間裡會成為女人。
在文壇,賢早已成為頗有地位的詩人,近年轉職研究,偶爾有人問起他的創作,都被他以工務繁忙為由把話題轉走,也沒人覺得奇怪。這次暗地裡寫這樣的詩,賢並沒跟任何人提起,也許有部分原因,是出於他對自身文字沒由來的不信任感。
賢將詩作放逐至日常的幽暗之處。詩作寫了幾行,放下,又忽然添上幾句,或幾個字,一如賢放空散步時行走的節奏。到詩作終於完成,賢將它擱置了兩個月再看,竟發現通篇不能成章,就連他也無法明白,兩個月前的自己,怎麼就成了一個與他截然二分的陌生人。
他本著研究者兼經驗詩人的執著,花了兩星期重寫詩作,讓意象連結,語義相和。他讓筆下的女學生與人相愛,把她從動物、植物和氣味的框架釋放出來。
經過改寫後,賢的詩變得平易而直接,即使不諳新詩的妻子都能夠勉強讀懂。後來他把詩作以課堂範例的形式,借故讀給那個女學生聽。讀的時候,女學生抬眸凝視著投射屏幕,身體前傾,雙手擱在桌上並托著腮。課堂完結後,女學生沒有像平日那樣留在講桌前,而是匆匆執拾背包,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賢把詩作放下。到了那些既要批改論文又要寫研究文章的繁忙時刻,賢已將寫詩一事,全然拋到腦後。一個黃昏,賢由大學走回家裡的途中,疲憊看著地上影子在面前散開,一輛單車迎面馳來,賢幾乎就錯過了,那隨單車而掠過的黑色入肩背心。只靠這麼不經意的一瞥,賢一下子就辨出了那件背心──單車上那個穿上它的人,毫無疑問,就是自己在詩裡虛構出來的角色。
事情就是從那個時刻起,出現無法挽回的轉變。
從那天起,黑色入肩背心一再出現於賢的日常生活,就好像熟悉賢每天的行程,而悄然躲在暗角等待。可是黑色入肩背心與他筆下所寫的不一樣,這個年輕的靈魂,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腐朽,不渴望相愛,又時常站在半枯的樹下發怔,新葉長時,就要費力地換氣。
在霧氣瀰漫的日子,黑色入肩背心是一盞燈,在白茫茫的河道上亮起,像一隻眼睛。
黑色入肩背心出現的次數愈多,賢出神的次數也就愈增。有次,賢出門準備回大學教授八半堂,沿河道行走的途中,他低著頭,反覆思考待會要教的題目──有關佛洛伊德學說和夢境在詩作裡的呈現。這時一輪單車把他撞倒,賢昏了過去,醒來時看到醫院天花的白光,開始忘記了怎樣說話。
來醫院探望賢的人眾多,他們都以為賢是因為腦部受創而變成了啞巴,但事實是,賢並非無法說話,只是所有詞彙的既有意思,都在他腦中丟失了意義。
就好像,在他的腦海裡,單車再也不是用兩個輪子推進的代步工具,而代表著一家四口在農田的邊緣向彼此叫嚷,其中一人變成了啞巴;兒子和父親、妻子和丈夫,這些稱呼並非從相對的關係裡獲得定義,而是迷路的生命體,被胡亂湊合時給自己冠上的名字。
賢在兩星期後出院,醫生替他作過多項檢查,包括腦部掃描,沒有發現絲毫異狀。出院後,賢失去了教職,朋友為了安慰他就說,不會說話也不要緊,你還可以寫詩。出院後兩個月,賢又重新執筆,可是他寫下來的詩,全部無人能夠讀懂。
賢活在自己的語言裡,寫一些不被稱為詩的詩。文字在他的腦中以極快的速度背離,以至當他看著事物在每一時刻衍生出來的無窮意思,在寫下來之際就被自己的文字所綑縛,最終發現描寫事物的最佳方法,就是不要去寫。
別人都說,不快樂的人才會寫詩,所以賢覺得,自己彷彿變得快樂了。那天他一如過往飯後的習慣,夜裡獨自沿河道散步,街燈濛濛,風也停滯,遠處亮著一盞不尋常的燈,比整條橋的燈飾都要耀眼。
賢沿著亮得沒有輪廓之物走近,才終於看見了那件黑色入肩背心。一切文字塌陷時的千分之一秒,忽然輪迴般掠過眼前。黑色入肩背心在橋上行走,時而揚手,或轉頭看向某處,彷彿要跟賢傳遞某種訊息。賢沒明白。黑色入肩背心早已不是他一開始寫的黑色入肩背心,而是發展出自己意願和舉動的某種新的生命體。
後來賢回家,躺到床上,正要關掉枱燈準備睡覺時,才忽然意識到,那時候站在橋上的黑色入肩背心,原來正在創作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