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見字__】專訪佘宗明:翻譯《百年孤寂》,無用時代尋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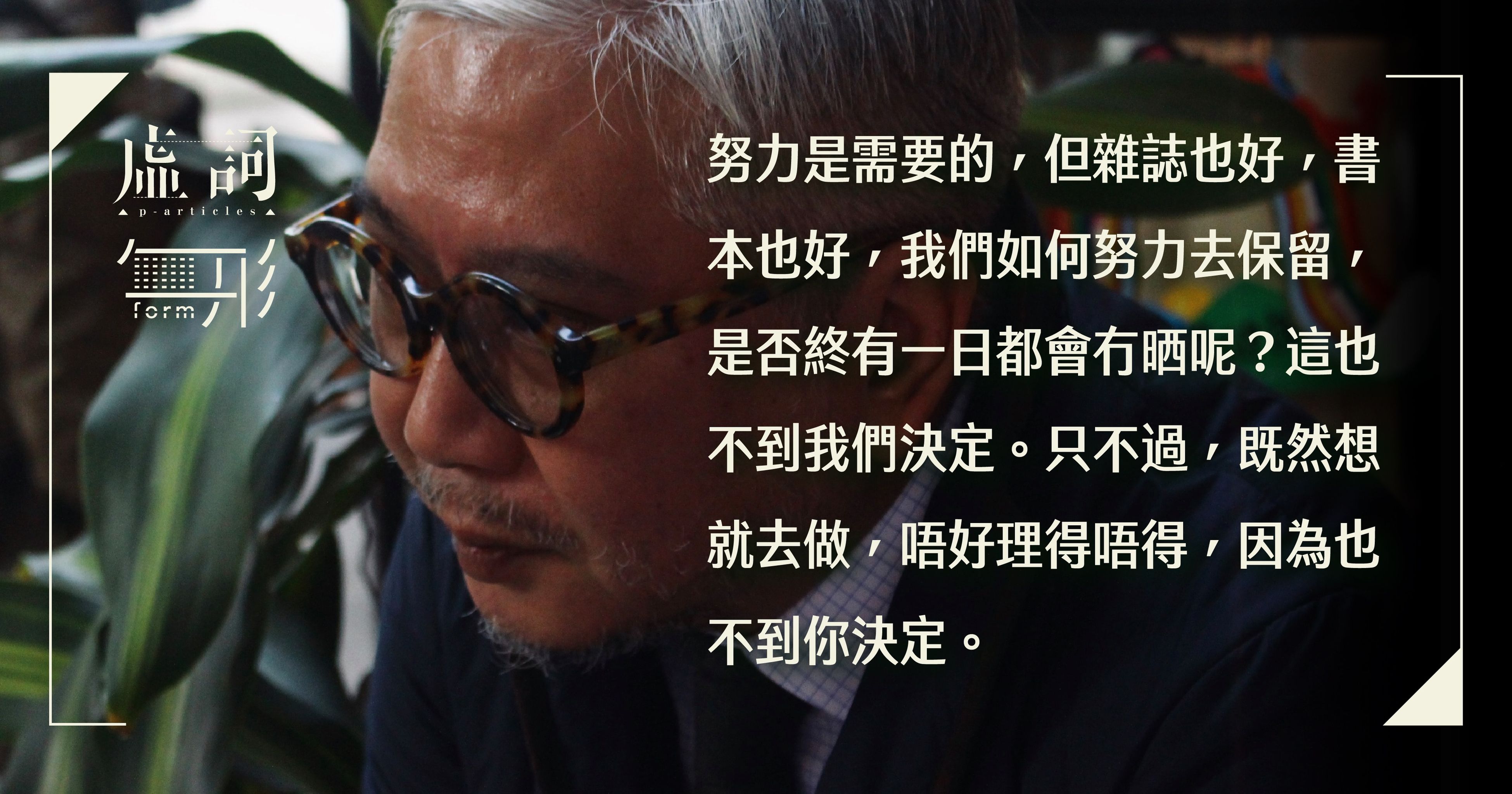
(姚嘉敏攝)
相約佘宗明做訪問,他提議在上環的見山書店進行,其再版散文集《在我還年輕的時候》,以及親自翻譯的中文版《百年孤寂》(孤獨家族),亦只放在這間書店寄賣。寫了專欄超過廿年,這位被尊稱「老爺」的資深傳媒人,去年卻辭掉任職十年的錶書工作,悠閒背後,是一份無法創作的辛苦。自覺過去兩年渾渾噩噩,之所以選擇翻譯《百年孤寂》;自覺虧欠了很多人,所以想做點有用的事;自覺也是攞苦嚟辛,但即使努力未必有成果,佘宗明仍然想用自己喜愛的方式,在這個時代留下一點有用的印記。
「私人習作功課」,為了香港人的
不懂駕車,卻從汽車雜誌開始入行,基於對文字的喜愛,讓佘宗明從名車名錶,寫到電影音樂,一寫將近三十年,行內人都尊稱他為「老爺」。然而,佘宗明卻自言並非甚麼作家,很多時候只是「戚起條筋」,想寫就寫。無論是散文集《聽歌・睇戲・看小說》,抑或半自傳小說《木衛二》,處處可見流行文化對他的深遠影響。「並非懶謙虛,我是個很庸俗的人,只是懶多愁善感。為何我會這樣思考和看待事情,基本上都在流行文化學返嚟。好像我寫影評,也是藉套戲發揮來寫其他東西,因為對我來說,所有藝術對所有人都是啟發,旨在帶你去認識生活和人生哲理。」年前寫成四十萬字的武俠小說《吟留別賦》,也是源於成長時期接觸的流行文化,那種警惡懲奸的俠義精神,讓他尊崇敬佩,也為其文字底蘊打下根基。「我爸爸以前喜歡租看武俠小說和推理小說,在我小學的階段,唯一在家裡看到非功課的東西,就是這些書,我細個會偷來看,也算是自細開始的一個小小訓練。」除此以外,年幼時跟隨婆婆聽粵曲,那些歌詞裡的文字雕琢,亦成為佘宗明後來的創作養分。「屋企細個阿婆會聽粵曲,我也有留意唐滌生,雖然沒有曲譜,但對於文字的那種靚,那種鏗鏘,我並非靠看詩詞歌賦得來,而是透過粵曲聽返嚟,這些對我來說也是滋潤。」
去年翻譯馬奎斯的名著《百年孤寂》(佘宗明將之翻譯成《孤獨家族》),佘宗明在前言開宗明義,著讀者「當成是我的私人習作功課」。的確,這本書並沒向原著購買版權,無法在書店獨立發售,只能依附其散文集,以贈書的方式被廣閱流傳。仍然執意翻譯,其一源自抗爭時期的無力感,讓他難以創作;其二是覺得內容跟香港情況對得上,希望更多讀者能因此翻閱原著。「其實我口味很狹窄,不是看很多書,但《百年孤寂》我卻很喜歡。因為抗爭事件,有段時間好攰,唔知寫乜,我覺得《百》同件事有啲幾啱,就貪得意譯兩段,代替本來要寫的專欄。譯過差不多十分一,都係諗唔到嘢,索性譯埋落去,譯完因為香港的情況,就想更多人去睇本書。」
當坊間的中譯本俯拾皆是,佘宗明的版本選擇以易讀舒服為先,將關係錯綜複雜的人名翻譯盡量精簡,行文間亦夾雜不少廣東話,因為如他所言,這是一本要給香港人閱讀的書籍。「翻譯是要將本來不懂的language,讓人看過理解明白。我在汽車雜誌做過翻譯,到我後期做senior,卻發現其他人的翻譯,點解譯完,譯到我唔知你講乜?我以前讀哲學書也有這種感受,為何中文版比英文版似乎更難?除了那些terminology我看不明白,句子結構好像也不想人看,所以我覺得應該寫容易讓人看得明白的東西。我絕對不算死譯直譯的人,純粹消化句子意思後,再用自己的習慣來寫。」其中一種他很自覺的寫作方式,是運用「三及第」的文體來書寫。「我的文字,由文言到白話到廣東話,三樣都包含其中,這對我來說很自然,出來的效果卻很有趣。像我翻譯《百》,有段講向示威者開槍,我就將它譯成『仆街,佢哋真係會開槍』。有人覺得無啦啦會有廣東話咁有趣,我覺得卻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也是香港這個地方很particular的東西。」
 (姚嘉敏攝)
(姚嘉敏攝)
負疚感:「已經頂唔順呢種消費」
經歷過去兩年,與城內大部分人一樣,佘宗明也有點渾渾噩噩。無法再寫傷春悲秋的文章,翻譯《百年孤寂》,讓佘宗明承受著難以寫作的痛苦同時,至少在過程裡得到滿足,繼而寄望它能發揮一點作用。「這兩年我都戇居居,思想和身體也是。寫作過程很重要的一點,首先是要please到自己,幾辛苦都好,起碼enjoy那個辛苦,現在會再想一層,希望那件事對人有少少用。」冇錢賺又吃力不討好,「唔知為乜」的想法,偶爾還是會在佘宗明的腦海浮現。有用與無用之間的輪迴,彷彿也是香港人過去兩年的掙扎。「最近有人跟我分享宮崎駿的documentary,他也會很苦惱,覺得自己手腳慢過以前,渣過以前好多,但叫佢唔做,仲慘。無論寫唔到嘢也好,香港環境也好,是辛苦的,但如果有日要承認自己江郎才盡,亦非過癮。仍然掙扎著要寫些甚麼,某程度也是攞苦嚟辛,但我鍾意做嘛,咁咪做囉。我不會說以前所寫的完全沒用,但現在我想做點適合這個時代的事。我完成《百》的翻譯,是因為覺得它跟香港好像有點關係,裡面很重要的一點,是一定要記得歷史發生甚麼事,所以我想更多人讀到。」
從錶壇涉足小說,亦曾自立門戶創辦腕錶雜誌,佘宗明卻笑言自己從來不好爭名奪利,只要可以繼續寫作,已足夠讓他感恩。「唔使擔唔使抬,就算有責任或壓力,但無須怕醫死人,無須像律師般,搞錯咗判三年呀,對唔住,這份其實是很輕鬆的工作。衰啲講句,我風花雪月又一日,仲有紅酒飲,有靚車坐,飛又飛得Business,未至於飄飄然,但感恩之餘也enjoy。」真正讓他覺得辛苦的,是香港過去兩年的環境,這種壓抑的感覺,亦令他決定於去年底辭掉十年的錶書工作。「這兩年我覺得辛苦,尤其當我還要寫二千萬一隻錶,唔好話二千萬,就算一百萬一隻錶,甚至五萬一隻錶,我現在也覺得吃力。在香港這個政治和經濟環境,好多人連飯都冇得開,我真係覺得,仲錶乜鬼呀。對我來說,此刻要推銷這些,我不會覺得很舒服。當然,沒有生意也是原因,但各種事情加起來,讓我覺得這種消費有啲頂唔順。」
「點解自己可以比好多人好」,這種guilty feeling,佘宗明說自己從小到大都有這種想法,並由此談及近年看過很喜歡的《海賊王》漫畫。「我為何會buy這個故事,是因為裡面最重要的元素,並非只有警惡懲奸,而是主角幾乎沒為自己出過任何一拳,打親每個大佬都是為其他人,我認為這是很難得的。」這種心態引申下去,亦令佘宗明自覺對周遭很多事物有所虧欠,尤其當下身處於集荒謬於一身的時代。「在我的武俠小說裡,其實也經常提及。到底自己憑乜嘢值得比好多人好?有幾多人上街被打斷手腳?老實說,我連行出去也沒有,但你話我攞嚟煩又好,我真的覺得自己欠了好多人,我連三唔識七都欠,最簡單畀人鬧兩句,我都欠咗佢。」
「好就好,並不代表成功」
亂世當前,時代巨輪卻沒停止轉動,線上線下的媒體生態亦不斷改變,佘宗明在不同雜誌擔任過總編和特邀編輯,以前覺得「變成活字印出來已很開心」,來到今時今日,實體紙本的重要性卻似每況愈下,對此他亦深有體會。「之前見到Facebook有人寫,樂壇已死傳媒已死香港音樂已死電影圈已死,但你只要努力就唔死架喇;我話,死就死,你努力都係死,就看你如何define死,如果跟以前比,其實已經死咗。未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會否其中有個可能性,以後永遠也是轉變期呢?你問我以前嗰種得唔得,如果以前賣一千本書,依家賣一百本都覺得賣呀,咁佢唔會死,但是否可以這樣survive下去,我真的會有疑問。」然而,作為上一代的傳媒人,佘宗明始終認為,翻閱書籍的感覺,無可代替。「我仍然enjoy望著紙上的illustration,仍然enjoy那種juxtaposition,打開本書,有左版右版,前前後後,其實是個sequence,等如望見motion picture有個連貫影像,而非獨立的一格一格菲林。先別說實體非實體,現在的digital無法給我這種感覺。」這些差異,隨著成長環境與經歷的不同,佘宗明覺得新一代未必能夠完全體會。「所謂的history gap,最簡單的例子是,羅馬時代看鬥獸是一家人的娛樂,現在會覺得有冇搞錯,但在那個年代卻很理所當然。同樣地,現在就連擁有的concept,也不再相同。以前細個覺得,要買返嚟才算擁有。好像我在itunes有千幾首歌,少咗首都似掹我肉,但對新一代來說,為何要擁有它們呢?」
有些東西,即使如何努力,或許也無法留住。努力未必就等於唔使死,但佘宗明覺得,如果凡事只看結果才去做,很多東西都可以作罷。「努力是需要的,但雜誌也好,書本也好,我們如何努力去保留,是否終有一日都會冇晒呢?這也不到我們決定。只不過,既然想就去做,唔好理得唔得,因為也不到你決定。」正如名垂千古的孔子,在世時沒人採納其意見,沒官做才回去教書,這個例子,佘宗明經常用作提醒自己。「若你當世問孔子成唔成功,梗係唔撚成功。如果要計所謂的成功,才去determine那件事好或不好,我可以唔使做,好多人都可以唔使做。好就好,並不代表成功,紙本也好,文字也好,甚麼也是,鍾意就鍾意,並不代表那件事會fruitful。」當然,鍾意亦非大哂,佘宗明評錶評車評電影,自然明白萬事萬物,一切盡皆比較的道理。「常說『人比人,比死人』,但其實比較是很重要的。我們的評論是比較,even自己也是個比較。並非強求要做百萬富翁,但起碼知道要提醒自己如何做得更好,不能覺得自己大撚哂。」

(姚嘉敏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