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關於「恐怖」的浮想聯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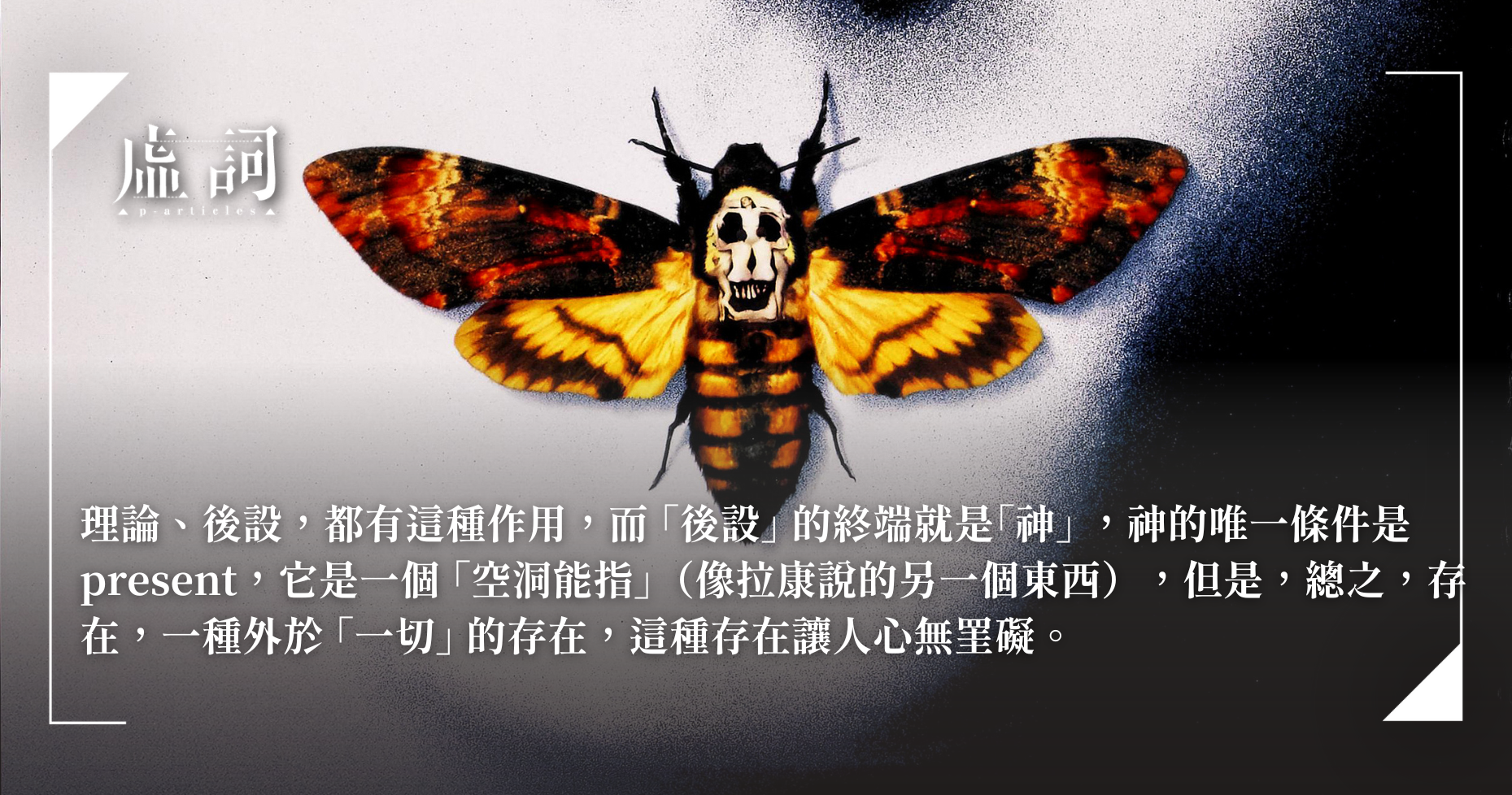
Template (10).png
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說過,人類最古老而強烈的情緒是恐懼;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是對未知的恐懼。
「對未知的恐懼」之中最強烈的恐懼,是對不應恐懼的物事之恐懼。
拉康說焦慮在「缺乏」本身缺乏時發生。
暗夜獨行,街燈照不亮的角落、路的拐角,它們使我害怕,因為我不知道「裡面」藏著些什麼——會有一個不安好心的人嗎?或者,半個?一顆懸浮的頭顱?
這是對未知的恐懼,而我有辦法消解、或者說,緩解它,我只需要硬著頭皮走過去。就像〈爸爸的花兒落了〉裡面說的,無論什麼困難的事,只要硬着頭皮去做,就闖過去了。
闖過去了,恐懼——對於那一個街燈照不亮的角落、或者那一個路的拐角的恐懼,便沒了。
又或者,那裡真的有一個不安好心的人,拿著一根棒球棍,我也會恐懼,但是,那是另一種恐懼,是一種對已知的恐懼,因為「可能性」已經大幅減少——「或者,半個?一顆懸浮的頭顱?」及其所衍生的可能性,已經被「一個不安好心的人,拿著一根棒球棍」及其所衍生的可能性所消滅——我知道他很可能要用棒球棍拿捏我。
毋寧說,那是恐怖的降維(dimensionality reduction)——它由「二階恐怖」降為「一階恐怖」。
又比如,像大學裡有一條小路,小路旁邊有一些儲物的小屋。小屋帶窗。其中一扇,裡面有一個雕像,它的「夜間形態」,我們叫它「吹笛者」。
假如我不識好歹地站在他面前,他對我的威脅是相當有限的——我意思是,在可能性上是相當有限的,他可能會突然動起來、突然抽出一根棒球棍⋯⋯之類。但我知道,在「危險性」(「安全感」的缺乏)之外,我別有恐懼的理由。恐怖谷理論(uncanny valley)是用來解釋這個現象的。所有分析都是為了減低我們的恐懼、焦慮,我們試圖把「未知」的空洞填滿、把「缺乏」的位置修補。觀看恐怖電影時考慮「鏡頭」的存在,有助減輕恐懼,而恐怖電影的「二階任務」,就是讓你記不起「『鏡頭』的存在」。理論、後設,都有這種作用,而「後設」的終端就是「神」,神的唯一條件是present,它是一個「空洞能指」(像拉康說的另一個東西),但是,總之,存在,一種外於「一切」的存在,這種存在讓人心無罣礙。
世上被稱為「正常」的人是「二階人」,被稱為「失常」的人也許是「一階人」、也許是「三階人」,拉康說所指與能指之間失去縫合點(point de capiton)導致「精神病」。那麼,如果反過來,能與「終極能指」縫合,便將會得到絕對的平靜,並且與「零階恐怖」(不恐怖)以上的一切恐懼絕緣——那就是「三階人」。
話說回來,如果我能真切地理解、認同「恐怖谷理論」,即使我仍然恐懼「吹笛者」,他對於我也只能是「一階恐怖」;如果我仍視「吹笛者」為「二階恐怖」,那麼,我對「恐怖谷理論」口口聲聲的認同便只反映了我對擺脫「吹笛者」作為「二階恐怖」的欲望。帕斯卡的賭注(Pascal's Wager)無法使「二階人」升格為「三階人」。
至於所謂「三階恐怖」——如果「一階恐怖」是缺乏「安全感」,「二階恐怖」是缺乏「確定性」,「三階恐怖」便是缺乏「可能性」。
感受到「二階恐怖」時,我至少知道我所缺乏的是什麼;在「三階恐怖」,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是什麼——我覺得該物事是「安全的」、「確定的」,我本應完全信任它——然而,我就是覺得恐怖:我知道它打不過我,知道它像花瓣般美麗、脆弱、溫柔;我知道它不會「突然動起來、突然抽出一根棒球棍」,知道它不會螫我、咬我,不會攻擊我,不會對我怎樣——我不覺得它會怎樣、不知道它會怎樣。
總之,它可怕。
也許是一種循環:我恐懼它,同時恐懼我恐懼它這回事,因為事情本來不應如此——它明明是不應恐懼的物事。
用四種句子類型作為框架的話:「零階恐怖」是一句陳述句(「是這樣的。」我自覺自身安全、環境安定),「一階恐怖」是一句祈使句(「請別這樣。」我對危險性說),「二階恐怖」是一句疑問句(「會怎樣呢?」我向可能性問)——感嘆句是降維的瞬間(「是這樣啊!」),至於「三階恐怖」,我能說些什麼?既然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我能說些什麼?
啊對了,噁心跟恐怖是兩回事,雖然某些物事可以兼而有之。
***
我想起以前讀過的《情動於中》(註),於是重讀了談論恐懼的第五章「毛骨悚然」(頁129-162)——「恐懼不單能在我們無法作出判斷時被引發,它甚至可以在我們判斷自己沒有危險時出現。」(頁146)
我想到休謨的太陽——我們如何證明,明天太陽照樣升起?曾經讓Siri說鬼故事,她的回答很簡短——你看看後面。這是一句指向「可能性」的句子,而我,我自覺自身安全、環境安定,但還是感到有那麼一點恐怖,恐怖從何而來?從「萬一」而來,萬一我後面真的有什麼呢?我「自覺」自身安全、環境安定,卻沒能完全拒絕危險性或/和可能性。
又比如《午夜凶鈴》(リング,1998),山村貞子會爬出電視。我知道這種事不會發生——但我怎麼知道不會呢?我看見了她爬出螢幕裡的螢幕——她可以爬出那個螢幕,誰知道她不可以爬出其它螢幕?這種事情從沒發生過,誰能保證就不能發生呢?電視是假的,這是我的「知識」,但誰能確認(acknowledge)這條「知識」是真的呢?我只不過是,「知道」這種事不會發生,換言之,我對「世界」產生了懷疑。「一階恐怖」和「二階恐怖」發生在不信任經驗、知識的瞬間,恐怖之物事具有「說服力」地向我展現、敘述了潛在的危險性或/和可能性,就在「電視」跟「假的」之間的關係被當下的感知鬆動時,恐怖於焉而生。大海理應是結實的水體,不應該有氣泡、泡沫,但是當某個空洞之物、或者說,具有侵凌、暴虐、強制⋯⋯的象徵意涵之物,掉進海洋、產生泡沫——雜質,便是維納斯的誕生。「為什麼人會主動追求恐懼?」(頁161)說不定是因為,恐怖本是一個掀開、揭示的動作——貝殼打開,皓質呈露,恐怖與美或/和真有著某種鄰近的關係。
註釋:
黃沐恩:《情動於中:生死愛欲的哲學思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