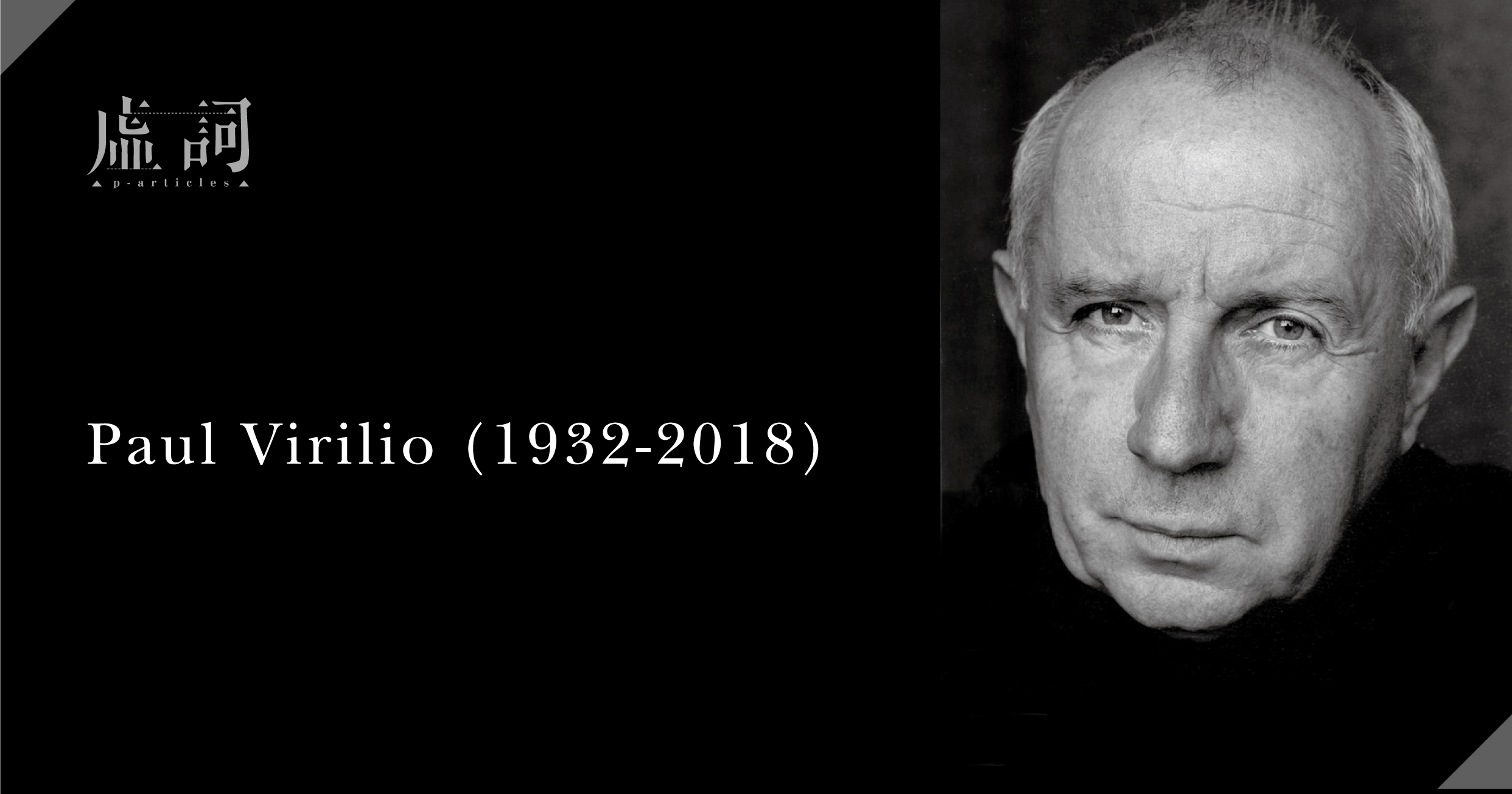維希留的恐懼:時間的獨裁
其他 | by 劉況 | 2018-09-20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維希留(Paul Virilio)影響深遠,其學術研究不斷比對昔日的戰爭和當前時代的相似之處,批判這個不斷加速的時代。
「1940年法國南特(Nantes),有一天早上,我們收到通知德軍在奧爾良(Orléans),中午我們就聽到德國軍車在街上。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我們仍然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記憶,當時的衝突在時間上和士兵佔據的位置之間,無窮延展開去,是一場消耗戰。三十年後,只需幾小時,就足以佔據我們這座城市。」
維希留當年只有八歲,可以想像他有多恐懼,而這份童年經歷成為他終生思考的課題。一方面,兩次世界大戰驚人地提升了軍隊移動的速度,速度伴隨著無邊無際的恐懼。以前恐懼的對象相對明確,預料敵軍來襲,人們趕緊撤離。隨著速度提升,人們根本無從逃避。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運用毒氣,第二次世界大戰空襲成為常態,沒有人覺得有把握逃避空襲,更遑論躲避核彈爆炸。另一方面, 政府和政治家可以利用人民的恐懼來管治。正因為恐懼越來越難以平息,政府可以聲稱為免災難性後果馬上就會到來,目前要立即採取「必要」措施,「假如我們不戰鬥,就會淪陷」充分體現了這種邏輯。集體的恐懼可以被政府利用,直至近年的恐佈襲擊,西方政府同樣會用恐懼來合理化其反恐政策。政府不再以政策來平息恐懼,而是維持人民對恐佈份子的恐懼,極右政黨甚至渲染對外國人或穆斯林的恐懼,來爭取更多支持。加速帶來恐懼,再引發對恐懼的經營,這就是維希留給我們的警惕。
熟悉西方思想史的讀者都知道,維希留並不是第一個指出時代不斷加速的哲學家。早在1930年,曾活在戰壕裡的德國作家榮格爾(Ernst Jünger)就提出「總體動員」(totale Mobilmachung)的概念,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劃時代意義。「總體動員」是指一切事物都捲入動員計劃之中,男人、女人、孩童、自然界、以至一切空間和時間。榮格爾後來更強調整個世界變成了一間間工廠,不斷在加速生產消耗品。一切不屬於工廠的事物,山河大地、動物、人類的休閒和精神文化,都被塞入不斷加速的生產線。可以想像,人類的自由,社會不同價值的辯論,通通在重覆作業和快速輸送的生產中被犧牲,社會變成只有生產和消枆,最純粹的資本主義!在這個脈絡下,維希留的觀點有甚麼不同呢?
維希留認為加速的不是歷史,而是真實(reality)。加速的歷史是指十九世紀以來,輪船火車飛機等交通媒介壓縮了時間和空間,科技進步的速度本身不斷加快。加速的真實則是指人類跟世界的關係逐漸變得單向度,只響往無止境的加速,加速等同進步,注意力落在最新近發生的事物,而忽略了橫向地接觸世界的經驗。在電視的時代,維希留就指出一切事物以倍增的速度同步傳送到世界各地,人類活在情感的同步(synchronisation de l’émotion)和情感觸動的共享主義(communisme des affects)之中,彷佛預見了互聯網和智能電話興起的時代。我在大學裡有很切身的感受。現在學生可以在課堂裡一邊聽老師講課,一邊運用智能電話查證講義上的術語或學術觀點,解決疑難,補充或修正老師的說法,又或者隨興觀看有趣的影片,同時跟同學或課後兼職的同事溝通。加速的真實不是扭曲了或複製了現有的真實,而是製造了多個並行的真實,彼此可以交會或者完全不相干。在複數的真實之中,人們可以同時活在許多個此刻(instant)裡,各種情感同時傳遞過來,雖然相隔千里,但可以受同一種情感所觸動。
這個現象相當複雜,值得研究之處頗多。例如頻密、持續和多樣化的情感觸動,會否改變了觸動的方式或深度?試想當我們在滑Facebook時,這一刻為緬甸羅興亞人的慘況而難過,下一刻為danso(舞蹈學會)「男神」的表演而興奮,再下一刻為學生公民抗命入獄而義憤填膺,這樣下去觸動會否成為慣性而失去不可預期的震撼,由震撼而來的反省和查根究柢,最終變成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批評的交互被動性(interpassivity)?每個人在Facebook上看到複數的真實,多大程度被計算法(algorithm)所編排,變得互不交會,各自封閉在小圈子之中?我們當然不能期望維希留全部回答,他著眼於加速的真實的弊處,當人們總是關注最新近呈現(也是最快傳遞過來)的事物,容易忽略了跟週遭世界的感覺關聯。他給了一個簡單的比喻:「屏幕就像車頭擋風玻璃,面對更高的速度,我們就會失去橫向的感官知覺,形成我們在世界中存在(l’être au monde)的疲弱之處,我們會失去橫向感官的豐盈、輪廓和景觀深度。我們發明了眼鏡來觀看三維空間,但我們卻正在失去橫向的觀察力,失去我們自然而得的立體真實。」在課堂裡,當我們依賴電話或電腦來學習時,相信無可避免會忽略跟同學和教師的互動,聆聽別人的觀點,理解彼此的差異,從而提出回應,讓討論可以繼續下去,引發更多思考,而不是滿足於簡單或「正確」的答案。維希留甚至諷刺地指出,當「屏幕」令人們專注於看新事物時,其實也令人們「失明」。
維希留認為加速的真實把人們囚禁在「此刻」之中,人們只活在每一刻不斷到來的「此刻」,既沒有享受當下的質感,也不願回顧歷史,從歷史中再籌劃未來,因為人們完全陷入加速的真實當中,速度本身成為享受。維希留甚至認為加速的真實以時間駕馭了空間。本來城市的空間有不同的功能,承載各式各樣的活動,但現在媒體和互聯網通訊完全凌駕了空間自行發揮的功能,由加速的時間來統馭空間。這個觀點乍看頗為極端,但我們想一下,中國的高鐵規劃不就是以速度來超越一切空間嗎?當然,空間並沒有消失,物理空間一直如此,但地理空間卻大為改變,不管原本的土地是民居、農地或別的,通通都要讓路予速度。新的中國由加速了的時間構成,不僅高鐵經過的空間裡受影響的居民作不了主,連其他地方生活的人好像也要加入這個規劃,不然就會被視為守舊,甚至阻礙國家進步。高鐵規劃固然來自政府,但政府並不想把人留在固定的空間裡,共同生活、建立傳統和集體決定未來,反而是把空間壓扁成速度可以隨意穿越的地圖。德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羅莎(Hartmut Rosa)受過維希留的啟發,提出獨特的加速理論,最近訪問中國後,就形容中國是「速度的帝國」,維希留則稱之「時間的獨裁」。
維希留強調「時間的獨裁」對民主社會有害而無益:「實時(temps réel)的獨裁跟古典的獨裁之間差別不是十分大,因為它傾向凍結公民的反思能力,催生反射性活動。民主關於團結,而非獨單的經驗,人們需要時間在行動前反思。但是實時和全球的當下要求人們成為電視觀眾,給予反射性反應,這已經屬於受到操控的層次了。」當人們不斷追求更高的速度,有沒有忽略空間為生活帶來的滿足,與他人共同生活的快慰?
維希留認為當代加速的時間沒有脫離戰爭的經驗,「此刻」不能脫離歷史,因而他喜歡引用克利(Paul Klee)的話:「要孤立於其他時刻來界定『此刻』,等如殺掉了它。」也許我們可以說,破壞空間來節省時間,無視生活的經驗以求享受速度,也就等如浪費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