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希留:向「速度利維坦主義」說不的思想家
評論 | by 駱頴佳 | 2018-09-28

維希留擁有衆多的身份:現象學者、科技藝術的批評家、城市規劃者、戰爭史學者、無政府主義者、畫家及大學教授,但多重身份背後,仍貫徹著他對速度與科技文化的關注。© DESPATIN & GOBELI / Opale / Leemage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權能,加上電能」
——列寧
「你並沒有速度,你就是速度!」
——維希留
剛過世的法國思想家维希留(Paul Virilio),生於1932年的法國。他的爸爸是意大利人兼共產主義者,而媽媽則是法國人及天主教徒。他早年在 Ecole des Metiers d'Art接受教育,後來成為玻璃畫的藝術家,與重要畫家馬蒂斯(Henri Matisse)合作。在上世紀50年代,他於索邦大學跟從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研究現象學。巴黎68學運後,在沒有建築的專業訓練下,他被學生委任為建築專業學校(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的建築學教授,直至退休。此外,他也是雜誌 L’Espace Critique 的編輯,而1989年更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帶領下,成為國際哲學學院(L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的課程部主任。在1998年退休後,維希留亦一直關注法國的無家者的住屋問題。儘管維希留擁有衆多的身份:現象學者、科技藝術的批評家、城市規劃者、戰爭史學者、無政府主義者、畫家及大學教授,但多重身份背後,仍貫徹著他對速度與科技文化的關注。
我仍記得閱讀維希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現代熱的事。當時一些介紹後現代理論的書藉〔例如克羅克(Arthur Kroker)的The Possessed Individual:Technology and the French Postmodern〕,總喜愛將維希留與另一法國思想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並排而讀(事實上他們本身也是多年好友及同事)。加上當時,著意推動後現代主義的美國出版社Semiotext(e)大量翻譯兩人的著作,使它們得到英美學界的高度重視。相對於當時的一些所謂後現代思想家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或德希達那種高度哲學性的書寫風格,維希留與布希亞對媒體文化的分析,反有助當時研究後現代文化的學者,能從文化現象來說明後現代社會的特性,特别對一種全面影像化的社會,及由此而生的再現危機(克羅克甚至認為維希留可能是第一個探索虛擬世界的理論家)。加上布希亞與維希留的書寫風格都喜歡將某一現象推到盡(前者以擬象;而後者則以速度),實為當時的後現代討論添上一種離經叛道的色彩。後來索卡(Alan Sokal)那本嘲諷法國後現代思想家故弄玄虛、操弄科學術語來蒙騙世人的著作《知識的騙局》(Intellectual Impostures),也將維希留與一衆當時所謂後學思想家如拉康(Jacques Lacan)、布希亞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並列其中一起接受批判。
當然,到了今天,以後現代這個框架已不可能窮盡兩者的思想,特别是維希留〔事實上他在一次訪問中指出他與後現代主義没有任何關聯(註1),甚至討厭所謂後現代建築,認為它是一場災難,反而柯比意(Le Corbusier)的現代主義建築才合其口味;文學上,他亦鍾情於現代主義的卡夫卡;而哲學上,他亦承認深受梅洛龐蒂、愛恩斯坦等現代型思想家所影響〕。儘管維希留的著作觸及媒體、戰爭、美學、城市空間甚至互聯網的世界,但他念茲在茲的問題是人怎樣在一個不斷生産及強調速度的社會或國家下理解自身及世界。正如他在Open Sky一書指出,速度不只容許我們移動得快,它更令我們在看、聽、認知及想像世界上更加緊凑,但這不一定令我們對世界知得更多,反而限制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所以,他建立的「競速學」(dromology;dromos的希臘語有競賽的意味,所以稱之為「競速」較「速度」適合) ,一種有關速度的系統性知識,某程度是針對一個崇尚「即時性」(immediacy)的文化大環境來理解速度,而不只是以個别的物或人的動速來理解速度。
當然,習慣歌頌速度的人,特別是香港人,我們很難批判地看到速度帶來的問題,甚至是當中的隱性暴力,而維希留给我們的貢獻便是揭示速度拜物教(speed fetishism),又或者一種所有主權國家追求的速度利維坦主義(speed-Leviathanism),怎樣對我們的城市、美學甚至身體帶來改變與衝擊。容許我大膽作一個比喻,維希留有點像印象派畫家莫內(Claude Monet;事實上維希留本身也是一位彩色玻璃畫家),兩者都精於「捕風捉影」,莫內將看不見的風影速度以色彩捕捉下來,而維希留則將社會速度,以理論及概念捕捉下來,所以稱呼他為「捕風捉影」的理論家實不為過。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與維希留。
空間:速度裡的變奏
維希留指出,速度的科技/機器(speed machine)决定了社會空間的形態,令空間變得多變與不定。當然,在法國學界裡,將社會空間視作一種生成及變動的空間不是新鮮事物。梅洛龐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或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都不只視空間為一個物理空間,而是不確定的、結連於主體的身體及想像的變易空間,甚至一種詩化的空間。但維希留認為,速度一直影響我們對空間的認知,但我們卻鮮有注意空間的速度維度,例如人在快速與慢行的車上看風影往往有不同的效果,又或者資訊速度化的世界,令我們對世界帶來短暫與片面的了解。維希留甚至大膽在Lost Dimension 一書指出,速度的加速(acceleration)及減速(deceleration)是空間的唯一向度,即空間本身就是一種速度空間(a speed-space),一種競速空間(a dromospheric space),所以單以容量、密度或伸延來理解空間並不能全面把握今日社會空間的特性。
對維希留而言,在競速社會,我們再難以找到一種猶如透視法背後的中心點看世界。正如我坐着一架火車看風景,我只會看到散亂的光與景,又或者窗外的風景猶如被擺動著的光與影所分解,再加上我的身體在火車上擺動,或看著手機跟遠方的好友作視像對話,或偷望隣邊小孩在手機上跟别國的小孩打機,所有的不同類型(實在與虛擬)的景像及空間都在這刻串連起來,令空間再非同質而是異質,是意外非實在(註2)。又或者高速的互聯網世界,在打破地域、空間及時間的限制及區隔之餘,更以光速輸送到閣下的手機裏,將全世界的影像統一成單一的實況時間(the real time)。所以維希留想指出,速度不只是一種移動的速度,不只是現象,也是一種「接連」(mediation),在同一時間將人與不同時間及空間的人事物串流起來,構成一種多中心多邊的空間世界。這裡速度已不再是手段,而是大環境(milieu)。
維希留指出,今天人類的處境一如坐在快車上(速度空間)的旅人,最終引致一種世界的荒漠化(dessertification),對世界的認知變得單向,對世界的再現變得不確定,更構成一種存在的威脅。他甚至指出,人的身體日漸被各樣資訊空洞化,只活在技術/機械的時間,而非生物/人的時間,勾消了人的靈魂與意志。難怪文化理論家費斯通(Mark Featherstone) 稱,維希留的理論,帶有基督宗教的終末論傾向,甚至一種帶有彌賽亞向度的政治神學(註3),而作為天主教徒的維希留究竟有否將自己的神學滲進自身的理論之中,則是另一有待思考的課題(當然,他自己承認他不擅長以文字討論信仰)。
這令我想到今天我們透過高速的電子媒體了解世界,訊息接收又以快及多為先,但能真正讓我們停下来想一想的時間又有多少?信息的真假甚至可能不再重要,因多真的信息在競速文化的影響下也會「失真」,因大家根本沒有耐性求真;而速度在各種維希留所言的速度機器(電視或手機)的操作下,動的權力(the moving power)比知的權力(knowing-power)更加重要,所以我們都在捕風,在捉影,留下的只有世界的片面及一絲絲我知得比你快的溝通快感(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維希留又認為,在競速社會,人往往只服從一種所謂「近速律」(law of proximity),即愈省力愈快的方法就愈多人使用,所以電子媒體在這種法則下必然勝過其它傳統的資訊媒體,例如我們只愛上網看新聞而不再讀報。在競速空間下,知得比人快比人多,可能比知得深及準更加重要,這不就是今日的媒體生態?所以,維希留建議,我們唯有重新學習减速,甚至停頓,才能給身體知覺新的可能用以重新認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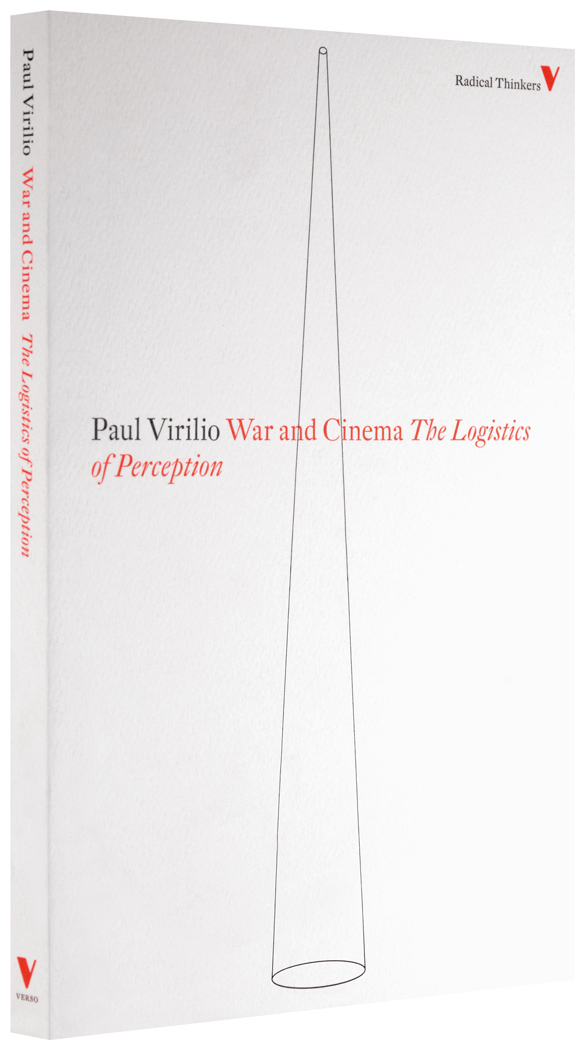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維希留著,Patrick Camiller譯
影像: 光影裡的遺忘
作為畫家的維希留,對圖像的形式變化相當敏感,特別是電影影像對圖像認知帶來的改變。電影跟圖畫及雕刻不同,畫是静態的影像,背後有穩定的物質框架,如展架固定展品供我們欣賞,令指涉的客體相對隱定,容易讓人記住影像的內容。但電影建構出來的影像是光,是觀感是印象。由於生產影象的是不斷流動的放映機器,它會不斷生產流動及瞬間的光影與時間,故此,電影所指涉的客體會不斷在顯隱中流動,在一種在場與不在場的影像運動裡對世界来一種捕風捉影的呈現,所以速度化影像不容易讓人記憶,反而促進遺忘。
維希留指出由圖畫到電影的過渡帶來了一種由「表像的美學」(aesthetics of appearance)到「去表像的美學」(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有論者以「失踪」翻譯 “disappearance”,但維希留不是指影像失去了,反而是指電影影像本身極不穩定(註4),被指涉的人事物不再是穩定的客體,而是或順序或倒序、或此時或彼時的流動時間。最後,電影呈現出來的往往是一閃即逝,不斷呈現又不斷被洗刷掉的影像,一種表像的速現速逝的影像經驗,而影像裡的空間與伸延最终受時間所操控以致消解,換來一種維希留所謂的「時態的密度」(intensity of temporality)。
當年本地學者亞巴斯(Ackbar Abbas)認為香港是一個“space of disappearance”,也是受維希留的啟發。但他不是指香港失踪了,而是指再現香港的影像外皮,會因著電影裡的時間流動而不斷被洗刷及消解,影像裡的香港速生速滅,過眼雲煙,而任何以為可以再現香港整體經驗的影像嘗試都是一種挫折。
當然,維希留的關注不只是美學性,還有政治性。在War and Cinema一書中,他就指出,當我們習慣了以電影來理解戰爭後,最終電影不會再是戰爭的呈現,而是將戰爭變為電影,即一切的暴力若不夠電影感就不再是暴力的行徑,武器也不再是破壞性的工具,而是一種打動人的視覺(perception)。這令我想起早陣子北韓不斷透過展示自己的核武器以至播放核暴畫面來脅逼美國及南韓,最終沒有動刀動槍就能迫美國及南韓就範,不能不說金正恩深明戰爭影像化的威力。維希留也說過,核武的危險不是來自它的爆破力,而是來自它對人類思想的威脅。當然,在911,這維希留稱之為一種「後人文主義敵托邦」(post-humanist dystopia)的恐襲,恐怖分子在電視面前,根本就是想製造了一次等同荷理活電影〔根本就是電影搏擊會(Fight Club)末段炸毀世貿的一次重演〕的景觀性襲擊。難怪維希留指出,「戰爭不可能脫離魔術性的景觀,因為製造這類景觀正是戰爭的目的的所在。」(註6)
政治:「速度利維坦主義」的實現
維希留對政治的理解是從空間與競速學的角度思考。若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指一種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那維希留則視歴史發展為一種軍事革命的發展史。當中他特別看重,各年代不同政體如何先以城市作為軍事空間(military space)來建立政體的正當性,而日後對城市的管治就離不開各種以速度為先的空間治理術。
維希留幾本早期的著作,例如Popular Defense and Ecological Struggles、Bunker Archeology、The Insecurity of Territory與Speed and Politics都嘗試點出國家及政體的各種控制、生產及保衛軍事空間的技術(特別有關戰爭),從中探索早期城邦及城市空間的形成。他深信,政治的開首必然是人工,而非自然構成的軍事空間(城邦、共同體或民族國家),這空間往往先於其它政治空間而建立。因以戰取地,這種「解除邊界」(deterritorilalization)的軍事行動,往往是一個國家建立的前題。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競速的運作,以最快的速度(包括發明各種快而準的武器或偵察器)來征服敵人或入侵他國,來爭取勝利。維希留甚至指出,中國的《孫子兵法》也一早指出,戰爭的本質就是速戰,而時間就是關鍵。所以,一個成功政體必然是一個精於提昇戰爭速度的政體,由早期透過運輸的革命,到今天透過快速的電子資訊整理,都是一場軍事速度化的發展史,也是一次將戰場從實體空間邁向虛擬空間的易變過程,甚至後者日益將前者消解。當然,人類要承擔的代價就是因著各種類型戰爭而生的,事前測不到的各種「意外」(accidents),例如细菌戰與地面戰對人類帶來的禍害便相當不同 (我甚至認為現在要加上貿易戰)。
維希留認為,未來的世界格局,也不再以資產與權力區分所謂強國與弱國,而是以速度作决定,既得利益者就是那些擁有速度技術的人,反之亦然。所以他說,我們沒有民主(democracy)只有競速政權(dromocracy);沒有策略(strategy) ,只有競速學(dromology)。(註7)難怪當年列寧说,「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權能,加上電能(electricity)」,政體對所有能加速國家力量的能量的迷戀可見一斑。
在Speed and Politics中,維希留又指出,競速政體就是以征服大地作為它的大藍圖。這或可理解「一帶一路」對今天作為一個競速政體的中國是何等重要,因這種「速度利維坦主義」,不只是土地的開拓與擴張,還是一場與其它競速政體(例如美國或印度)作抗衡的速度戰,務求以最快的時間與其他國家,建立更大的聯盟來對抗敵對的力量。此外,除了全球化的地緣政治講求速度,今天的中國亦以高科技來加速治理國民的速度,例如以高速的手法清除低端人口,或以電子信用系統去建立市民的資料庫作更快速的規管,這些都為維希留的競速學找到更多的事實基礎。
作為天主教徒的維希留,自稱是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者〔這與同代的法國新教科技社會學家以綠(Jacques Ellul)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一致〕,對國家,特別現代的主權國家,帶有一種反國家主義的立場。維希留深信這種以速度征服空間的政體最終並不會以人為其主要的關懷,因征服空間的速度欲望,自必然對更多的人進行征服,甚至不惜以非人化的方式進行。這所以競速政體最終必然使自己發展為更高科技的政體,一隻追求速度的利維坦,務求令征服與控制變得更多元化及速度化,甚至慢慢轉向由物質空間到虛擬空間的操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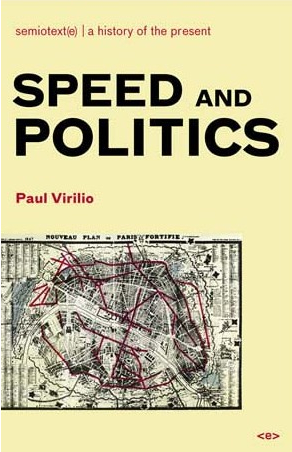
Speed and Politics
維希留著
結語:回到身體與空間的城邦政治
維希留始終是一個古典的人文主義者,而不是甚麽後現代或超現代主義者。他理想中的政治是古典的城邦政治,當中人能夠在實在的空間,與其他真實的肉身彼此討論及議政。他指出,民主就是分享,不是分享金錢,而是分享决定(decision)。但在競速政體下,我們只容許在很短及快的時間下作决定,根本沒有反思的時間及空間,且决策往往由電腦數據或資訊所决定,例如今天的金融政策很多時是由電腦大數據所决定,政治人的位置日漸被邊緣化,又或只充斥著無腦的技術官僚(今日香港的實况)。
維希留又擔心,當實體空間的政治慢慢成為非空間(non-place)的虛擬競速政治,城邦式的議政便愈來愈難。當然你可與遠方的一個美國人討論政治,但與自己社區及城市的市民反而少了面對面的交流,因前者只是虛擬的「速度-空間」而非實體的「時間-空間」,而唯有後者才能促進深入的政治討論。維希留指出,這最終帶來一種「城市的去實現化」(derealization of the city)的問題,及衍生「非權利」(non-right)的危機,因城市的失去也意味著權利的失去。
維希留說的或許不合時宜,甚至有點保守,但當我們活在速度利維坦主義的大氣候下,當一切都變得輕飄飄的時候下,他對當代社會的敏銳剖析,反而讓我們慢下來,檢視我們一直被速度利維坦規訓得習以為常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從而重尋一種實在的、緩慢的身體與空間政治。正如維希留引用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說法,「即時性就是欺騙」,或者這正是當下競速社會我們須要小心謹慎的地方。
【註腳】
註1:“From Modernism to Hypermodernism and Beyond: Interview with John Armitage” in John Armitage (ed.), Virilio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Sage, 2001), p. 15.
註2:Paul Virilio, Lost Dimensi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 35.
註3:Mark Featherstone, “Virilio’s Apocalypticism,” C theory.net, 2010, p. 2.
註4:Paul Virilio, Lost Dimension, pp. 25-6.
註5:Paul Virilio, Speed & Politic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6), p. 150.
註6:保羅.維利里奧,《戰爭與電影:知覺的後勤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2-3。
註7:Paul Virilio, Speed & Politics, p. 46.
註8: Paul Virilio, Negative Horizon, (London: Continuum, 2017), p.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