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快感.革命構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
報導 | by 致寧 | 2018-09-27

八月上旬舉行的香港馬克思節,六號一晚請來駱頴佳在序言書室主講「情感政治與左翼」,趁著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當下,探討左翼如何看待社會中的情感經驗。
「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情感政治的問題,也是駱頴佳博士思索已久的課題,「為何要談情感?第一件事,在西方學術界有所謂『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論述,還有『情動』(affect)這個諸多討論的概念。 」西方經已蔚為顯學的情感研究,何以作為香港社運政治路向的借鏡?
八月上旬舉行的香港馬克思節,六號一晚請來駱頴佳在序言書室主講「情感政治與左翼」,趁著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當下,探討左翼如何看待社會中的情感經驗。駱頴佳早年讀文化研究,後來鑽研法國哲學,尤其對身體、情感等題目感興趣,他笑言:「談《資本論》的話,相信很多人比我講得更好。我決定講一直思考中的情感政治問題,交代一些『左抄右抄』的思想。」於是一整夜駱頴佳旁徵博引左翼理論,開出一張琳琅滿目的情感研究書單,又以前年《100毛》的分獎典禮爭議切入,反覆辯證閱讀情感的壓迫性與顛覆性。
一、當代思潮中的情感轉向
「誰能操控群眾情感,誰便可掌控政治運動。」這是近年很多批判理論家注意到的問題。現今政府、傳媒與不同陣營的政治團體,不需要太理論化地解釋政策背後的因由(rationale),只需引起群眾的恐懼心理。譬如說,我們不難觀察到,特朗普上台和歐洲右翼崛起所帶動的民粹政治,對於難民、新移民與穆斯林等他者的排斥,其運作往往牽涉到恐懼的情緒。更不用說,香港人每當遇上政治爭拗,隨時鬧到七情上面。駱頴佳一句點出情感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每一日都受到很多情感牽動,但少有意識到情感如何控制我們作出政治上的抉擇。」
這個西方批判理論中的情感/情動轉向,可以回溯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哲學脈絡。斯賓諾沙說的情動(affect),是一種影響別人情感,同時反過來被人影響的能力(a capacity 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駱頴佳解釋說,情動是一種改變人們行為的隱性逼力。譬如他在序言書室開講,聽眾們的反應如搖頭、打瞌睡,都會隱若地影響到他的情感狀態。如此,人們的行為不單只受制於思想,更會被某個空間內的情感流動改變。
去到當代的政治哲學家中,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提出過重要的情感政治論述。駱頴佳舉出其中兩本:《政治的情感》(Political Emotions)與《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納思邦認為,情感背後往往牽連某種價值判斷。當我們回應各種事情變得日益情緒化,無論是對他者的恐懼、厭惡抑或愛惜,值得深思的是情感背後附帶甚麽價值判斷。我們討厭哪些族群?見到哪些人會感到憤怒?納思邦說,這些問題盡皆反映你的價值判斷。
此外,駱頴佳還特別推薦自己常用的教科書,納思邦論教育的著作:《培育人文: 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其中一個洞見是,如何培育學生的情感與公民價值建構有莫大的關係。簡單地說,假如人們習慣用討厭的眼光看所有非我族類,我們無法真正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最終,培育情感就是培育我們需要的人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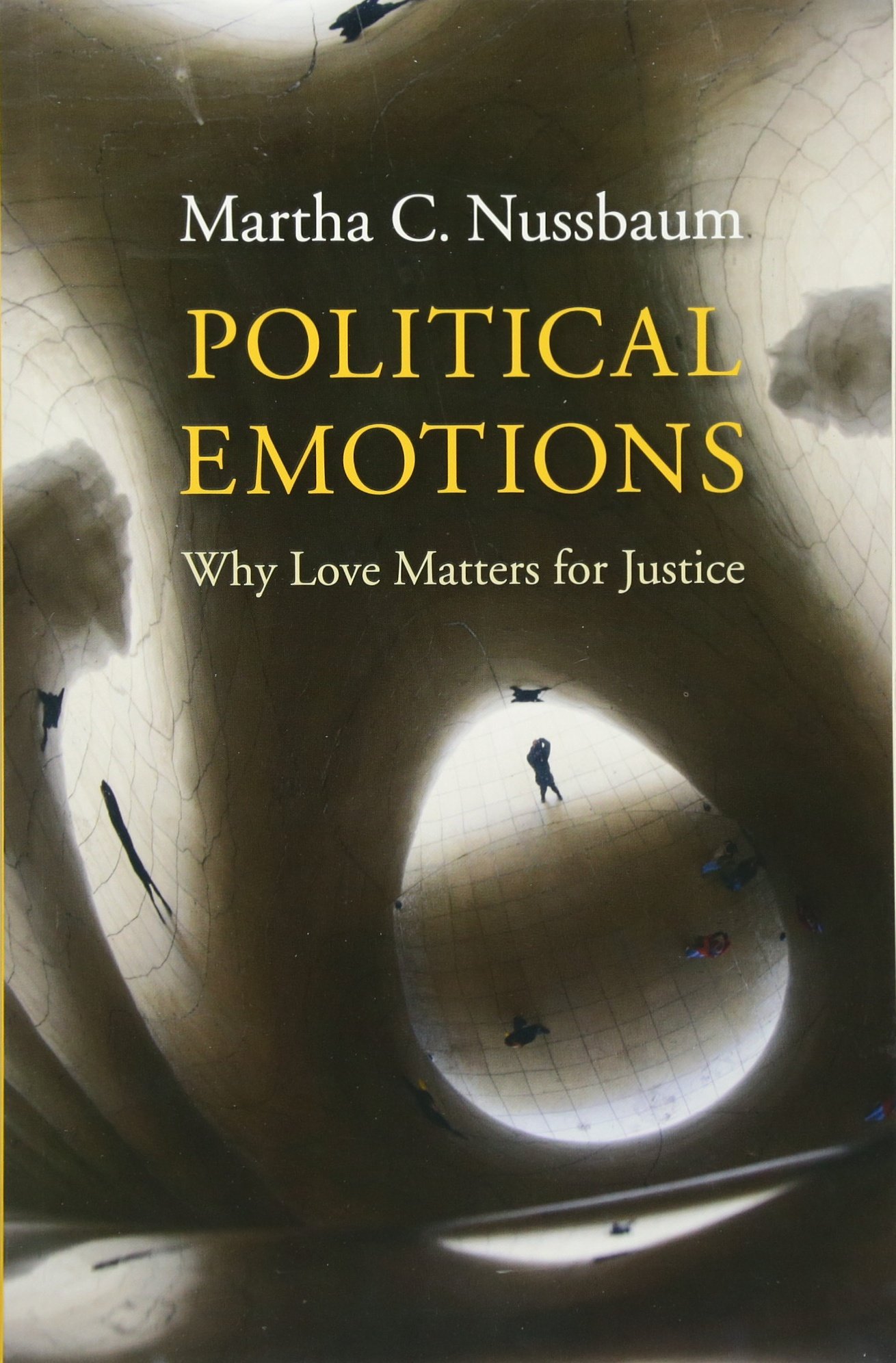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納思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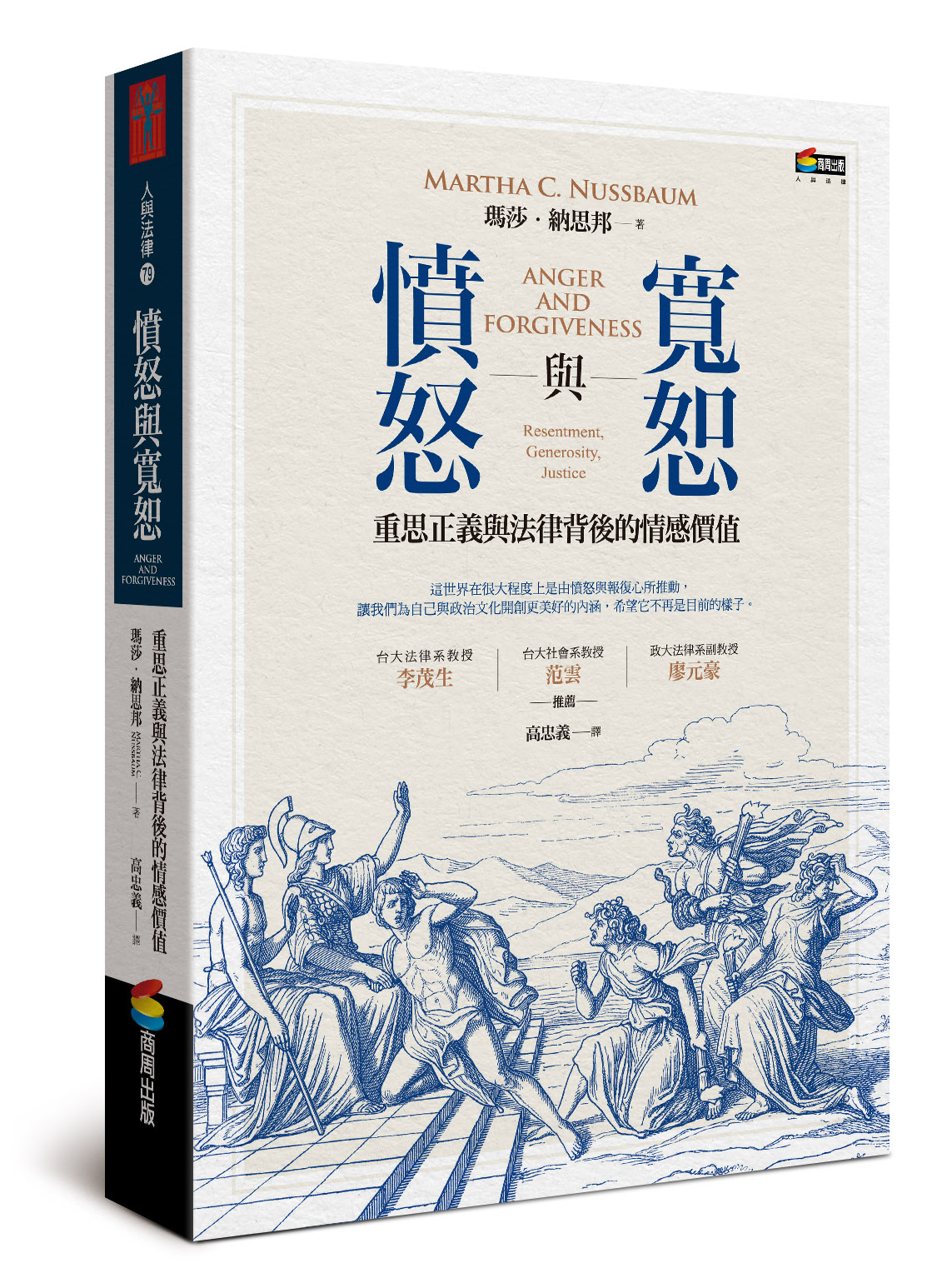
《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
納思邦著,高忠義譯
二、問馬克思,情感為何物
對於左翼宗師馬克思而言,情感又是甚麼呢?駱頴佳說,研究這個問題會發現學術界有不同觀點,對情感在馬克思的理論位置存有分歧。美國社會學家Stjepan Meštrović在其著作《後情感社會》(Postemotional Society)指出,馬克思主義運用的修辭偏重認知(cognition)遠多於情感。通常馬克思主義者提到情感,都是屬於商品拜物教、異化和宗教的非理性等脈絡。由此推論,人性中的情感面向是妨礙革命的,重要的是提高群眾對階級意識的認知。
另一端的詮釋是把情感視作馬克思人性觀的內在核心,這角度可以在青年馬克思著作中得到印證。譬如社會學教授L. Frank Wehyer就發表過一篇學術期刊論文,Re-Reading Sociology via the Emotions: Karl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Estrangement,當中引述到馬克思寫於26歲的代表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青年馬克思說,「人類是感官的存有(sensuous being),因而是受苦的存有(suffering being)。」換言之,情感是我們感知痛苦的條件,若不同意這一點,便無法推斷出我們能感受工人被剝削之痛苦。
馬克思更認為,情感乃是人與世界建立整全關係的條件,駱頴佳闡釋道,「大家知道馬克思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知,必須先由情動身體(affective body)的物質性出發。」客觀地説,馬克思從未建構一套有系統的情感理論,我們閱讀《經濟學哲學手稿》,也只能引述一些相關的段落。但是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情感與身體這些物質元素可謂構成勞動主體的重要條件。
即使談到勞動異化的問題,背後也基於一個假設:人需要自主地選擇熱愛的工作,隨本性發揮自己的情感才會感到自由。駱頴佳興奮地讀出《經濟學哲學手稿》一番話,說很適合放在臉書分享:「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相信讀者諸君都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偷懶某程度上可能是為了「向異化說不」,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不想出賣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已。這不是說笑的,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便寫過一本著作叫《懶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azy),高舉懶惰和創作力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泉源。
假如讀者對異化問題感興趣,駱頴佳再推薦楊照的一本入門書《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資本主義一日未崩潰,馬克思的批判便永不過時,依舊值得細聽。近十年來,不少左翼學者從情動理論的角度重新閱讀馬克思,由此打開我們對情緒和異化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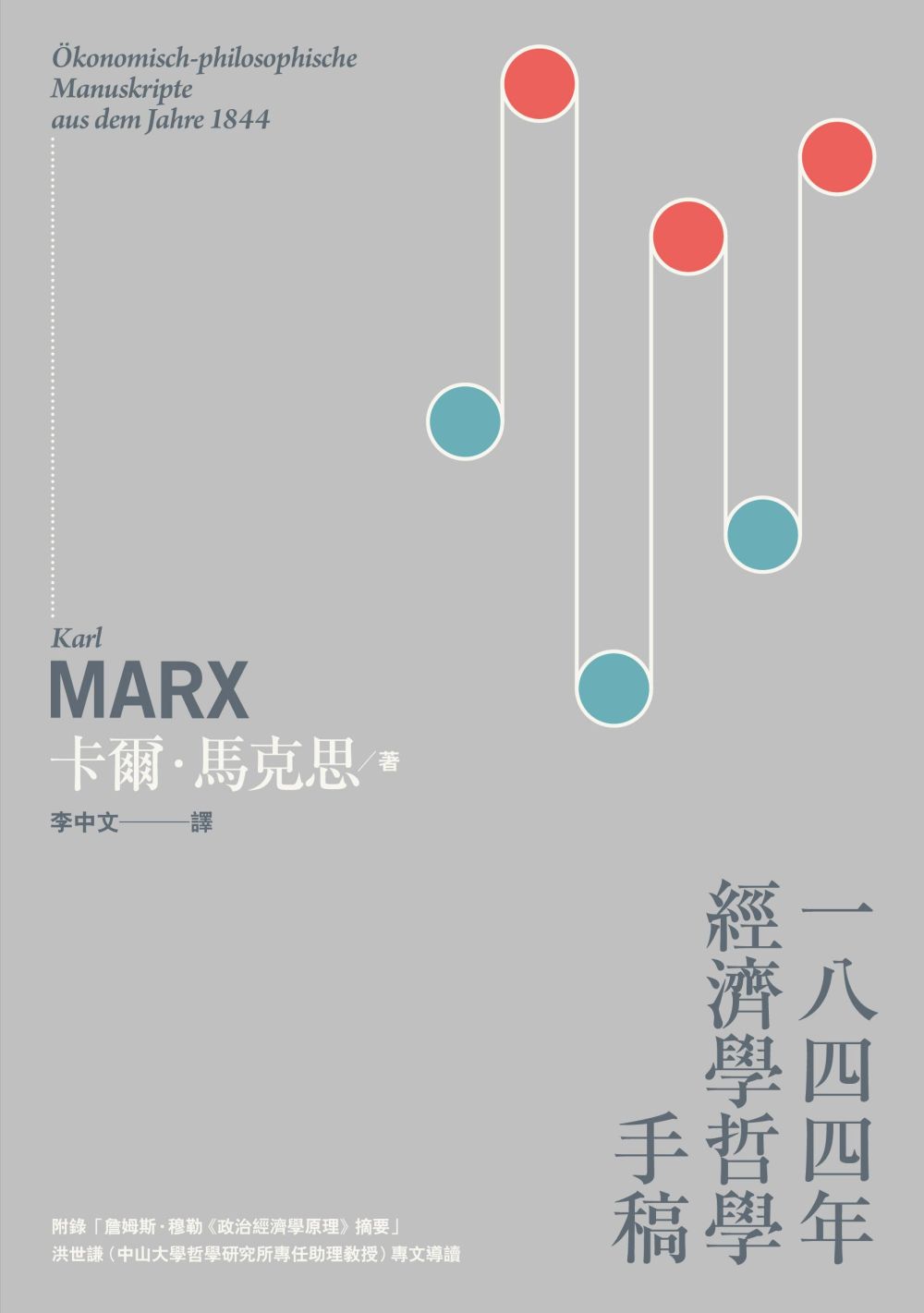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馬克思著,李中文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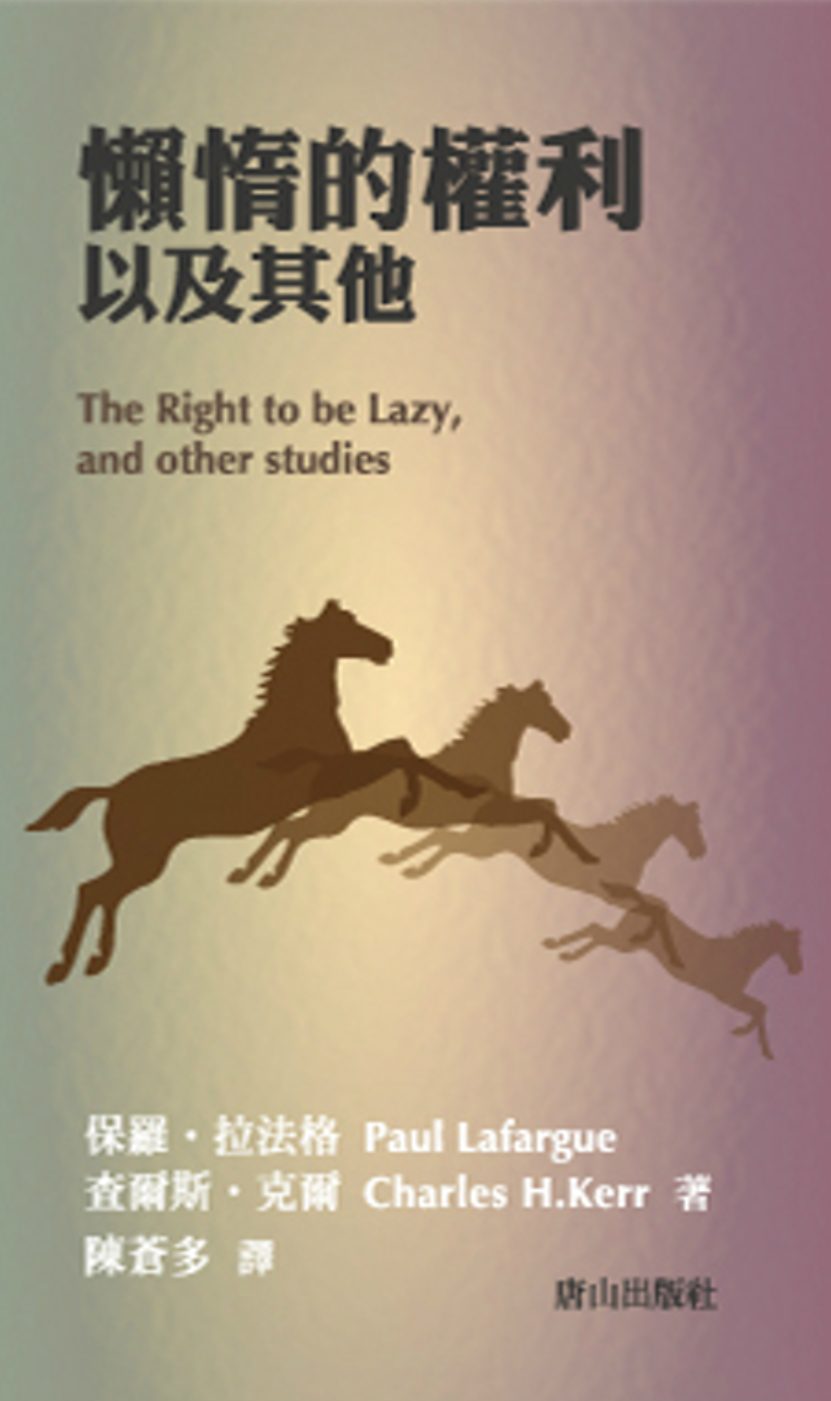
《懶惰的權利以及其他》
保羅拉法格、查爾斯克爾著,陳蒼多譯
三、被剝削的情感:壓抑、倦怠與憂鬱
其中一種左翼角度,就是看人的情感如何在資本主義下受剝削。上文提到Meštrović的著作,他提出的「後情感主義」(postemotionalism)即現代社會所設計的一個防止情緒失調(emotional disorder)的系統。狂野的情緒須要被教化,社會機器才能保持運作順暢。這說法不難理解,只消到寫字樓上班,便感受到工作環境要求員工保持冷靜。有見及此,駱頴佳要為講是非的打工仔平反:「是非就是規範下的一道裂縫。公司要控制你的情緒,於是你在廁所、茶水間盡情釋放。」上班時情緒受盡壓抑,下班了更急需渠道宣泄。《後情感社會》於1997年出版,其見解卻愈發在今天社交媒體中得到印證: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由文化工業胡亂錯置和操控的情緒,而Meštrović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情緒表達對改變社會又有沒有益處?
寫字樓職員需要長期保持冷靜,而服務性行業則跳到另一極端,動輒發揮情感服務顧客。此說法出自另一位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經典著作《被管理的心靈》(The Managed Heart)。她用上異化(estrangement)一字形容「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為了迎合顧客,就連本屬私人的情感也被商品化,情感不再由自我出發。例如迪士尼服務員需要接受笑容訓練,將之標準化,這些都屬於情緒勞動。霍希爾德說,這種形式的情緒是很淺薄的(thin),並且減弱自我與他者的連繫,更加劇了馬克思說的勞動異化問題。
這還不夠,當今職場常說要有生涯規劃,鼓勵你整個人生保持樂觀積極,隨時壓抑了別的情感。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的著作《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就從哲學角度解釋,我們為何上班要搞到這麼累。韓炳哲指出,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功績社會,過度強調要不停爭取成就,從而產生「功績主體」。追不上這種節奏,或者追趕得太快的人自然感到倦怠,呈現出一種類似憂鬱症的狀態。
談到憂鬱,駱頴佳同時推薦另一本書:甯應斌與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當中提到,若有人無法交出符合社會標準的履歷,便會陷入情緒失調狀態。駱頴佳特別談到當日準備講座時,留意到兩宗對比很大的新聞:其一,當然是情緒病患者盧凱彤驟然離世的噩耗;其二是文憑試狀元穿上醫生袍大談對未來的抱負。我們的社會一向只欣賞積極正面的人,而這些狀元日後將成為主流社會標準下的成功人士。駱頴佳由此聯想到此書:「《民困愁城》講到,在一個用履歷建立自我的社會文化之中,最悲慘的就是有一類無法進入主流的人」。如此種種,無法不教人深思社會壓榨情感的嚴酷性。

《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
韓炳哲著,譯者:莊雅慈(正文)、管中琪(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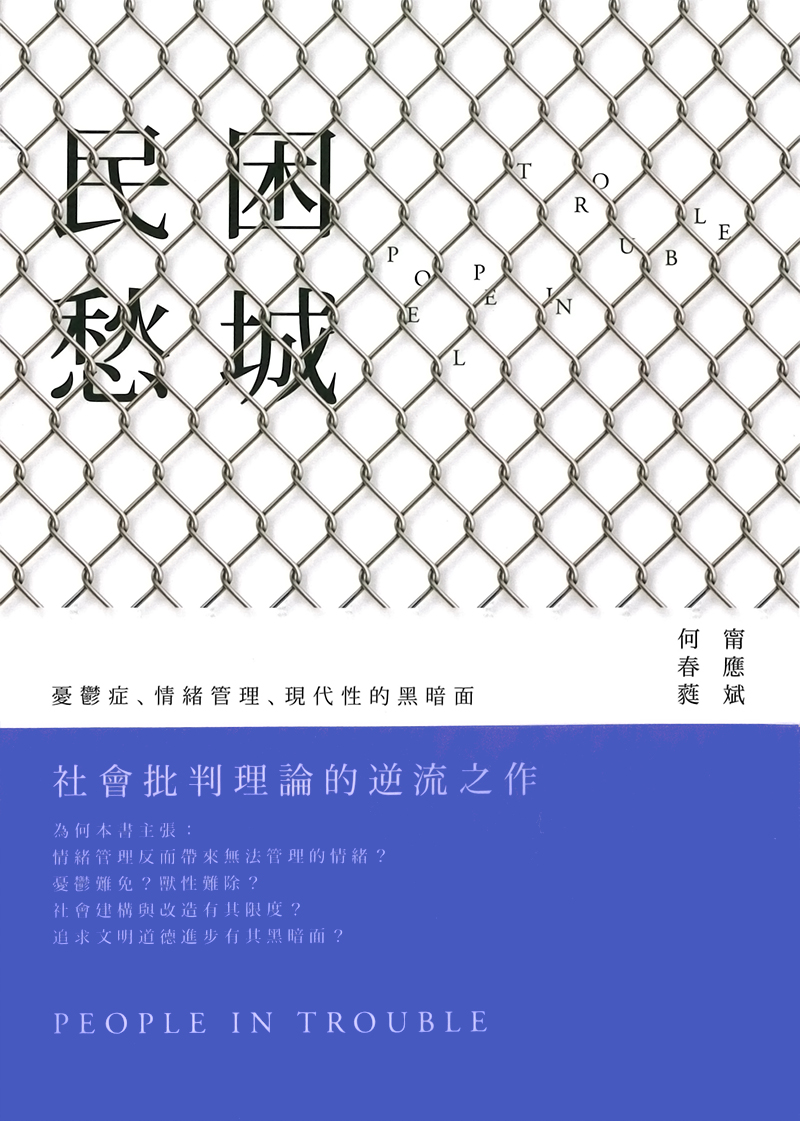
《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甯應斌、何春蕤著
四、快感的解放——以毛記分獎典禮為例
左翼對情感的思考也不是全然地批判其剝削性。銅幣的另一面是逆向操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如何動用情感重新組裝抗爭意識?在此,駱頴佳先重提2016年毛記電視「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當晚,社運圈子在社交媒體上的論爭。「我覺得分獎典禮引起的辯論,其實背後反映出左翼如何理解快感的問題。」駱頴佳說。這並不是甚麼新鮮的討論,早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學者梁濃剛的後現代理論專著《快感與兩性差別》已在書寫相關課題。雖則時代變了,問題的核心仍然一樣:到底快感經驗能否帶來真正的解放?
毛記分獎典禮打正旗號大玩二次創作,無綫電視不會播放的敏感搞笑內容,例如「有請小鳳姐」、「繁忙兒童合唱團」和「盧海鵬試咪」等,在分獎典禮中逐一登場。節目炮製出一時熱話,有觀者讚賞其顛覆性,尤其因為它斗膽挑戰「大台」的媒體霸權及其代表的保守意識形態。例如黃宇軒就表明典禮的反抗精神:「他日睇返香港歷史,《100毛》會唔會一個唔覺意就係呢個城市嘅『膠人』,開始左一場唔向現實屈服嘅運動」;何雪瑩更指出典禮可以為她充權:「今晚的分獎典禮時我們對嬰兒潮一代高呼我來了的宣言。例如整晚典禮都市廢青前廢青後,阿叻說這些網民們在現實生活中都是失敗者……我們不介意你們說我是廢青,我們會以廢青自居。」
同一社運圈中,亦有人對分獎典禮感到不以為然。當晚最大的爭議,莫過於石油公司Shell冠名贊助節目,在社交媒體衍生出「#多謝Shell」的hashtag。莫哲暐便質疑該石油公司一直破壞環境,是一家不道德的企業,進而追問:「《100毛》係一盤靠抽下政治水區取悅年輕人嘅生意……問題係呢種政治教育最終有否導向認真對待政治、分析政治,甚至起而反抗嘅力量?」我們都知道,《100毛》始終是一盤商業生意,不久以後就成為了上市公司。而這種冷嘲熱諷的媒體,最終散播的快感,會否只是另一種驅逐嚴肅政治的保守意識?
回到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傳統,流行文化工業所產生的快感一直是其批判所在。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中說道:「內在與所有歡快藝術,尤其是娛樂形式中的非正義行為,是抵制死者之苦難的非正義行為,那苦難是積累起來的,是難以言表的。」聽起來很誇張,駱頴佳就補充指,阿多諾對美學理論的思考,自是無法繞過納粹屠猶的經驗。而這樣的思考帶出的問題是,流行文化工業的本質是漠視社會的不公義的。英國左翼學者Mark Fisher的著作Capitalist Realism更會說,就算看似批判資本主義的流行文化,實際上都是建議人們接受資本主義的現實性,不會提供革命與解放的可能。
與此同時,左翼文藝傳統卻不一定完全否定快感,甚至反過來強調快感有其顛覆性。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便指出,戲劇衍生的快感有助觀眾反思社會與群眾的關係。舉例說,他所創作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會運用疏離效果,通過打破第四面牆逼使觀眾反思現實與想像的邊界,許是從作品的娛樂性和批評性中拿捏平衡。
再進一步,或者可以參考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文本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the Text)中對快感的區分:保守性的「愉悅」(pleasure/plaisir)與顛覆性的「狂喜」(bliss/jouissance)。羅蘭巴特說,「愉悅」是保守性的,即是說讀者笑的同時,只會鞏固自己既有的主流社會身份,維持原定的立場。駱頴佳舉例說,王晶的喜劇電影有時會嘲笑智障人士或女性,以此獲得的快感就是愉悅。相反,「狂喜」會使主體迷失,不斷挑戰讀者的想像與世界觀,這是顛覆性的快感體驗。
當然,駱頴佳提醒我們要小心,別太過浪漫化個別讀者的另類或自由詮釋。他提到英國文化研究學者Jim McGuigan的《文化民粹主義》(Cultural Populism)一書,當中便針對提倡創造性閱讀的學者如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批評他們盲目擁抱庶民的流行文化快感經驗,漠視背後剝削性的經濟消費生產模式。如此,McGuigan擔憂文化研究最終只會淪為沒有條件、毫無批判地接受所有流行文化的「文化民粹主義」。
回到剛才分獎典禮的論爭,駱頴佳歸結出兩種左翼觀點。對《100毛》這類流行文化持有否定態度的,往往側重於宏觀政治經濟的批判方式。譬如莫哲暐的批判,是基於文化工業背後有龐大的資金企業支持。而欣賞典禮的一群人,會較接近羅蘭巴特的說法,相對看重讀者的個人解讀。例如一個經歷過雨傘運動的抗爭者,或會在典禮的惡搞內容中找到當下處境的共鳴。駱頴佳認為反對者的觀點並不是無的放矢,尤其是經歷過雨傘運動的挫敗,不少人急於浪漫化地想像《100毛》的嘲諷作為潛在的抗爭模式,無視了它本身是一盤文化生意的事實。
「不過正反雙方都忽視一點:快感有不同性質。」駱頴佳試圖延伸羅蘭巴特的概念。他以何國榮唱《真.香港地》為例說明,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的:「係真香港人/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你一崇拜馬雲/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相對於垂直的愛國霸權,何國榮這位來港多年的澳洲籍演員以廣東話翻唱《香港地》,其快感是具有顛覆性的;但另一方面,相對於本應多元的本土文化,歌詞對香港人身份的狹隘定義是保守性的。因而駱頴佳指出:「典禮呈現出是一種雙重的快感經驗,我們對快感的理解充滿著曖昧辯證的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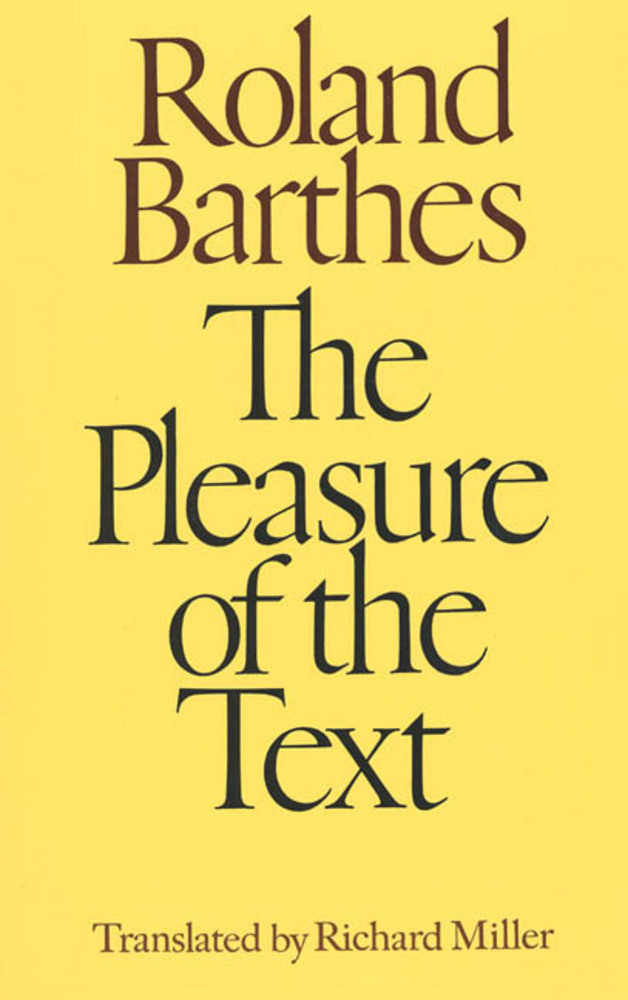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羅蘭巴特著,Richard Miller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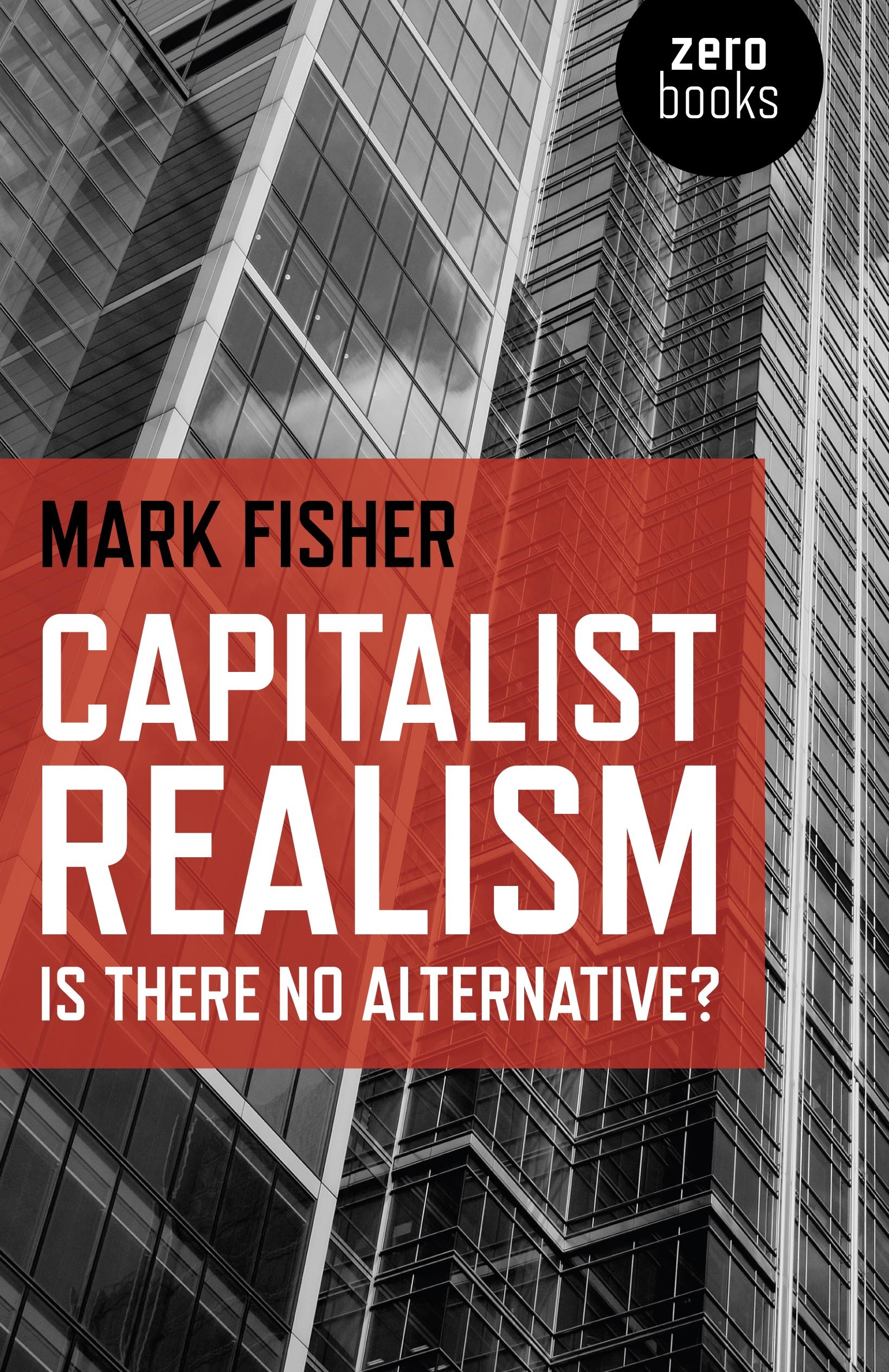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ark Fisher著
五、尾聲:情感政治的革命構想
講座至此,駱頴佳讀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80年代寫在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的一段話,句句鏗鏘:「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猶如羅蘭巴特的狂喜論,詹明信肯定快感具有革命潛力,是因為相信快感能夠動搖主體的身體。
最後,駱頴佳提到兩種以情感作為革命力量的想像。其一是意大利哲學家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諸眾」(multitude)論述。內格里認為馬克思說的階級分野已經涵蓋不了現時的社會狀況:社會剝削的再不限於物質性的勞動力,還有更多知性的、情感性的勞動力。所以他提出「諸眾」作為一種聯結不同勞動力與勞動者的概念。到底今日還可以如何聚集群眾進行社會革命?內格里指出我們要訴諸一種情感力量,回到一種斯賓諾沙說的「愛的生機力」。皆因人們遺忘了,愛是一個公共政治的概念,是一種為他者負上責任的情感;愛不應演變成僅存於保守家庭的私有化觀念。駱頴佳補充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反而會視愛為一種凝聚群眾的力量。他在陳錦輝主編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文集中也論述道,無論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抑或齊澤克(Slavoj Žižek),都在聖保羅身上看到一種革命力量。而內格里以「愛的生機力」作為基礎號召的,是一種擺脫國家主權、在憲制以外所實踐的基進民主。
而假如讀者還嫌談情說愛過於陳腔濫調,駱頴佳會推薦你看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哀慟。巴特勒認為面對「脆危性」(precariousness),或一個不斷營造不安感的苦難世界,我們需要將這些情感轉化成一種公共性的哀慟。她在近作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便談到哀悼集會的倫理。這裡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真正與社會的弱勢群體,甚至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同在?對於巴特勒而言,公開的哀悼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倫理性的身體操演(performative act),能夠產生出一種生命政治的倫理力量。她說,真正值得活的生命,是可以哀慟的生命(grievable life)。透過生命的痛苦,我們或可以連結成改變社會的生命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