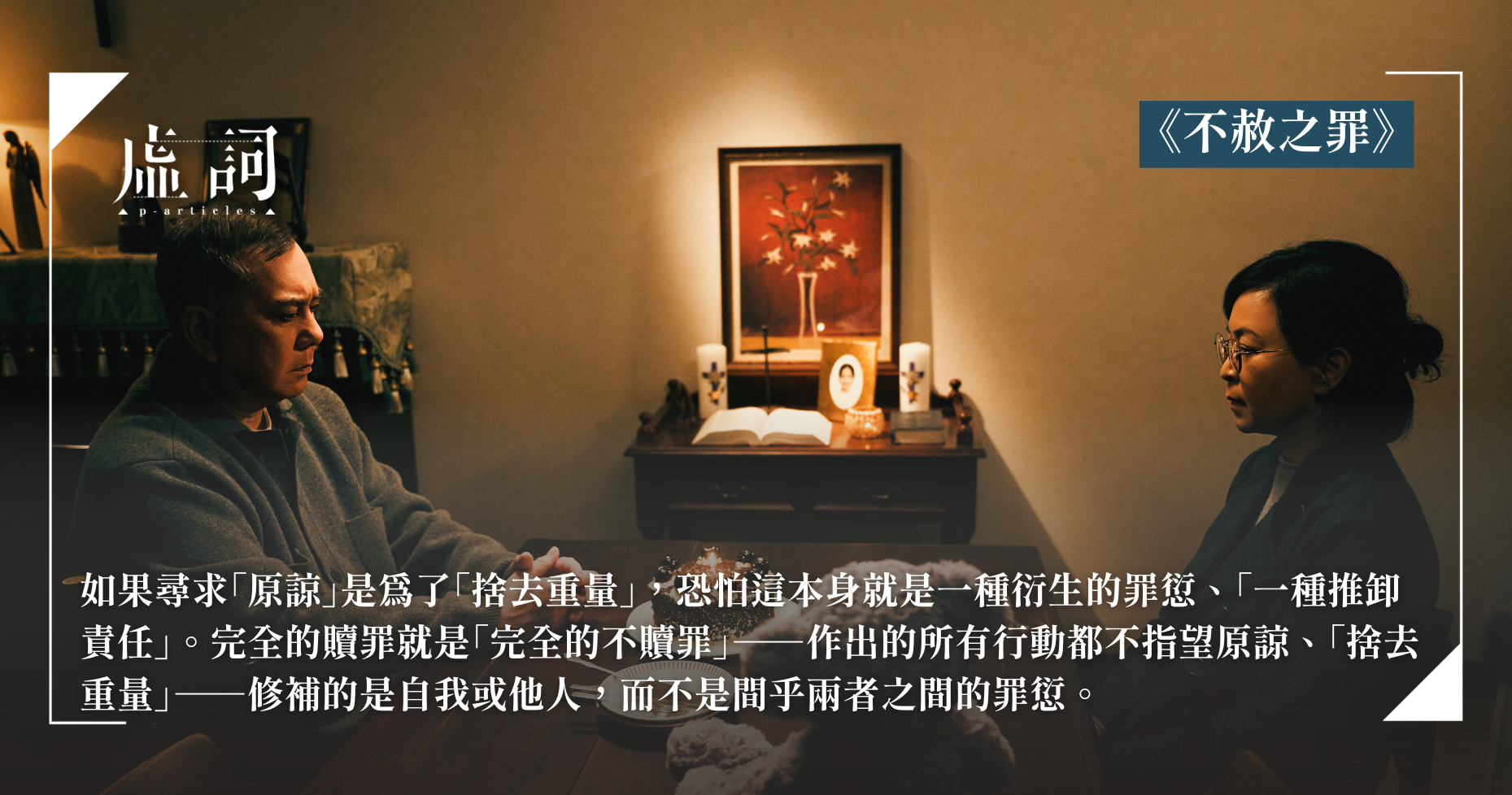《不赦之罪》與「重蟹」——關於重量、罪愆與上帝
「心思細密的觀眾或會察覺到,戲名《不赦之罪》可以解讀為不赦是一種罪,或者一種無法赦免的罪,〔⋯⋯〕。」(曾繼賢,〈《不赦之罪》:聽說過神愛很多人〉)
不可靠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之為不可靠,一個理由——按照肯南(Kenan)的說法——是其敘事被有問題的價值觀(questionable value-scheme)所渲染——「有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與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價值觀不相符。梁保羅(梁牧師,黃秋生飾)的行為、心理、言語、神態構成電影的大部分「敘事」,而他是「不可靠的」——我這樣認為。他一直覺得女兒恩晴(陳書昕飾)的死完全是陳梓樂(歐鎮灝飾)的錯,但是,從事實的層面看來,在陳梓樂的不赦之罪和恩晴的死之間,難道不是橫亙著另一樁不赦之罪?即,梁保羅對恩晴的終止懷孕的禁制。難道這不——如果不說「才是」——也是導致恩晴自殺的主要理由?然而他有多少負罪感、有多少反省?就只是在Grace(陳紫萱飾)懷孕時那短暫的閃回(flashback)而已,就沒了,這樣真的沒問題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梁惠王上》)政就是政策、法令、法則、規則。以政殺人,這就是梁保羅的不赦之罪——不帶引號。
說到「終止懷孕」的問題,基督教反墮胎的主要理據是十誡中的「不可殺人」。胎兒也是一個人——那種主張如此強調,但顯然易見的是,在這種討論中,往往是作為不用「也是」的人的懷孕女性被不在場掉。
不在場的是恩晴,她已經死了。陳梓樂得到梁保羅的原諒之後欣喜若狂,這樣真的沒問題嗎?這個男的的原諒,跟恩晴的原諒半點關係沒有。如果他想要得到的是在其不赦之罪上的原諒,他在此所得到的原諒是偽物——徹頭徹尾。
作為「無法赦免的罪」,無法也許不是指「沒有人有辦法赦免」,而是「沒有人有資格赦免」。他莫名奇妙地給恩晴發文字訊息,說請給我一次機會,梁師母(蘇玉華飾)回覆說,我不能回答你,恩晴已經不在了——事情就是這樣了。嘛,勉強要說的話,神有資格,神是一切的代理,同時也是沉默的代表,不到最後的審判沉默都不會被打破——似乎是這樣的吧?梁保羅自己也說,只有神能赦免,人是不可以的。
也正是因為神的沉默,所以梁保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引用神的話語——有時是新約的「要愛你們的仇敵」,有時是舊約的「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並城裡所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陳梓樂倚靠神的話語,也是出於自己的需要:他只是想要自己好過。恐怕,梁保羅的「原諒」也只不過是想要自己好過,因為他對陳梓樂在實際上的無法原諒與根據他所理解的教義的應該原諒無法調和。於是,通過「原諒」,這兩個男的再一次把恩晴不在場掉。
在李滄東的電影《密陽》(밀양,2007),女主角李信愛(全道嬿飾)的兒子被殺,其後她信仰上帝,並決定要去原諒殺害兒子的兇手。是上帝原諒了我⋯⋯我用眼淚來悔改,並得到了神的原諒,之後便可以心平氣和⋯⋯在上帝面前悔改並得到原諒,真是舒暢——對方這樣說。他所得到的「原諒」是真物嗎?如果是的話那還真是難以接受。但是李信愛想要給出的「原諒」又是真物嗎?恐怕也不是這樣。她發出與梁羅保相同的提問——神你憑什麼原諒他?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認為真正的原諒(forgive)外於經濟範疇,應該是純粹且無條件的。想要通過得到、給出「原諒」來換取和好,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和好聖事(confession),也就是「告解」:通過向司鐸告明自己所犯的罪過,從而得到司鐸代理天主的赦免,以與天主重修因為犯罪而被破壞的舊好。新教出於「只有神能赦免,人是不可以的」這樣的主張而不承告解的效力——懺悔的對象應該是神,而不是同為人間的司鐸。「告解」,這個詞語當作何解?我想意思是「告而後解」——解就是免除、消除的意思。
「蟹這個字,寫起來就是解體的蟲類對吧?也可說是解開糾結的蟲啊。」《化物語》裡面提到一種叫「重蟹」的怪異,「就是『意念之神』的意思。〔⋯⋯〕又可以解釋為思念與執念——也就是羈絆的意思。〔⋯⋯〕他是代替人類,承擔思想的神靈。」牠滿足人這樣的願望:「停止去想。捨去重量。」陳梓樂就是把上帝當成「重蟹」來使用——他把自己的「難以承受之重」轉嫁給神,由是自使「心平氣和」(《密陽》)、「輕鬆自在」(《化物語》)。就像把髒水倒進大海,就當作髒水從不存在。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罪者,墜也,就是重量的意思。念起來是「不赦之罪」,也可寫成「不卸之墜」(粵語讀音完全相同)。
德希達說的「原諒」後面是接著這樣一個片語的:“s’il y en a”,假如此物存在——假如此物不存在呢?終極的「捨去重量」是死亡,死亡有時被視為帶有淨化、贖罪的功效——《武士道》說作為自殺方法的切腹,同時也是「律法和儀式。〔⋯⋯〕它是武士用以抵罪、謝過、〔⋯⋯〕的方式。」但是同時,為回避上天所授予的使命而死去則完全是怯懦的。在此我想引述托馬斯.布朗爵士的奇書《醫學宗教》中一段與武士道箴言完全一致的描述:「蔑視死亡是勇敢的行為,而在生比死更可怕時,敢於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空之境界》寫到,自殺比較輕鬆啊。一時的勇氣,與必須永遠維持下去的勇氣,哪邊比較痛苦,你應該懂吧?這麼說雖然很極端,但我認為無論出於何種決斷,死亡其實都是一種推卸責任。不過,當事人可能也有逼不得已想要逃避的時候吧,這點我無法去否定,也無法提出反對意見。〔⋯⋯〕我們必須活下去,接受自己的所做所為導致的結果。
我想要討論的不是自殺,而是「不赦之罪」——無法被原諒的罪愆。重點不是罪愆的性質,只要自覺無法原諒自己,即是「不赦之罪」。這樣的話,普遍程度恐怕跟四善端不相上下:「人與罪惡的關係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我們每天都會或多或少地犯下過錯。因一些瑣碎的話傷害到別人,因無心的行動而招來別人的怨恨。人類的本質就是會將某人對自己的惡意無意識地傳達給另一個人。只要不是尚未懂事的孩子或是臥床不起的老人就不會有例外。」(《緇衣巫女》)如果尋求「原諒」是為了「捨去重量」,恐怕這本身就是一種衍生的罪愆、「一種推卸責任」。因此,完全的贖罪就是「完全的不贖罪」——並不是不作出任何行動的意思,而是,作出的所有行動都不指望原諒、「捨去重量」——修補的是自我或他人,而不是間乎兩者之間的罪愆;如果勇氣與誠懇是贖罪的必要條件,一時贖罪的勇氣,與必須永遠維持下去的勇氣,哪邊比較痛苦、哪邊比邊誠懇?
如此一來,神的意義何在?《密陽》裡面,李信愛起初被如此傳教:你看,就那一縷陽光裡,都深藏著上帝的意思。她就走到那一縷陽光那邊,說:這裡有什麼?就是陽光而已,陽光,你說有什麼呢?什麼都沒有。後來,她信教之後是這樣說的:就像戀愛一樣,戀愛的時候,總會有人給予我愛,替我著想,這樣就會很幸福啊。
兩次發言在立場上是矛盾的,但我認為具有同樣的真實性。戀人的目光能給予愛,而這種「給予」實際上並不成立——要說有了「愛」,力量就上來了,說穿了所有力量都是憑己所出。就是目光而已,目光,你說有什麼呢?這種「秘密的陽光」,甚至連實際上的溫暖都不能產生——「密陽」的溫暖是「感生」而來。神不是容納髒水的大海,而是,當凝望著大海,就覺得,即使事情無法勉回、罪愆無法償贖、重量無法卸下,也沒關係。沒關係的——讓人產生這樣的念頭,然後,繼續背負著重量地走下去。
也許是這樣的也說不定。
參考資料
- 曾繼賢,〈《不赦之罪》:聽說過神愛很多人——訪導演林善、譚善揚〉,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5308.html(瀏覽日期:2025年6月27日)
- Richard Kearney moderated. “On Forgiveness: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In Questioning God, John D. Caputo,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J. Scanlon e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3.
- 〔日〕西尾維新(林信帆譯),《化物語》(上),臺北:尖端出版,2010。
- 〔日〕奈須きのこ(鄭翠婷譯),《空之境界》(上),北京:人民文學,2019。
- 〔日〕阿泉來堂(王華懋),《緇衣巫女》,臺北:獨步文化,2023。
- 〔日〕新渡戸稲造(朱可人譯),《武士道》,杭州:浙江文藝,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