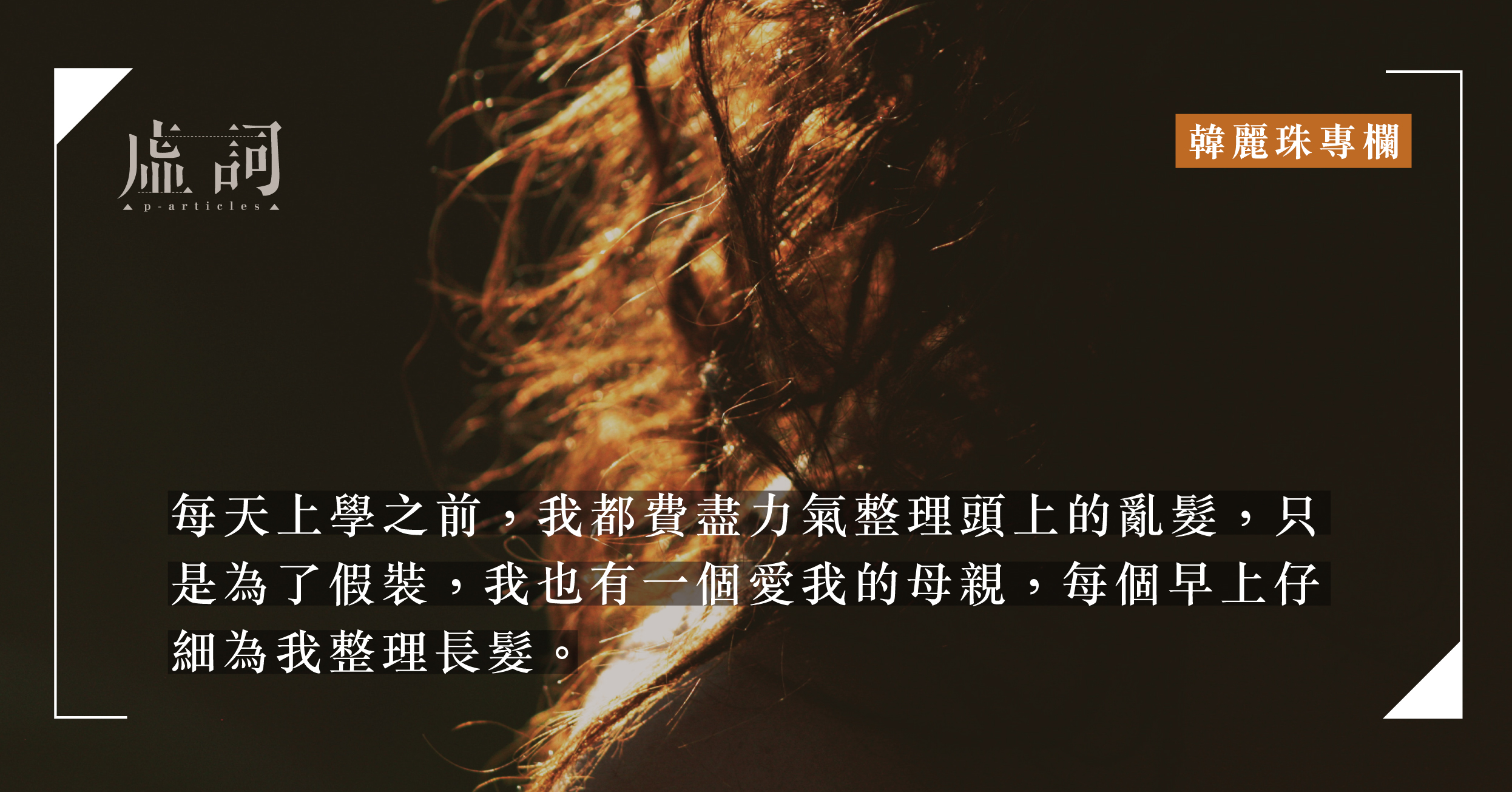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把生命綑縛
現在,G在擔憂頭頂的髮量日漸稀疏的同時,總是向我憶述,多年前那一段準備會考的日子,她如何日夜坐在書桌前,一邊溫習考試範圍和歷屆試題,一邊徒手拔掉頭上最粗硬的髮,掉落在地上的黑髮隨著她溫習的時間而漸漸增厚,完成溫習時,她會把掉髮收拾,丟進垃圾箱,而且感到非常滿足,彷彿那些令她羞恥的頭髮隨著她對於會考範圍日漸純熟而掉光。當時她非常年輕,並沒有因為拔頭髮的習慣而成為一個秃子。據她後來解說,她本來就不喜歡自己的頭髮。
我比她小十歲,那時候,無論青春期或會考都離我非常遙遠,但有時候我會拾起她拔掉的扔在地上的頭髮。那些硬生生被拔下的頭髮,毛囊仍具有冥頑不靈的生命力,那裡黏黏的,常常吸吮著地板。或許是因為那些頭髮,令孩提時期的我感到,考試就是一個削掉自己某部份的過程,即使那部份是完好無缺。或許也是在那時候開始,我本能地抗拒裁剪自己。
那時候,我的頭髮跟G的一樣,野性難馴,髮量濃密像許多匹焦躁的馬同時要跑往不同的方向,我從不想拔掉它們,只是想要編一根整齊的辮子,可是我的年紀還不足以理解梳理和編辮子的邏輯,指頭也不夠靈活。儘管如此,每天上學之前,我都費盡力氣整理頭上的亂髮,只是為了假裝,我也有一個愛我的母親,每個早上仔細為我整理長髮。
其實,K從來不管我們的頭髮,而且一直希望我們都把頭髮剪得像男生一樣短,那麼就可以省下洗頭的用水。她常常都站在鏡子前,為了收藏頭髮內早白的髮,讓自己頭髮的顏色更接近大多數的人。我喜歡注視她站在鏡子前的模樣,戰戰兢兢同時又不容有失,就像她嚴厲地教訓我們的樣子。那時候我就知道,她是我未來的模樣。頭髮是生命力的展現。她把我們生下來,把生命能量裡的精華部份分給我們。我一直認為,她髮上的色素,早在我們還只是個胚胎時,就透過臍帶輸送到我們頭上,以至她的頭髮不久後就幾近全白,而我們一直感到頭髮沉重又纏人很像一個巢穴或苦惱。
後來,當我對於編辮子早已駕輕就熟,而且常常站在鏡子前,為了控制一頭早已經歷過漂染、燙捲、剪得極短又曾留長及腰而且原因不明地大量脫落過的頭髮時,K早已不再染髮,而是讓一頭發亮的銀髮自然地暴露在任何人的目光之下。她在街上不止一次碰到對她的頭髮讚賞不絕的人。「這是在哪裡染的金絲白髮?太美了吧。」幾個陌生人(包括銀行裡偶遇的婆婆、巴士排隊等候車子時站在前面的阿嬷和在菜巿場裡一起挑魚的人)不約而同地這樣說。K感到驚訝的是,在她小心翼翼地掩蓋白髮時從沒得到認同和讚美,卻在她自覺年邁而對自己抱著接近放棄般的全然接納時,不但得到了還比她所想像的更多。
但現在我不再感到K是我未來的模樣。因為,我已習慣每天都把頭髮編成辮子,不是為了假裝被誰愛著,而是為了向自己證明,雖然頭髮長在腦後,可我還是可以不必依賴任何人的幫助,單憑自己的力量駕馭一頭亂髮。只有在那些把頭髮盤起或綑縛時,頭皮的緊繃感才令我感到實在。或許,人們對待自己的頭髮就像對待生命本身,只有通過近乎自虐的約束時,才能得到一種被規限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