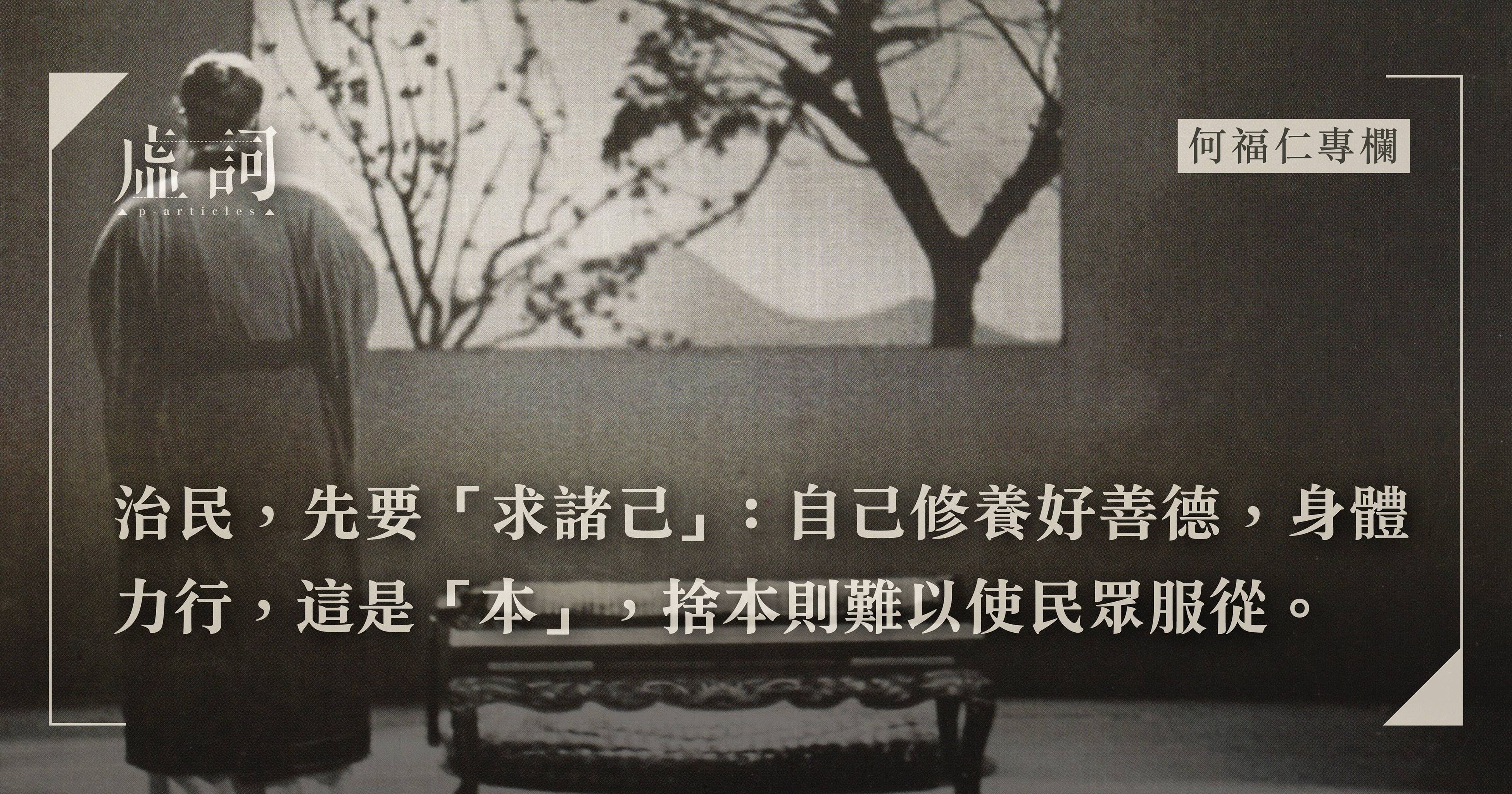【何福仁專欄:時宜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讀
1
〈泰伯8.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論語》裡孔子另一備受爭議的話,這句話,歷來由於不同的文化時空,或攻擊,或回護,至少有五六種句讀。又以說他主張「愚民」的最多。古漢語就有這個難題。這不得不頌讚五四引入標點符號之功。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分讀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譯成白話,是這樣的:
孔子說:「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什麼。」
楊氏注釋云:「這兩句與『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史記‧滑稽列傳補》) 所載西門豹之言,《商君列傳》作『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
然則孔子不啻是法家愚民說的先聲。西門豹是戰國魏文侯時的鄴令,他的話,是有見於治渠時父老子弟嫌辛苦,不想做。這是「河伯娶婦」的故事,是《史記‧滑稽列傳》的補篇,由褚少孫執筆,不無戲劇的誇誕。西門豹對「民」的斷語,下句是「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云云。
至於商鞅的話,則是游說秦孝公變法時說的。西門豹是水利專家,商鞅則是政客,都不是教育家,不以為要教育老百姓。何以說商鞅是政客?從他游說秦孝公的過程可見,他第一次說之以「帝道」,孝公直打瞌睡,還指責為商鞅引薦的人;商鞅第二次說之以「王道」,孝公仍然沒有興趣。第三次,商鞅改變策略,用「霸道」之術游說,暢論富國強兵之法,這一次孝公接納了。變法十年,《史記》云:「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下文值得注意: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說新法好,跟說新法不好,都是「亂化之民」,換言之,這才是法家「不可與慮始」的本意,好話壞話,根本不容說話。商君這種思維,為專制愚民的秦法的依據,而商君之法,又本之於魏文侯時西門豹的上司李惺的變法。
譴責孔子主張愚民,大不乏學者名人,包括馮友蘭、楊樹達、高亨、蔡尚思,等等,在「批林批孔」的年代,尤其眾口一詞。這倒奇怪,孔子要是主張愚民,與法家同呼一鼻,則理應獲得同等表揚才對。文字訓詁大家楊樹達 (楊伯峻是他的子侄)在《論語疏證》(1942年寫,1955年問世)按語云:「孔子此語似有輕視教育之病,若能盡心教育,民無不可知也。以民為愚不可知,於是乃假手於鬼神以恐之,《淮南子》所云是也,此為民不可知必然之結論。即淮南子所舉四事言之,皆人所易知之事,民決無不可知之理也。」
「盡心教育,民無不可知」,則民不單不愚,而是非常聰明,問題變成教育者能否盡心。這真是楊樹達的想法?至於孔子是否假手鬼神以恐民,大可討論。但從孔子整體思想去考察,像他這麼一個人,大半生從事教育,創辦私學,弟子三千,自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7.2),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7.7) ,又說「有教無類」 (〈衛靈公〉15.39),他種種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現代人仍奉為圭臬。他如果不是偉大的哲學家,肯定是偉大的教育家。這麼一個人會不盡心教育,甚且認為民愚,於是愚之可也?
通觀《論語》、《孔子家語》、《左傳》等等,並沒有相關愚民之說的例證。
2
清以前,學者怎樣理解這句話?
漢代鄭玄云:「民,冥也。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劉寶楠《論語正義》轉引)
魏晉何晏《論語集解》說:「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宋朱熹:「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真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四書章句集注》)
大抵都屬於回護孔子,不過細節裡有鬼。
鄭玄根本認為民愚;冥,愚昧之謂,成語云「冥頑不靈」,愚昧的民眾,倘知道本末,不利設教,故不可讓他們知道。何晏句中「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來自《易經‧繫辭上》:「百姓日用而不知」,與朱熹所說:「不能使之知真所以然」,意思相近,費解在那個「真」字。我們想想,這倒是事實,譬如我對電器真可說是白癡,但我日用,而且正在用。分工越細,老實說,如非必要,我也不想知,知了,也未必永遠記得。孟子同樣說過:「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孟子‧盡心上》)
不過,三段說法,對孔子的「可」與「不可」有不同的理解。鄭玄的「可」是應該之意。到了何朱兩位則是「能」,關乎能力問題,既是受教者也是教者的問題。有論者以為,「不可以」與「不能夠」終究都是「愚民主義」。我想,對待民眾,尤其是先秦的民眾,這二者不啻是兩套思維。前者不為,是認定不應為,因民眾知道了會有害施政;後者不為,是誠不能為,不以為讓民眾知情會有害,是做不到而已。這其實是法儒之別。儒者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2.20) 一面舉薦善才,另一面教導能力薄弱者,他們自會互相勸勉。就是要打仗了,孔子也主張進行軍事教育,否則是唾棄人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13.30) 教民,是儒者一個唸唸不忘的關鍵詞。
到了1913年,嚴復對孔子的話這樣解釋:
章中「不可」二字乃術窮之詞,由於術窮而生禁止之義,淺人不悟,乃將「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語,與「毋」、「勿」等字等量齊觀,全作禁止口氣,爾乃橫生謗議,而聖人不得已詔諭後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王栻編《嚴復集》第二冊)
然後他舉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以事理情勢利害言,都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他的「不可」,是指窮盡辦法也做不到。
1944年,郭沫若寫孔墨批判,承繼了嚴復之說:
要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愚民政策,不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則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釋也是有問題的。「可」和「不可」本有兩重意義,一是應該不應該;二是能夠不能夠。假如原意是應該不應該,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僅是能夠不能夠,那只是一個事實問題。人民在奴隸制時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故對於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樣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級的事理自不用說了。原語的涵義,無疑是指後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十批判書》)
中國古代曾否有過奴隸制時代,是另一問題。
3
不可漏了康有為和梁啓超兩師徒的意見,康南海的《論語注》對孔子此言,發揮想像:
愚民之術,乃老子之法,孔學所深惡者。聖人遍開萬法,不能執一語以疑之。且《論語》六經多古文竄亂,今文家無引之,或為劉歆傾孔子偽竄之言,當削附偽古文中。
他指出不能泥執這麼一句就質疑孔子愚民;愚民,可能又是古文派的劉歆作偽,竄入《論語》中。《論語》中的聖人,一如《新學偽經考》的角色,成為他推動政治變革的工具。一千九百年前的劉歆不是他的假想敵,而是不斷曝光的真敵。他在《論語注‧序》中云:「(《論語》)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為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篡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公羊傳》、《穀梁傳》、《春秋》,焦、京兩師徒傳的《易經》……全都滅沒,連孔子的大道也掃了地,一切,都是劉歆。
《論語注》是康氏在1902年竄居印度之作。同一年,梁新會對孔子的話有不同的解讀:
經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使知之,正使其由不可而進於可也。」(《飲冰室文集‧孔子訟冤》)
這是五四之前的新解,無論如何,結合了孔子的通盤理念:開啓民智,而不是愚民。後人因此句讀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比一股腦兒諉過劉歆有意思得多;師徒不單識見越行越遠,說到人品道德,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計。
稍後,1913年,宦懋庸的《論語稽》出版,其子宦應清為之校注,對孔子的話,加以按語:
清按:言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其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其知之。
看來實不出梁啓超之說,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無疑合情合理。奇妙的句讀,後來層出不窮,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變成孔子自問自答,而且是白話式的。
4
1993年10月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墓主大抵生活在戰國中晚期,當在孟子前後(抄寫自必早於入土),其中儒家典籍十四篇,《尊德義》、《成之聞之》兩篇對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極有參考作用。
兩篇都是向為政者說教,一篇要為政者尊德義,要遵道而行,所謂「道」,舉例說「聖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馬,馬之道也;后稷之藝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然則這個道,大抵為物事自我itself的法則,要順其質性,不能違逆。「不由其道,不行」,例如夏禹治水,要搞清楚水性(水之道);教民,同樣要知民性(民之道),民性是什麼呢?是上行下效,雖被動,卻也不是完全沒有意志,「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竹簡《緇衣》,有同樣的句子。「道」成為動詞,與「導」相通,則是教導,而這教導,也不能強迫為之。《尊德義》云: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
句意與句式,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呼應,民眾可以引導,但「不可使」,就是不可強迫。這樣的解讀,無論時間與心思,應該最接近孔子。《成之聞之》則進一步從根源上囑咐君子,治民,先要「求諸己」:自己修養好善德,身體力行,這是「本」,捨本則難以使民眾服從。「行不信則命不從,信不著則言不樂」,原來民眾是可以不從命的,果爾是思孟學派的心法。民眾可以引導,卻不可蒙蔽;可以順性駕御,卻不可牽著鼻子走:
苟不從其由,不反其本,雖強之弗入矣。上不以其道,民之從之也難。是以民可敬導也,而不可掩也;可御也,而不可牽也。
竹簡出土,揭開二千多年前孔子「可使與不可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