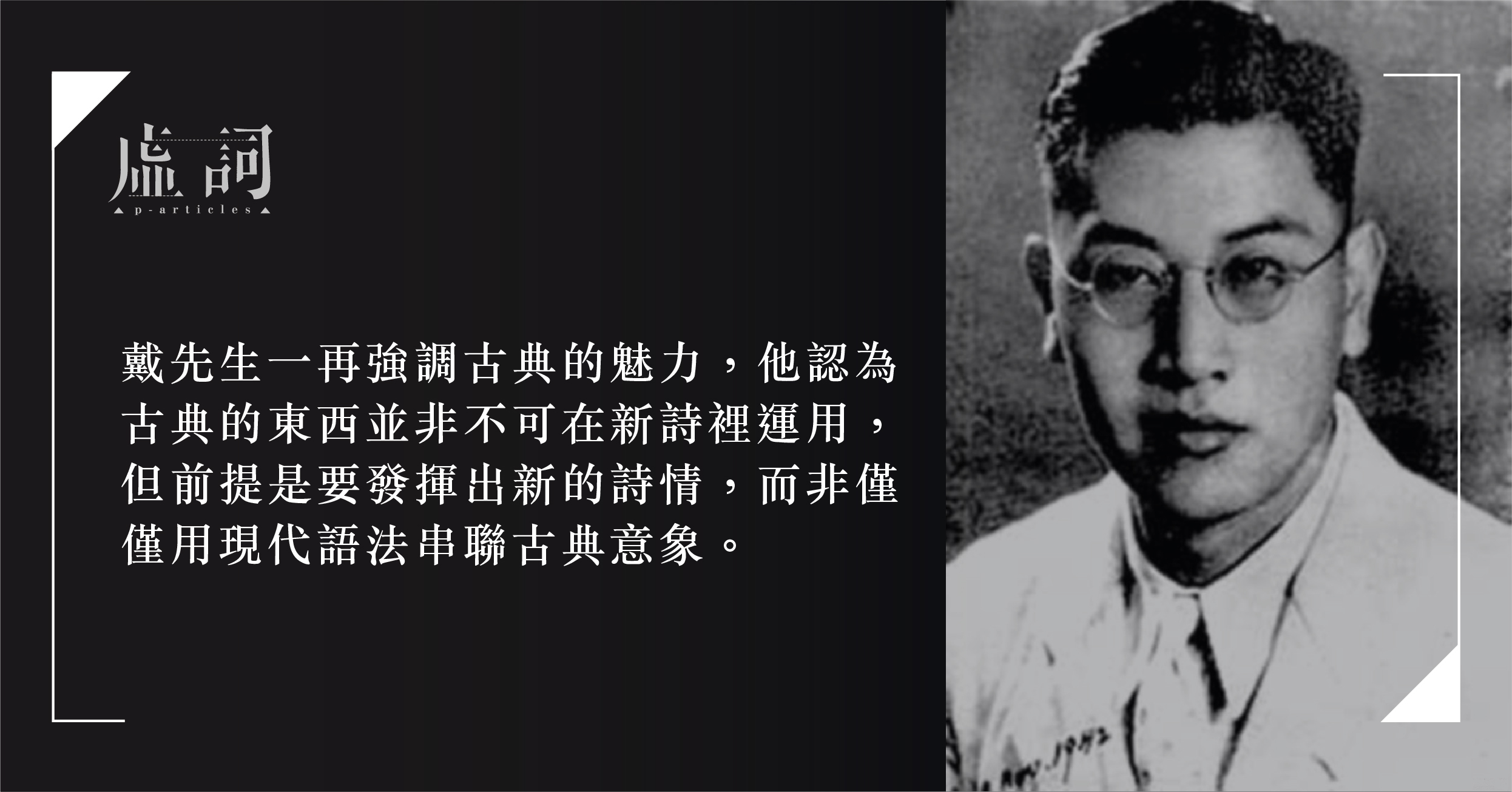聲有飛沉,響有雙疊──評戴望舒〈望舒詩論〉
最近翻讀戴望舒全集,發現其散文質量遠遠高於新詩質量。眾所周知,戴先生憑藉一首〈雨巷〉紅遍中小學的課程,但他的其他詩作(諸如〈自家傷感〉、〈寒風中聞雀聲〉、〈生涯〉),無論是節奏、意象、創新,還是他自以為豪的象徵,都實在不能算是一流,甚至在結束中學課程後,以一種較為嚴肅的視角重讀〈巷〉,也不難發現〈雨巷〉實在被全中國的中學老師過分美化了。正如余光中對他的評價:「在早期新詩人中,戴望舒的成就介於一二流之間。用中國古典與西洋大詩人的標準來衡量,他最多只能列於二流。」這首詩之所以能成名,只不過是因為內地五四以來一直推崇的溫柔敦厚的文風。
但對於戴先生我還是十分尊敬的,原因就在於他曾翻譯了我最喜愛的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且譯得不錯。因此我在翻讀全集的時候也特別留意他對於詩歌的見解,其中〈望舒詩論〉就清晰地記下了他對詩的見解。這篇詩論以點列的方式書寫,應是創作雜感,篇幅不長僅有17句話,但這短短的17句話中矛盾重重,想法雜亂,更遑論能自成一個詩論體系。原文如下:
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失去了音樂的成分。
詩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
單是美的字眼的組合不是詩的特點。
象徵派的人們說:「大自然是被淫過一千次的娼婦。」但是新的娼婦安知不會被淫過一萬次。被淫的次數是沒有關係的,我們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
新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aunce。
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緒成為畸形的。倘把詩的情緒去適應呆滯的,表面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剝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較合腳的鞋子,但是智者卻為自己製最合自己腳的鞋子。
詩不是某一個感官的享樂,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東西。
新的詩應該有新的情緒和表現這種情緒的形式。所謂形式絕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絕非新的字眼的堆積。
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我不反對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舊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詩情。
舊的古典的應用是無可反對的,在它給予我們一個新情緒的時候。
不應該有只是炫奇的裝飾癖,那是不永存的。
詩應該有自己的originalite(法文,即獨創性),但你須使它有cosmopolite(法文,即普世性),兩者不能缺一。
詩是由真實經過想像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像。
詩應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詩本身就像是一個生物,不是無生物。
情緒不是用攝影機攝出來的,它應當用巧妙的筆觸描出來。這種筆觸又須使活的,千變萬化的。
只在某一種文字寫的,某一國人讀了感到好的詩,實際上不是詩,那最多是文字的魔術。真的詩的好處不就是文字的好處。
筆者在上文說到,這17點矛盾重重,以下仔細分析:
首先,第1點和第5點之間有矛盾,第1點說詩歌不能借重音樂,這應該是為了回應當時新月派注重詩歌音樂性的理論。但在第5點,戴先生卻說,詩的韻律在情緒的抑揚頓挫上。這裡可以看出,戴先生實際上是注重詩歌的音樂性的,但他強調的是情緒的頓挫而非音節的安排。但筆者認為二者是不可分割之物,情緒的頓挫必然會導致音節的頓挫,音節的合理安排也有助詩意的更好傳達。《毛詩・序》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也就是說志(情緒)成為言(詩)的過程當中必然需要藉助語言。詩的其中一種功用是表達情緒,我們不難想像,惱怒的人所寫的字自然較為憤慨,愉快的人所寫的字自然較為柔和,正如《禮記・樂記》所載:「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是故其哀心感動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這段引言即說明構成樂的音會因為人的不同情緒而改變,而音同時也是一首詩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首詩讀出來便有了音,因此詩歌作者情緒的抑揚頓挫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作品文字的節奏,讀者在讀一首詩的時候也可從字的抑揚頓挫去感受作詩人情緒上的跳動。因此詩的韻律了可體現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詩歌也不可能去掉音樂的成分。
其次,第1及第2點和第8點之間有矛盾, 第8點作者說詩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的東西。感官不外乎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等。戴先生說「全感官」,也就是說他承認詩歌應該包含所有的這些感覺,即不能僅僅只是其中任何一種感覺。而最能體現聽覺的是「音樂的成分」,最能體現視覺的是「繪畫的長處」,為何主張「全感官」的戴先生要反對詩歌的音樂成分和繪畫成分呢?
還有,第9點戴先生說新詩應該有新的情緒和表現這種情緒的新的形式,這其實和第4點的說法是重複的,所謂新的表現形式不過就是他在第4點說的「新的淫具」和「新的淫法」。但戴先生卻在第9點多補充一句「所謂形式,決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決非新的字眼的堆積。」這一點實際上和戴先生另一篇文章〈談林庚的詩見和「四行詩」〉的看法一致,該文批評林庚先生的四行詩只是用白話文的語法串聯古典的意象,只是新瓶裝舊酒。照邏輯上講第9點並無甚麼毛病,只是筆者執著於第一句的「形式」一詞。辭典對於「形式」有兩種解釋:一是事物的形狀,解構。二是把構成事物的諸要素統一起來的結構方式及其表現方式,與內容相反。無論是解釋一還是解釋二,都可見「形式」即是內容的對立物,而一首詩中與內容無關的(即形式)不外乎文字的排列、語言的選擇,但他下半句又說這形式絕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非字眼的堆積。從後半句看來,戴先生對新詩的主張或許是要內容創新,這和〈談林庚的詩見和「四行詩」〉的主旨吻合,因此,筆者認為第9點的兩個「形式」都應改為「內容」。否則,既主張形式,又說形式非形式,那這種既是形式又非形式的東西到底是甚麼?故弄玄虛,容易混淆讀者。
另外,第10、11點意思也重複,二者都在肯定古典的價值,戴先生一再強調古典的魅力,他認為古典的東西並非不可在新詩裡運用,但前提是要發揮出新的詩情,而非僅僅用現代語法串聯古典意象。他的〈雨巷〉即十分吻合這一理念,〈雨巷〉一詩便是藉丁香表達愁結,而同時又結合時代的抑鬱,表達了一種比愁結更為朦朧、更為幽深的迷惘和感傷。藉古典意象抒發現代情緒。這本是目光很前衛的看法,可平衡守古派和創新派之間的衝突,但筆者想到了第1、2點,為何如此前衛,如此主張古可化為今用的戴先生卻要將音樂和繪畫排斥在外,難道音樂性和繪畫性不是古典詩歌的特性嗎?《文心雕龍・聲律篇》談到:「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也就是說,凡是語音聲調都有規律,如果違法了聲律配合的規律,就會佶屈聱牙,好像作家得了口吃一樣。〈聲律篇〉又說:「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也就是說古代走路時左右會佩戴不同的玉器以調節步伐,何況聲律是用來是文章具有聲韻節律之美的,怎麼可以忽視呢?至於繪畫的長處,王維〈使至塞上〉、杜甫〈望嶽〉都以畫法為詩法,烘雲托月,移以作詩行文。由此可見,音樂性和繪畫美自古都被運用於詩歌創作當中,戴先生說舊的古典的運用是無可反對的,那麼在新詩創作中融合音樂性和繪畫的長處也理應是可以的。
第14點,戴先生認為詩是處於真實和想像之間的東西,筆者認為此處「真實」若改為「現實」更為恰當(哲學界認為現實為客觀存在之物,是世界的表象,而真實是穿越表象的真理),但戴先生的意思是很明確的,即認為詩歌人的心受過現實的激蕩後所產生的聯想和想象,二者缺一不可。詩歌究竟是否真的如此,筆者在此不做評價,筆者只是覺得,這個說法也和第1、2點有矛盾。如果說詩的一部分是由現實而來,而我們觀察現實的表象不外乎透過眼耳口鼻,眼睛所見必然是畫面、耳朵所聞必然是聲音,那麼認為詩歌是由現實而來的戴先生為何又要將音樂的成分和繪畫的長處排斥在外呢?
最後,戴先生在第17點認為好詩是經得起翻譯的。我們知道戴先生曾留學法國,後來翻譯了雨果、波德萊爾、魏爾倫、果爾蒙、保爾・福爾、耶麥等人的詩作,他說這句話好像十分具說服力。但筆者認為經不經得起翻譯與原詩無關,同樣是一首詩,經不經得起翻譯還得看譯者譯得如何,不難想像,一個較好譯者當然可以翻譯好一首詩,而在一位三流的譯者手裡,再好的詩也經不起考驗。戴先生還說,真的詩的好處就是文字的好處,也就是說詩歌是由文字構成的,是文字的藝術。但筆者認為,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藝術,難道我們可以說金字塔比長城偉大嗎?而且,同樣一首中國詩,被不同語言翻譯的效果也是不同的,難道我們可以說日本語翻譯的〈靜夜思〉比美國語翻譯的〈靜夜思〉較好嗎?翻譯過程中難免會削弱該語言文字的特點,比如中國古典詩歌被翻譯為外文時就很難完美地保留平仄、押韻等聲律美。若按戴先生說,好詩是經得起翻譯的,筆者認為相較於文字,在翻譯過程中削弱較小的應該是意象,若從這個角度看,戴先生認為一首詩之所以好,就是因為意象運用得好,但如果說戴先生認為意象對於一首詩十分重要的話,第2點(認為詩歌應該除去繪畫的長處)的觀點又和他自相矛盾了。
綜合上述,戴望舒先生的〈望舒詩論〉邏輯混亂,謬誤甚多,若作為他個人的創作札記尚可,若要視作「詩論」,則實在有待修飾。
(標題由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