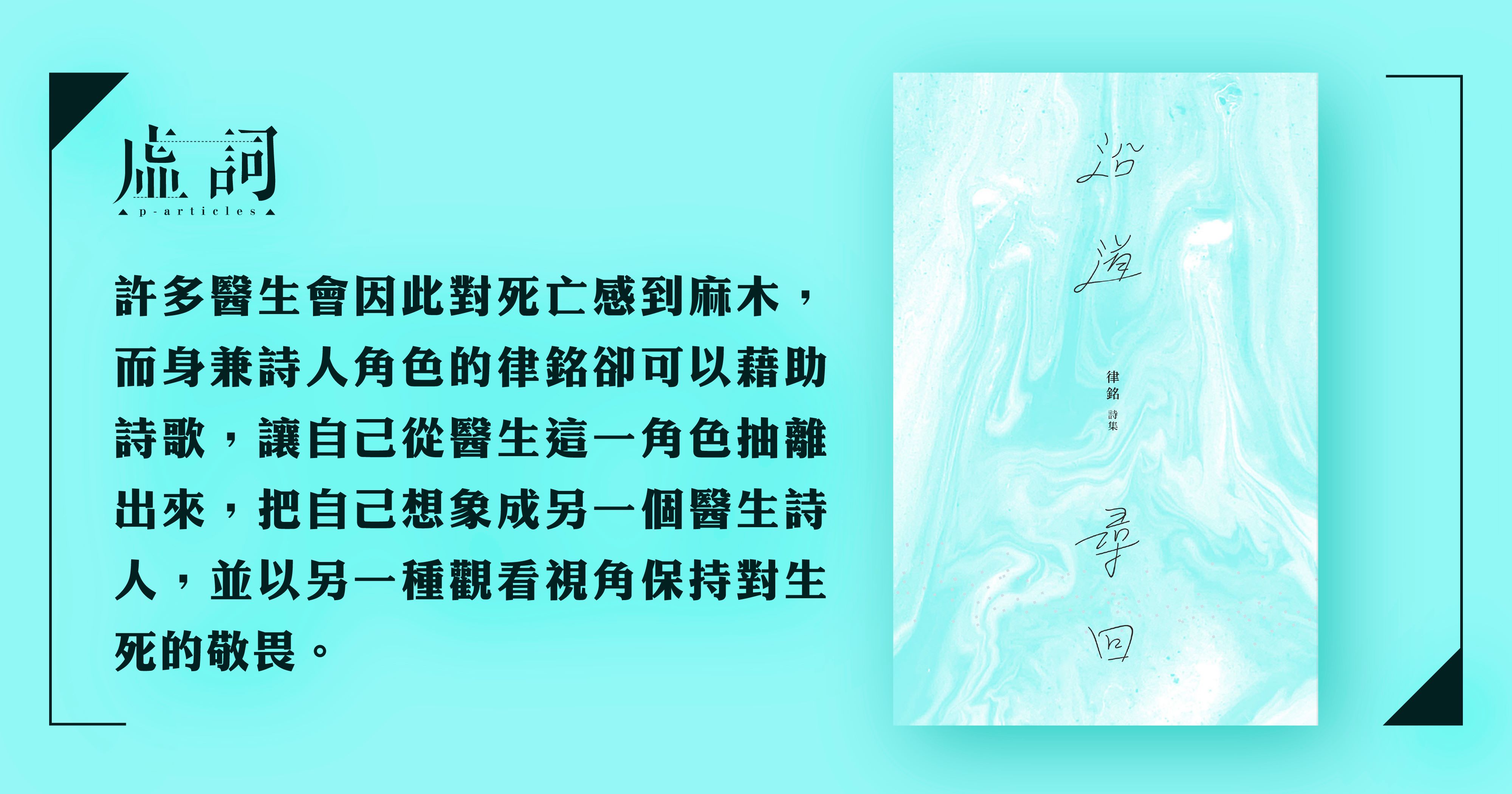律銘的「醫」與「文」之辯證——評詩集《沿道尋回》
(一)
在「作者已死」這一口號高喊了半個多世紀的今天,在多數人都認定詩歌無法言傳只能意會的今天,竟然再次見到有作者願意為自己的作品做詳盡的解釋,為讀者作耐心的引導。這是我翻讀律銘新詩集《沿道尋回》時最深刻的初印象。無論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者是什麼》(What Is an Author?),還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gesture之說,都在不斷質疑和反對由古典主義以來便日漸鞏固的作者之權威。在這種質疑的潮流之下,許多對作品作過多詮釋的創作者都會被扣上落後的「罪名」,被認為是不願接受所指(signified)的任意性。而律銘在這本詩集中卻一反潮流,在不少詩作之後附上一段後記,清楚交代寫作時間、創作緣由、書寫主題、寄予對象,甚至是不少寫作者最不願意向他人透露的構思歷程,有意地「將文學的門檻降低」,以遷就「普通讀者」的閱讀。這與其說是一種退步,不如說是一種讀者與作者之間的相互監督,以免作者不負責任地將文本意義的解讀全然交予讀者。這種有意反潮流的價值取向在其開篇之作〈沿海岸線行走〉之中已可見一斑:
百年來沿海岸線行走,綠色鐵箱間中
吞吐叮叮聲,提醒過客「馬路如虎口」
路不再有馬,對弈時代,車前倒後比較堂皇
而鐵箱,只沿著記憶,始終明確,勝在純粹
相對巴士,路線一呼一吸,廢氣從沒
納入討論,車費如排放有增無減
人口漸長,鐵箱日趨擁擠,另建地底長蛇
由最東去最西,表面四十分鐘(不覺爬行四十年)
由時代走入月台,歎聲「行到腳軟都未到」
長蛇善走長途,鐵箱月台成了長者的
安全島,接駁前往街市買魚數百步
原來的,霋東街車場被藏攪牌內,暴亂時人潮
還不及現在,配名廣場,大電視為記
秒秒更替,不用人手,或推移
路軌變向,航道不曾搖,兩旁走馬燈風景
潮汐遷徙,見證維港逐漸夾埋
自由和眼界,如果,歷史應被保護或淘汰
輝煌叫人難解,情緒生鏽怕複雜
趁時代明媚的日子,不妨沿著海岸線行走
如果路還知道有馬,海還知道有岸
這首詩雖然明顯是以香港為背景書寫今昔之對比,但當中刻畫出的強烈的時代轉變卻也暗含作者在時代更替之中的價值取向,他直接在該詩後記中寫到:「時代的更替是恆常的,沒有好壞對錯,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活在一個大時代中的角色和位置。」這正是他對語言的選擇,即使在一個人人都任由讀者自己解讀文本的年代,作者仍有權選擇為自己的詩歌作或簡單或詳盡的解釋,因為現代的「鐵路」和「巴士」,未必就比「曾經的電車」可靠。
律銘的詩作有其獨特的節奏、語感以及聯想邏輯,書面語和口頭語相夾雜,許多詩作甚至隨著意識的流動而出現前後主題不一致的情況。就像〈一直逃避的原因〉便是這樣的創作狀態,從詩作一開始的「關於死亡」到「就如落葉無法得知」寫的是死亡,從「為何被選上抑或不被選上」到「被獵與捕食者一脈之差」寫的是寫作的過程,從「詩人甚少受到攻擊」到詩末寫的是因寫作而不得不面對的恐懼。這三個部分的所指並沒有明顯直接的聯繫,這當然不算是什麼問題,但一定程度上為讀者揣摩作者原意增添了難度。而他在該詩後記清楚寫到「本來是想寫死亡,後來盪失路。寫了自身。和恐懼。」便為讀者和評論者提供了若干解讀線索。
(二)
筆者和律銘相識於由《聲韻詩刊》舉辦的某次詩聚上,詩聚上與會者各自分享自己的詩作。詩聚結束後回家的路上,筆者收到律銘傳來的簡訊,詳細指出了拙作的可取之處與有待改善之處。此後只是偶爾才會在社交軟件上交流談論。在筆者印象當中,最為深刻的莫過於律銘的職業——醫生,一名寫詩的醫生。先不論「棄醫從文」是否真有其事,受魯迅的影響,「醫生」與「詩人」這兩個標籤讓筆者馬上聯想到靈肉的二分。認同這一說法的評者承認「醫生」與「詩人」都有救人的功能,但普遍認為前者只能拯救個體的身軀,而後者拯救的是個體的精神或靈魂,並且強調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詩人周漢輝也在〈代序〉中也留意到〈這年頭有些話開不了口〉一詩引用了魯迅的說法:「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但筆者認為,這無疑是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中提到的「倒錯」現象。所謂「倒錯」,也就是顛覆正常的認知順序,因某物後天概念的影響而認為該物自古便是如此。就像魯迅棄醫從文之事廣為人知之後,後人便慣性地將「醫」與「文」之衝突當作是必然,忘記了這其實是兩種互不相斥的身份。除了魯迅之外,郭沫若曾獲得福岡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學士學位、冰心曾是協和女子大學醫科預備班學生、畢淑敏曾經從事醫學工作數十年、羅大佑畢業於私立台灣中華醫學院醫學系;至於西方國家,柏拉圖、契科夫、渡邊淳一、毛姆等大家都是(曾是)醫生和文人的結合體。姑勿論那些可以完美協調兩種身份的例子,單論棄醫從文的例子,那些醫生作家放棄行醫/讀醫的原因已經各式各樣,我們又如何可以簡單地將所有原因都總歸為「靈肉衝突」呢!
宮愛玲在〈「棄醫從文」現象新論〉一文中對不同醫生作家放棄行醫的原因進行細分,除了每一種情況都共有的「棄醫從文者對文學的熱愛和癡狂」之外,還有:
- 棄醫從文者的文化啟蒙;
- 從文(有助)改善物質處境;
- 對生命獨特體悟和敬畏之情;
- 文學是沉重生活裡的自由暢想。
首先討論文化啟蒙。魯迅所處的年代外憂內患日益嚴重,知識份子極須尋求救國的方法,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小說救國論」影響著一代的青年,魯迅等人便是在這種環境下接受和創作文藝,這與律銘所處的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大相徑庭,先不說國族局勢如何不同,單就文藝在社會上受重視的程度而言,此時與彼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至於第二點,「從文(有助)改善自身物質處境」,這在當下的香港更是天方夜譚,不必贅述。
因此,若我們仍舊單憑律銘的這兩個標籤簡單將之與魯迅進行比較,並認為他和魯迅做著同樣的取捨,未免有點附會典故的牽強。由上文論證已可得知,律銘和魯迅之間還是有著極大的不同之處,而且至少,前者沒有徹底放棄行醫,我們甚至不難發現他在詩歌中常常寫到與自己職業相關的場景,例如〈幫助〉的「治療者,和病者應保持。兩米距離/相同的問句,會有不同的答案/影響流水的速度和方向,甚少差池」便是以病者的視角觀看醫者工作的日常。因此我們絕不應該簡單把魯迅的典故套用在律銘身上。律銘在「醫」與「文」之間的取態,筆者認為更接近第三點與第四點。
先論第三點「對生命獨特體悟和敬畏之情」。宮愛玲在她的文章中以畢淑敏為例,說明醫生這一職業帶給醫生作家的死亡經驗讓他們產生對生命的敬畏,並借書寫將這種敬畏轉化成文字。律銘從醫多年,所接觸、所見證的生死也必然多於其他人,就像〈請容我以為自己是鯨向海〉一詩所寫:
我無法面對世界的荒謬
望見熱血醫護的自爆
病人在急症室等三天才可能上到病房
間中一兩個心跳停頓原地施救
死去的眼睛依舊睜開
許多醫生會因此對死亡感到麻木,正如〈幫助〉一詩的後記所說:「很多時醫者可能做過相同的步驟一萬次,已經習以為常。」,而身兼詩人角色的律銘卻可以藉助詩歌,讓自己從醫生這一角色抽離出來,把自己想象成另一個醫生詩人(鯨向海),「讓一切荒謬留於紙上/讓一切真實歸於虛無」,並以另一種觀看視角保持對生死的敬畏。
也正是因為這種抽離,文學成了作者「沉重生活裡的自由暢想」,亦即上文提到的第四點,可以讓律銘在面對「實體的病人」時,「不會在看到實在的血肉之軀」。就像宮愛玲文章中提到的馮唐之例,寫作於律銘和馮唐而言都並非謀生之道,而他們都選擇了在擁有正職工作的同時進行創作,「這一方面與其醫學經歷有關,即在學醫過程中,深切地體會到了生老病死的難以捉摸。另一方面則與其對時間的恐懼有關,馮唐自稱試圖通過文字來打敗時間。在馮唐看來,不朽的寫作就是作品同時間的較量。」這在律銘的詩作中亦有所體現,〈我的淆底獸〉便形象地寫出一名醫生日常時間的恐懼和焦慮(淆底),可幸的是,讀者可以在詩的結尾看到詩人對自身恐懼的克服:「我知道淆底獸會慢慢長大/因為當經驗累積/會懂得擔心得更多更遠更全面/我是一個更安全的大夫,至少」,這種對恐懼的克服,筆者認為便是文藝創作帶給他的和解。
綜合上文所述,與魯迅所處時期的環境相比,如今詩歌(文藝)向外的作用逐漸減弱,更多轉向了轉向私人領域的內在協調,「醫生作家」這一特殊身份雖然仍是靈與肉之辯證,即「醫」和「文」仍然分別對應「肉」與「靈」,但「五四」時期對「靈」的治療效用指向接受者,而律銘和馮唐等人則是將這一治療效用指向創作者本身,從外向於讀者轉向對作者自身的關注和治療。正如宮愛玲一文的結尾所說:「(醫者寫作的)動機從歷史的一元集結走向了多元共存。從救世救國的大使命轉變為個體自我的興趣追求。」若沿著這一角度閱讀《沿道尋回》,可以發現律銘詩作中更多外向於讀者/世人的觀察,以及內向於內心的自我關注,並見證一場關乎內與外的自我辯證的過程,直至在時間之河中匯成一條緩緩的長流。
2021.1.12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