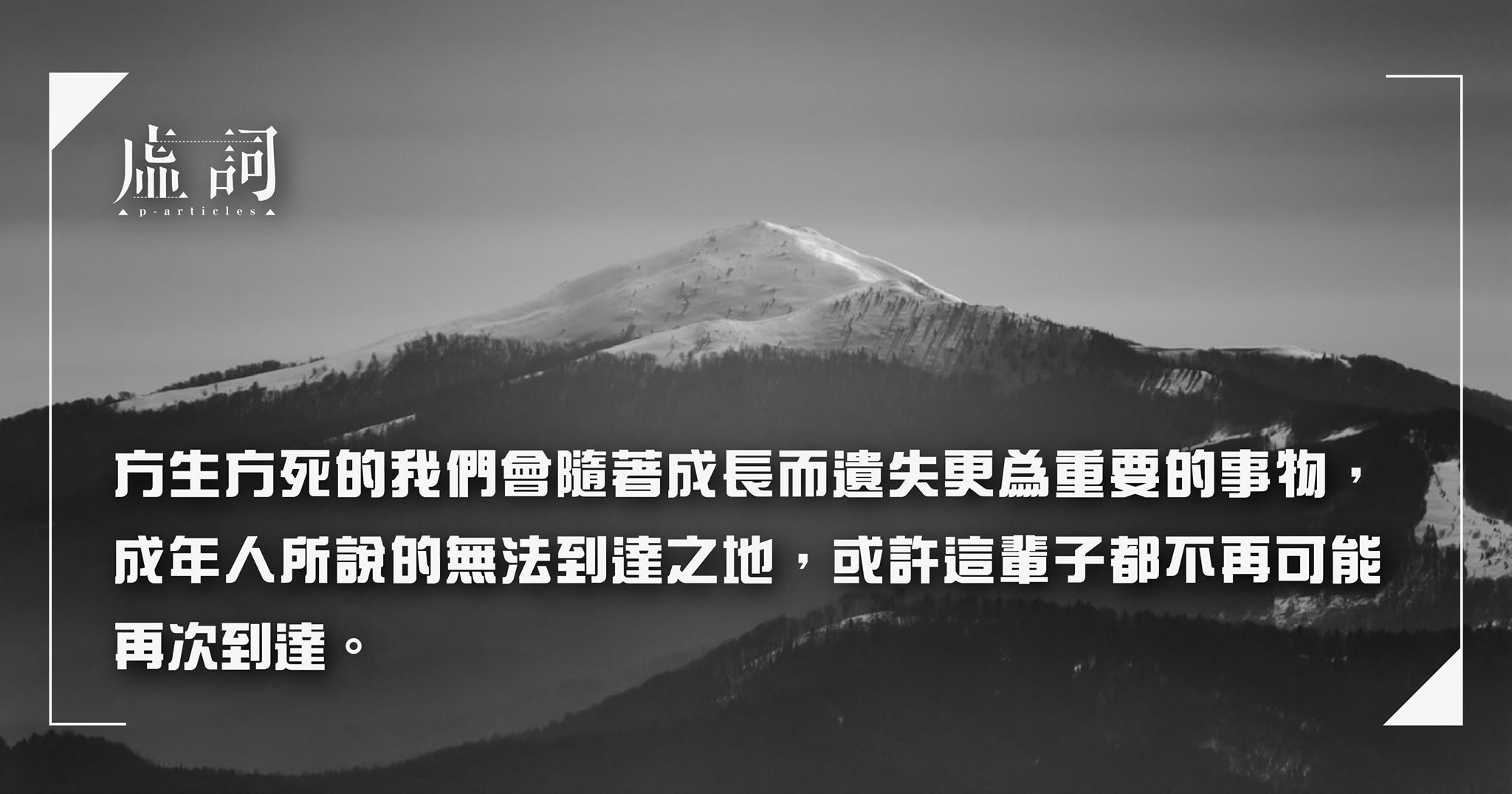方生方死——讀米米〈一個無法抵達的地方〉
詩題讓我想起最初學習創作的時候,總會直截了當地在作品中構建一個烏托邦。「無法抵達的地方」,跟「給二十年後的自己」、「我的夢想」之類的題目一樣,似乎都是每個創作人無法避開的練習,我也因此從中感到一絲童真。而對於早已成年的詩人米米而言,再次為一首詩進行如此童稚的命名,當中的情緒或許就不只是簡單的對烏托邦的構想了。
限於能力和財力,年幼時的我們總有許多地方無法到達,例如百聞不曾一見的異國,例如高不可攀的山頂和雲端,例如那些被父母列為禁區的場所,但這些曾經無法到達的地方現在我們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抵達;由此觀之,孩童眼中無法抵達的地方或許並不難以到達,相反,方生方死的我們會隨著成長而遺失更為重要的事物,成年人所說的無法到達之地,或許這輩子都不再可能再次到達。筆者認為,詩人說的這個無法到達之地是一個純粹以感情主導的世界。正如開首設置的場景:
湛藍的海在枯枝末端
萎縮成一滴淚
和你的歎息一同墜毀
那是一個我們完全沒法抵達的地方
「淚」和「歎息」都是情感極為濃厚的意象,在這個詩人夢幻的場景中,一滴淚可以容納整個海洋,一聲歎息可以讓一切都墜毀,那些我們習慣性去抑制的情感在詩人幻想的世界中竟然可以主導一切,甚至連痛苦都會被治愈,「無間地翻騰」,翻騰過後便是蒸發、汽化,沉重的痛苦因此變得輕盈。詩人此處用「痛苦將被治愈/或無間地翻騰」呼應首句「湛藍的海」,可見於他而言,所謂的痛苦不過是因為大量消極的情感無法充分得到抒發,若有一個允許情緒主導的世界,這些痛苦也自然會變得很輕。
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便可以卸下防備,摒棄所有不必要的考慮和理性,盡情用情緒去感受自然。現實中我們不斷成長,也不斷習慣憑藉理性對待身邊的所有事情,這些社會教曉我們的處事方法或許能夠很有效率地解決問題,但已有不少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更多時候是非理性的。因此,如果我們僅憑理性待事,視野難免過於狹窄,只能得到可見之物,那些需要用心感受的物外之物則會被我們遺漏。我想起清人沈復在〈童趣〉中回憶的那些趣事,他之所以能夠時常感受到「物外之趣」,正是因為能夠拋棄成人世界的待物規則,憑一顆童稚之心去感受和想象世界,正如米米所寫,「赤腳踩著熾熱的沙灘/接收雲端以外的私訊。」拋棄理性後所感受到的世界,或許更真實,更真切。
詩人首節是第二人稱,「你」可理解為過去的自己,那麼整節都可視為現在與過去的對話,這種穿越時空的對話延續到第二節:
你好嗎
還在蹉跎
還在端視流星的尾巴嗎
這節所用的意象和所營造的畫面都很簡單,不過是一個對未知的成長感到迷茫的孩子仰望著星空,但筆者認為這個畫面是為第三節的出現而做的鋪墊。如果說第二節的煩惱和痛苦充滿了未知,那麼第三節所寫的痛苦則已經真真實實地發生過,或是正在作者的生命中發生的事情:
在霧一樣的時日
我常常校正膨脹的字體
用指尖安撫它們
碎裂的意圖
灰冷的文字被摘下
成為寒夜發光的詩題
我們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長大,但迷茫還是依舊,時日也像迷霧一樣模糊不清。霧是虛無縹緲的,詩人似乎很喜歡運用這一意象,正如同一詩集中另一首詩〈之後〉的最後一句「而方向/『也不過是一種指示性的霧』」,同樣以霧指代不確定的前程。我們再看回〈一個無法抵達的地方〉,詩人把現實生活中經歷的一些苦痛比喻為海,出航日久,難免有瀰漫的海霧模糊視野。面對眼前渺茫的迷霧和不確定的去路,我們是保持初心?還是會在時間之流中逐漸迷失自己?米米結合自己寫作的經驗,用「膨脹的字體」隱喻逐漸走樣的初心,作為一個渴望保持自我的人,他能夠做的只是不時地「校正」。這一方面暗示了現實社會對童心毫不留情的考驗,另一方面筆者又聯想到本土詩歌創作的實況,近年來詩歌比賽總是會更傾向於挑選較長的詩,即所謂的得獎詩體,在這種「主流風氣」的影響下,不少參賽者將詩歌越寫越長,以為寫得長就有深度,唯恐短了就會顯得單薄,這種不斷「膨脹」的詩句,是否已經失去了寫詩的初心呢?詩人似乎給出了答案,當膨脹到一定程度,原本的「意圖」便會「碎裂」,我們只有把碎裂後「灰冷的文字」摘下,留下最原本、最初始的核心,才能「成為寒夜發光的詩題」。往往,我們窮盡一生追求的東西,早在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完成。正如那本終將以「你」為名的詩集,「一早已被完成。」
首次讀這首詩的時候,讀到的是一個並不完美的愛情故事,但再三細嚼,發現可以有第二種詮釋。也許作者創作時並無這層考慮,筆者只希望把「好與壞都交給讀者自行判斷」的米米不要介意我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解讀。
原詩摘自詩集《如是跋扈》,如下:
湛藍的海在枯枝末端
萎縮成一滴淚
和你的歎息一同墜毀
那是一個我們完全沒法抵達的地方
在那處
痛苦將被治愈
或無間地翻騰
如同我赤腳踩著熾熱的沙灘
接收雲端以外的私訊
你好嗎
還在蹉跎
還在端視流星的尾巴嗎
在霧一樣的時日
我常常校正膨脹的字體
用指尖安撫它們
碎裂的意圖
灰冷的文字被摘下
成為寒夜發光的詩題
我答應過你的
終將以你為名
寫一本屬於我們的詩集
或許它
一早已被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