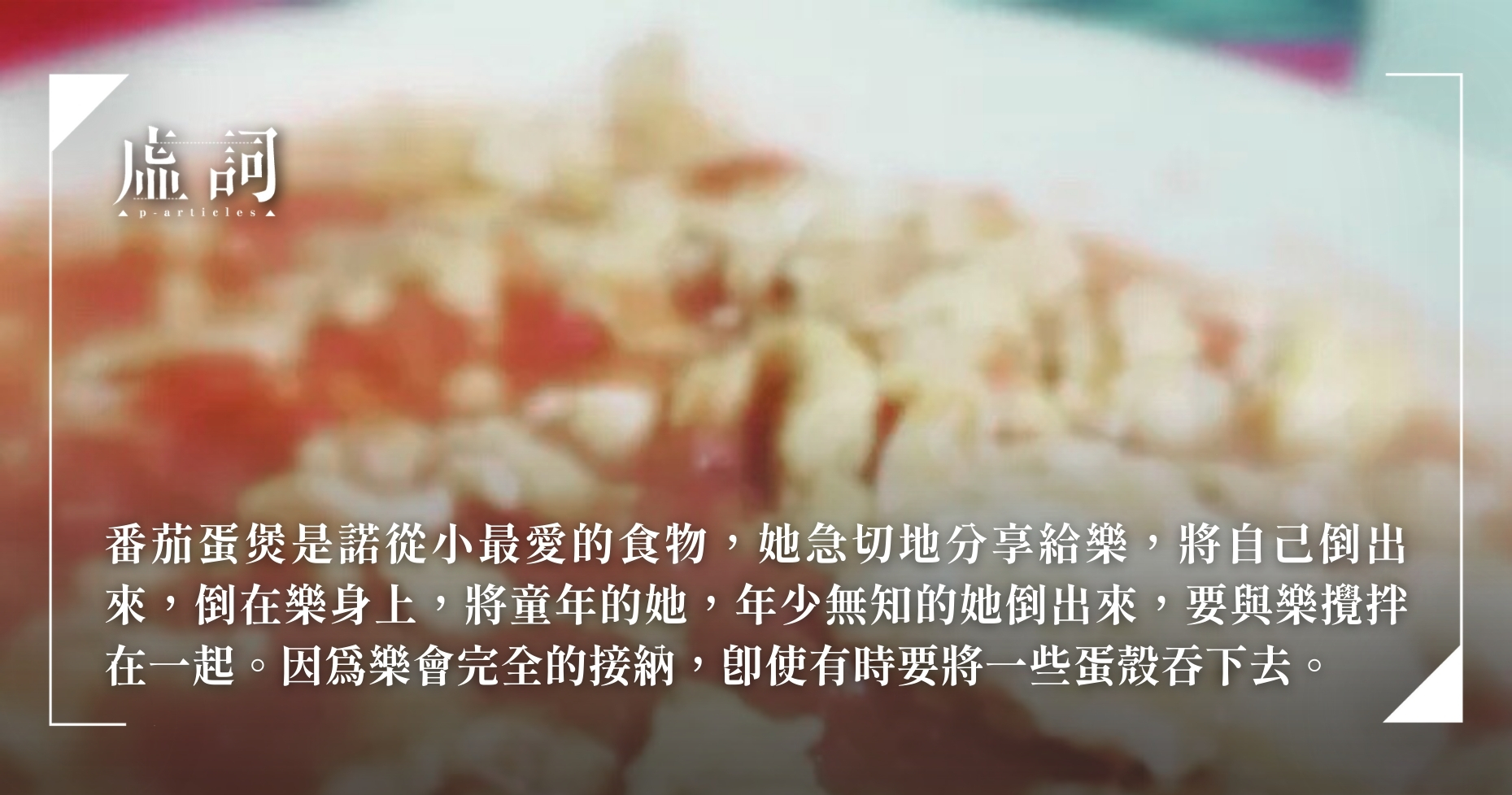【字遊行・米蘭】意大利製造
惟得遊意大利米蘭,先在中日合璧的飯店中嚐意大利的「米」,在米飯之下竟能看見半首七言詩句,還有旗袍歌女獻唱一曲《客途秋恨》,唱出飄洋過海的人間酸楚。之後到訪如雷貫耳的斯卡拉歌劇院,本身有感歌劇院其貌不揚,不過卻在其中聽到韓德爾正歌劇《帖木兒》(Tamerlano)的插曲,仿如替他拭去沾臉的灰塵,才發現斯卡拉歌劇院原來是空谷裡的幽「蘭」。 (閱讀更多)
悼邵家臻
在70年代開始發表詩作的前輩詩人李金鳳傳來新作,悼念上星期與世長辭的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他有如鴿子一般飛回天家,留下了彩虹般的身影,讓彩虹佈滿天空,足以叫留下來的人好好惦念。讓我們在彩虹的彼端再會。 (閱讀更多)
獨力湊仔兩日談
中學選修經濟,學過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較優勢)的概念,意思是即使你做兩件事情都比別人好,也要選最有效益的一件來做,而非兩件都做。 菲傭姐姐快將回來,工作較彈性的我便做了兩天全職爸爸,先說結論,父母貼身教導兒女肯定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但無奈,返工比湊仔輕鬆,所以懦弱的我,比較之下,還是必須收回跟妻子說她工作、我靠她養的戲語。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