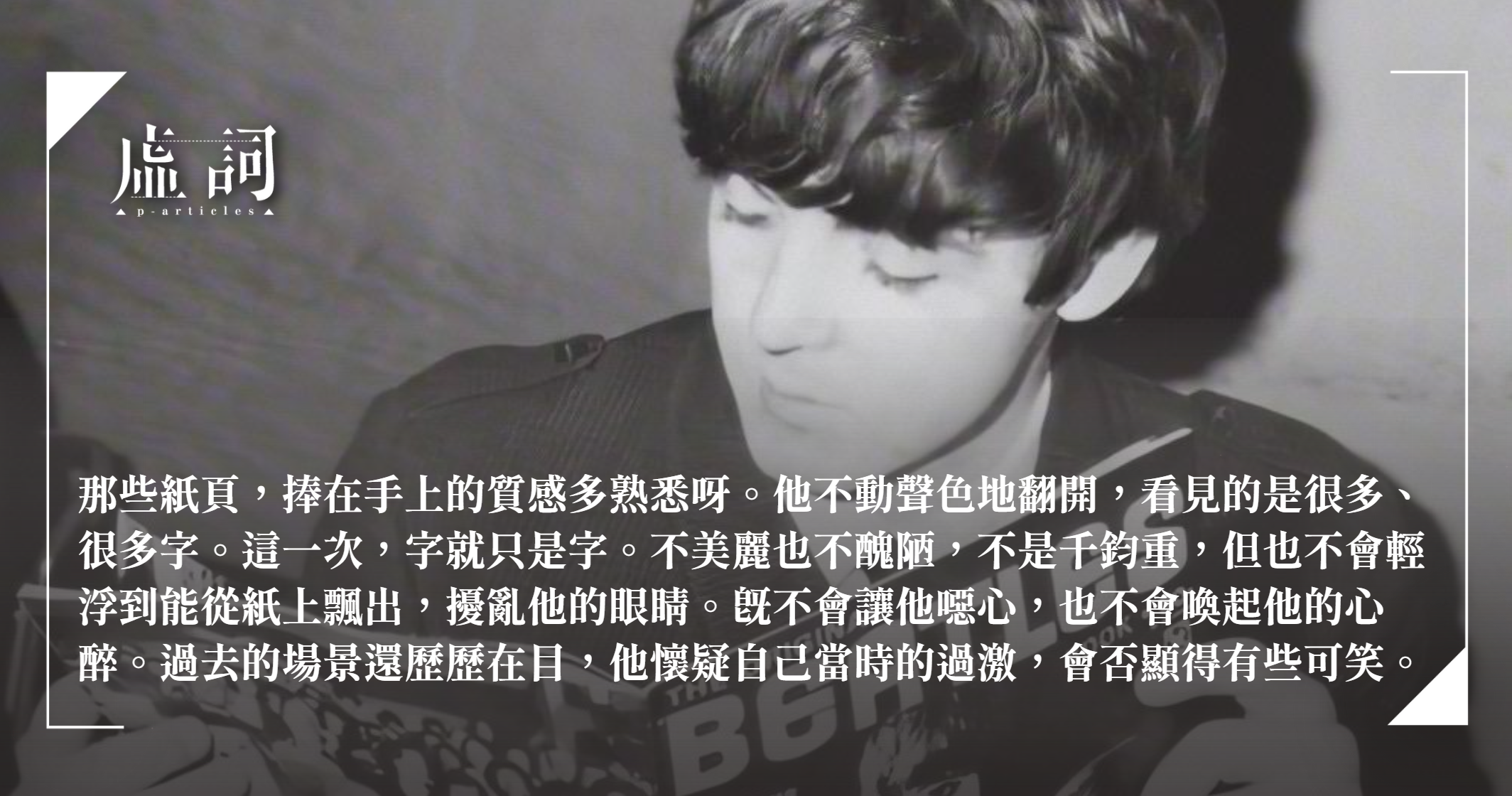【虛詞・◯】懸浮的空心
小說 | by 李曼旎 | 2024-05-18
「假死在曾被處決的秋日。
我們的空心
潔白到像一個剛剛升空的氣球。」
——《正午幽靈》
1.
那個正一點點覺察到自己步入中年的男作家,曾經有過一個很年輕的女友,確切來説,還不到二十歲。那是一個讀文學系的,任性到有些可怕的女孩,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就聲稱自己除了他的書誰也不喜歡看——「與你相比,其他人,還有文學的歷史,都可以燒掉了。」女孩如是說。
這樣近乎於瘋狂的偏愛,曾讓男作家感動不已。而除了這顆偏心之外,他所留戀的,還有女孩那具潔白到不似真實的肉體。擁抱著它時,那份輕盈和柔軟,就好像能和文學中所描述的那種永恆的夢幻融為一體——他太需要一場幻夢了。
人生的前三十幾年如水流逝。物理學博士畢業很久,他始終沒有找到一份可以讓他感到有意義的工作,只是繼續在大學裏,做一份體面卻不痛不癢的研究。同事裏沒有人知道他寫作,當然,即便知道了也不會如何,這只不過是沉重的人生裏,一些最微末的事情。
但第一次在書店的架子上,生澀湧入眼睛的那些文字裏,驟然抓到一本詩集底下輕飄飄署著他的筆名時,他的心還是被揪起來,懸浮在空氣中。女孩也正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首先飄臨的是她的聲音,在書店強烈的白光照射下,變幻得有些發燙:「我知道你,你就是……」
隨之,他的視線也從書脊上飄下,短暫地停留在女孩的臉頰上。女孩也正靜靜地望著他。刺眼的光好像熄滅了一瞬,連同那些聲音一起落在地上,水銀般流動成鏡面。
2.
認識不多時,女孩便搬出大學宿舍與他同居了。於是狹窄的房屋裏,開始擁擠著他的一箱箱書,和她散落在各處的影子,剩餘的縫隙,只夠塞得下一隻某日被撿回來的流浪三花貓。只有他們兩個人時,女孩喜歡赤裸著身體在家走來走去,「在文字裏和文字外都要坦誠相見嘛」,她開玩笑說。
他們那間陰鬱的屋子近乎沒有窗戶,杜絕了被外人看到的可能。唯一的問題是,那隻才結束流浪生涯的貓咪脾性暴躁,每次都蹲守在角落出其不意地襲擊女孩,將她沒有衣物保護的軀殼抓住累累血痕。她疼痛到抑制不住眼淚的時候,男作家也手足無措,只好按住貓說:「你不要去咬她,從那邊過去的不是一個女人,只是一陣白色的幻覺。你去咬她,是會撲空的。」
女孩便被他的這些瘋話逗笑,眼淚在臉頰上打了一個微燙的滾:「你怎可以說我是幻覺?」
「我的意思是,對貓來說,你是幻覺。對我來說……」
他想不起當時剩下的話了。
其實回想起來,儘管他在大學裏的薪水只是在維持兩人一貓的生活後還有些剩餘,絕稱不上奢侈,但那陣時光的確是在他迄今不長不短的人生裏,為數不多的一段稱得上純粹和溫馨的時光。成日悶在屋子裏,女孩鬧起脾氣說,覺得一個人讀書,一個人寫作太無聊,他就找了些本地的朋友,一起創辦了一本文學雜誌。雜誌的名字,叫做「氣生根」:這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一種常見的植物形體,是樹的根部,卻不潛埋於土壤,而是懸浮著暴露在空氣中。女孩點頭贊成他所起的這個名字:
「它和我們一樣,能從明明是虛無縹緲的東西中獲得養分。」
開始只是枯瘦的氣生根,就這樣摸索著生長,想盡辦法攫取養料。最初幾期的稿件幾乎全都來自朋友們,他在空白的文檔上,將蜷縮成一團的文字以合適的形式舒展開來,最後看到它們漂亮地排列在紙上。至於印刷出來以後,有時是聯繫書店,有時,就一本本堆疊在書攤上,以最原始的方式尋找著能夠與它們相連的人。那可是在亞熱帶潮濕的夏天,剛剛印出來溫熱的紙,很快就在空氣中發潮、坍縮了,只好又尋找更合適的包裝方法。氣生根一隻隻繁衍著,鑽進四面八方無形的孔洞。漸漸地,他們有了更多陌生的稿件,來自隱沒在人群中不同的臉。文字像潛行在城市中的幽靈,隱形又無處不在。
3.
「這是你創辦的雜誌沒有錯,可是,它也不只屬於你一個人,不能只有你的主張。最重要的是,你不可以要求我們所有人都為它無窮無盡地投入時間。」
《氣生根》雜誌的第二年即將步過。讓男作家欣慰的是,在本地,有愈來愈多讀者曾聽說過他們,而在這兩年裏,他亦有了幾本新書的定稿。他想,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然而某天一位擔任編輯的同伴,在與他一場關於雜誌的爭執時,説的這些話像破碎的鏡面那樣刺進他的心裏。
男作家覺得有了相當的名氣以後,雜誌的風格便不如開始時純粹,在聚餐時他也這樣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聽到他的話時,同伴盯著盤子白花花的米飯裏,不知怎麼混進去的幾粒砂石,忽然放下筷子,對他說:「我們誰也沒有酬勞,只是想一起走下去,才義務做了這些事。」
是呀。從徵稿、製作到發行,他們誰也沒有酬勞。恐怕除了從最初就滿懷期望的男作家,沒有人想到可以做這麽久,但兩年就這麽過去了。
部分朋友的離去,讓他想起在大學裏時而有教課的任務,他一向對學生放任自流,便有一次,他講到一些和考試無關的知識時,眼睜睜地看著學生一個個走掉,最後竟一人也不剩。如同衰老時,牙齒一顆顆從口腔中鬆弛,老人的臉面目全非。但和教書時的隨性不同,在文學上,他是個太執著,又目空一切的人了,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甚至因為和出版社的理念有所衝突又不願讓步,被移出了他們的書系。此刻自己創辦雜誌,總算可以不管不顧地堅持自己的想法了吧?他並非不珍惜自己的同伴,也不是不理解他們各有難處,可是聽到朋友們抱怨他太過不近人情,他在心裏喃喃著,
「我為文學做出的犧牲,比你們所有人都要多。」
這本來只是說給自己聽的話,也只能説給自己聽。可在一個貓咪熟睡的午後,安靜的屋子裏,這聲音不受控制地愈來愈大,最後索性掙脫了聲帶的束縛,從顫抖的嘴唇狼狽脫出。當時女孩正忙著蹲在地上清點才印出的雜誌數目,聽到他從心底發出的聲音時,似乎仰起頭看了他一眼。
這眼睛還是兩年前的眼睛,空氣中一對圓圓的,受潮的孔洞。
——我只喜歡你的書。
兩年前被女孩一個字一個字吐出的這句話,猶在空氣中飄浮著,還沒有落地,像一個永遠也不會被戳爆變成碎片的空心氣球。然而,也不會沒有盡頭地上升,有一個看不見的天花板圍在最頂部,將他們都困住了。
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倒真想看看,那個空心圓最後到底會停在哪裏。
4.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吧。」
雜誌停辦的那一年,女孩從大學畢業了。曾經他和女孩約定,等她結束了大學課程,他們就忘掉包括文學在内的一切,一起去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流浪。但在此之前,讓男作家痛苦的是,女孩的文學系畢業論文,是寫一位生活在當代,他很不喜歡,覺得遠遠不如自己的作家。
「我覺得他也,還不錯呀。」面對男作家毫不掩飾的輕蔑,女孩支支吾吾地說。在翻閱了她那本論文稿和所引用的文章以後,他終於忍不住對她說,「你喜歡的東西,根本都是不入流的貨色。」
「可是,我也喜歡你……」
她困惑地睜大眼睛。那些稿紙被推開,疲憊地癱軟在桌上,一灘灘等待乾涸的白色。
他很想忘記閱讀那篇論文的不快,於是從書架上抽出一直珍愛的,自己的那幾本書。本行工作之餘,他為它們投入了不知多少時間和心血,儘管未曾得到足夠的承認,他依然相信,他的東西是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可是這次翻閱,他反覆辨認著自己的文字,卻像是被女孩的困惑傳染了,看見它們都變形扭曲,內在的涵義被不可名狀之物嚙噬一空,成了漂浮在紙頁之外的幻覺。曾經讓他心醉不已,或是為了寫出一行,生生要把心嘔出來的句子,此刻都只是——讓人噁心。
他要證明不是他的問題。一定不是。
便奪來舊時一起做的那些雜誌,一頭鑽入那些字的叢中,目光停留在女孩寫的一首詩,又一首,指著它們對女孩,重複著念念有詞,「這些,這些,都是不入流的貨色。」然後輪到那幾箱無辜散落一地的書收藏,他青年時就一遍遍讀過的瘂弦,以致於陶淵明,最後是莎翁、荷爾德林。果然就連那些傳世名句,也都在這時破碎猙獰,沙啞著,念不出一個完整的音節。
如此他反而感到一種報復的滿足。
「既然你們都不認可文學的價值,那我也不認可,這樣就好了吧。」
女孩已經捂上了耳朵。
她聽見長久的,讓人想要與它一同碎裂的嗡鳴。
5.
一種白色的幻覺。
即使開過這樣的玩笑,男作家也沒有想到,女孩會真的就那樣蒸發在感官中。雖然她本來就潔白到好像可以隨時融化。
就在某一個很尋常的午後,門輕輕一晃,貓趴在那上面,發出一聲聲撓心的尖叫,似乎在抱怨自己沒有辦法化作一陣煙,從門縫裏飄出。男作家被貓的哀嚎吵醒時,環顧房屋四周,女孩已經不見了。
什麼也沒有帶走,可屋子就這樣變得空落落的,只有影子漫不經心地懸浮。像有一些東西從空氣中消失。
自那以後,他很久沒有翻開自己的作品,也沒有再看過那些雜誌,就連幾箱藏書,也在後來移居歐洲時分贈給了舊書店與友人。只留下幾本與物理學相關的專業書籍。
異域的生活對他來說不算難以適應:貓可以托運到當地,依然陪伴著他;物理學,那些他爛熟於心的定律,到了哪裏都不會改變;歐洲的植物是另外一些植物,有著不同的根莖,但是看久了,也是一樣的美。就連語言,這滲透進生活中的障礙,他也可以輕易克服:他的外文很好,一直都很好,並且不只是會一種。像他這樣的人,無論移居多少次,都不應該感到寂寞的。
意思是,並不比最開始要更寂寞。
然而流利地用外語交談的時候,偶爾他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個說什麼都有些磕磕絆絆的女孩,想起用母語寫成的那幾冊詩集。莫名其妙地,他總覺得自己最好的部分應該是在母語裏——這和人生一樣沉重的東西,是枷鎖般捆綁著他墜落,還是氫氣球一樣讓他在茫茫的空氣中上浮呢?
生活的瑣碎讓他無暇思考。
只是有一次,旅遊時前來探望的朋友說,我給你帶來了一些東西。
他看見包裹裏隱約浮現出幾塊不厚也不薄的方形。
那些紙頁,捧在手上的質感多熟悉呀。他不動聲色地翻開,看見的是很多、很多字。這一次,字就只是字。不美麗也不醜陋,不是千鈞重,但也不會輕浮到能從紙上飄出,擾亂他的眼睛。既不會讓他噁心,也不會喚起他的心醉。過去的場景還歷歷在目,他懷疑自己當時的過激,會否顯得有些可笑。
男作家的目光就這樣懸浮在紙頁之上,最後,停留在女孩的某一篇小說結尾。他還記得女孩寫完那篇小說,怎樣都不肯給他看,印出來了才告訴他,那是一個以他為原型寫作的故事:
「……他在重力的物理學裏,抓住了一隻文學的氣球升起。那裏看似空無一物,其實卻漲滿了可以讓人上浮的氣體。」
對,就是這樣——
一點點上浮進永恆的虛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