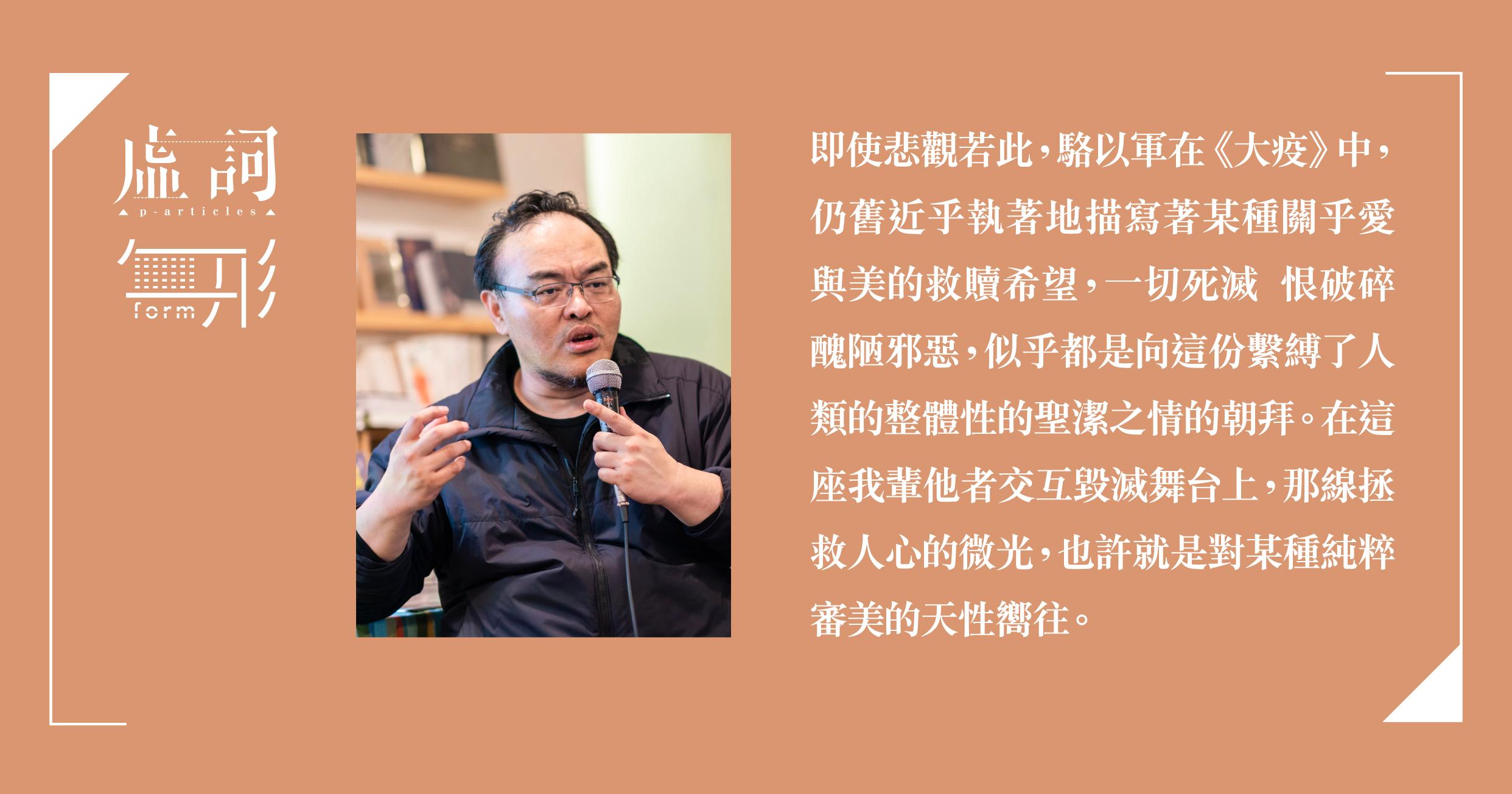末日絕境與太虛幻境──專訪駱以軍《大疫》
駱以軍最新長篇小說《大疫》,有如一洞深不可窺且分歧為無限螞蟻窩的龐複迷宮,讀者隨著小說家的引誘,像是懵懂孩童一路跟隨著吹笛人,舉步涉入那神隱魅現的故事森林。《大疫》體現了小說家最繁華的敘事技藝,以及某種變形的存在主義式的創作關懷,且鞣合了跨領域的知識元素。或可說,《大疫》是一部科幻意味濃厚卻不止步於科幻邊界的作品。而駱以軍動用了小說家所能具備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心智能量,疊加建造出一則則極度炫目而又至深哀傷的小說謎,有心解謎者,且隨小說家之自道,解答屬於各自身靈內部最隱密的慾望、哀告與創傷。
科幻如何做為小說本身
駱以軍近年小說創作,幾乎都摻入了某種程度的科幻元素,但有別於一般科幻文本的寓言排演,就與《女兒》、《明朝》、《匡超人》等同被歸類為科幻書寫的《大疫》而論,科幻即敘事,形式即主體,是曖昧的救贖與末日的絕境。而小說家筆下的科幻思維,在《大疫》裏不斷挪移跳躍的時空維度,教讀者懷抱困惑也滿心好奇。不過,駱以軍反而表示,他從未明確地針對科幻去建構小說情節,然而,他的小說裏確實有著飽滿的科幻因素,這已成為駱氏近年的首置風格,其緣由卻遠自高四重考時,啟發他對於基因列、染色體、DNA等知識興致的生物補教名師姜孟希。因為姜老師的啟發,他靠生物一科奪得高分,考上大學後,駱以軍開始如野獸吞噬肉物般吞食著各種文字與翻譯小說,而其背後始終矗立著一座隱形的結構之塔,塔內的螺旋階體一層層藏納著細胞學與生物學的知識系統,也導致駱以軍的小說存在著某種著魔般的感官性與透視性。「尤其是我讀了波拉尼奧、波赫士、卡爾維諾之後,我特別吸吮這些小說家筆下那近乎顯微鏡、昆蟲學或解剖學般的質地,內置至我自己的小說身體中。我早期曾被人戲稱為『微血管學派』,實際上,我大量耗心去調度、動員的,是感受性的無限變態,包括了情慾、類死亡、空無、虛幻。」在西洋星盤的推算下,駱以軍屬於八宮之人,「八宮之人是擁有極強的對他者的同體感,常導致人我之間分際趨於模糊,但這也就是一種小說天分,對於他者痛苦羞辱惡之感同身受。」
2014年的長篇小說《女兒》,駱以軍耗費極大心力去理解量子力學,並將其納入小說中,「雖然我個人對量子力學的理解也僅止於科普程度,而西方某些小說家早就做過極美的示範。因此《女兒》中那故事與故事的層層疊加,那螺旋塔式的語言結構,也受到我過往讀《紅樓夢》、《2666》時觀見的近乎數學結構的疊加感。又譬如《陶庵夢憶》與《牡丹亭》,這類古典小說沒有那樣的嚴謹結構,但這些作品藉由人生幻虛及境界分鏡去統合、結論何謂真實的存在。我也在某次香港的科幻文學會議上聽見一名中國學者主張:《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座超級VR!當那時的世界還沒有科技、電力、虛擬、數位、攝影,曹雪芹就以文字建構出一完整的層蓋疊加的超級虛擬實境。」駱以軍說道。
駱以軍表示,《明朝》(2019)與《大疫》, 與《西夏旅館》、《女兒》及《匡超人》等花費多年完成的長篇大構不同,後者是跳脫式的、動用截然迥異的心智能量去各自重建,但時機不佳,小說家此時遭逢了健康上陡坡式的衰壞,「這並非誇張,我真的感覺到自己在兩三年前,可能就會走著走著暴斃於半路。」重度糖尿病、失眠與各種藥物,不斷地侵蝕並嚴苛考驗著小說家的身心極限,也影響了創作的節奏與風態,而重新拉回關於「科幻」的思索,駱以軍說,《大疫》其實並無如此絕對而立即的轉調,同輩小說家中,董啟章甚至比他與黃錦樹更早就往科幻邊界移動而去,「而我自己做為小說創作者,曾頻繁出入咖啡館,坐在桌前攤開某個章節或專欄就動筆疾寫,那樣的時刻我腦海中仿若《全面啟動》的開關被捻亮了,這也可能與我多年來抄寫小說的習性有關,我內部擁有一座巨大的各種感知的編排檔數據之海,而《大疫》剛好就是碰上病毒肆虐的時代,我自己也遇到何謂『說故事』?何謂『自己的故事』?乃至於『他人的故事』?就像剛剛提到的,我是命盤落於八宮之人,自我與他人的邊界於我是流動且曖昧且可互溶的,而這個困惑我多年的問題,剛好就被放置在《大疫》之內。」
病毒戰爭與無出口的故事迷宮
就故事本身而言,小說家在《大疫》裏安置了大量的時空亂流與意識的未爆彈,故事裏人物繁多細節龐然的意識亂流,有如深海珊瑚式的無限突觸與搖盪的細肢,每一觸肢的尖端都站著二十萬隻天使。寫作《大疫》時,新聞不斷播報的死亡數字送入眼簾,連帶世界局勢的搖動拉鋸和台灣必得面臨的台海危機,藉由網路肆虐橫行出各種陰謀論與真假難辨的小道情報。快速推進分秒演化的大時代的極速動感,人們發覺自己原無更多知識去面對病毒的變種與蔓衍──病毒遠遠超前了人類的追趕,人類四百年來的科技文明瞬間面臨滅絕恐懼,然而當代高端科技依然不斷進行這場大規模死演的競賽。見證現實局面,駱以軍以《十日談》為《大疫》的結構基礎,「《十日談》是啟發中世界百年黑死瘟疫以來、教會統治崩潰、文藝復興興起的啟蒙作品,我套用《十日談》的結構並注入現代性,就形成了這本『類十日談』的現代小說。」
而《大疫》在故事最末呈現了類似《黑鏡》的急促翻轉,讓讀者察覺到:在溪谷中藏身的這批人,並非僅單純的《十日談》式說說故事,卻是人類所留下的十來隻病毒小人,整座溪谷只是一個虛擬VR觀景,「我覺得這個概念很不錯。即使我們這輩以降,已經不會被現代城市的光炫風景驚嚇,但至少我們可以像波特萊爾那樣的現代偵探,去窺探當代世界隙縫裏暗度的情慾,謀殺,蕩婦,情夫與兇手等等。如果是五十歲以前,我不太可能去寫《大疫》這類型的小說,因為五十歲以前我的心靈工具箱其實不堪這樣巨量的調度使用。而意識與時空的穿梭感,我確實是有意為之,我希望讀者讀到小說中後半時能有不安感──這作家說的故事靠譜嗎?──我其實想暗示這群人實際上是一群病毒的可能性。」
每晚,因失眠與焦慮而掛在網上吸收大量資訊,駱以軍已經確認自身的夜夜死去與重新復生,他形容道,自己的大腦內每晚如同蠢動著億萬病毒,在腦內快速演化短基因段,隨即跳躍死滅而重構為新物種,「我」因而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物種,因此,《大疫》中各人物的故事變形如黏液,爬藤,觸鬚分泌的腐蝕酸液,得以侵入其他人設的故事,產生角色的移形換位,如同所嗑藥後數個夢境的混合溶解流動互滲,在這般情境下,故事方能發生。
前述提及,《大疫》是駱以軍藉由小說敘事重新思索、校正他者與自我邊界的實踐與除魅。經歷過集體霸凌,他至今仍不斷回視當初那堂地下室裏的小說課究竟發生了甚麼,導致後來如此龐大快速如病毒集體入侵的創傷經驗,「其實現在你讀到的《大疫》已經被摘除了六萬字左右,那六萬字可以被切分成二十篇內容一模一樣的故事,附身般不斷地去寫那間地下室的那堂小說課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無法停扼地回視所有痛苦的當下,隱藏的惡意,莫測的人心,「那時,我的心智瀕臨崩潰,處於非常扭曲糟糕的狀態,甚至去做了心理諮商──我不斷思索:如果當初指控我的理由成立,他們甚至可以以同樣手法去指控所有現代小說家,譬如昆德拉、赫拉巴爾、波拉尼奧──所有辛勤蒐集整座都市身世細節而化為小說者,都可以被指控為抄襲。」
《大疫》裏有許多段落,近乎神啟地度入佛經之語,且引用了許多《心經》。當時面臨龐大集體無名匿名的指控與陰謀論,獨自承擔所謂「全世界僅有你一人明白真相並承受痛苦」的駱以軍,每週僅有赴母親家的時刻是,在觀世音菩薩前不斷地念《心經》及「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觀世音菩薩曾立誓渡萬千眾生而救贖世人,他發願道他的頭將碎裂為千萬片,後來當他的頭即將崩裂之際,阿彌陀佛用這句真訣救了即將破碎的觀世音,而『嗡嘛呢叭咪吽』這六字,即是《心經》的總咒,對當時身心皆垮的我而言,每週去母親家,在菩薩面前念經,每每念到欲淚──『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這是菩薩的話語啊!這樣的話語,包納並承接了人類生命中一切感知,也影響了我寫《大疫》時的心緒。」駱以軍說。
人性破變與審美的救贖微光
《大疫》的面世,適逢全球面臨COVID19席捲滅殺人類存在的大浪,疫情時代,病毒不僅侵入人身肉體,也使人心裏某種純粹的善質與信任變調而不復。集體式的抓戰犯的歧視與霸凌,再混以中美抗峙、霸權爭奪、全球化恐懼、烏俄戰爭、台海變局等等恐怖暴力、無數性命的犧牲、大國之間的巨大利益交易等全球局勢,對於未來,人與人之間充溢著懷疑和互相戕伐,在如此時代之中,人類社會是否還存在著救贖或康復的可能?
因《明朝》事件而被集體撻伐、指控為投降主義者、抄襲犯,整個文壇卻無人敢為其主持、發聲,對小說家而言,那成為對於創作與心智的雙重暴力的褫奪,「人與人之間的理性、邏輯、信任消滅了,台灣近三十年現代小說的基本默契消滅了,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價值混淆與困局。」駱以軍說道,近年他看見中國各世代的創作者,對於自身所處的位置無法直敘,得繞著彎以避開那敏感處,因為一旦被針對,創作者所面對的就是人身生命的直接抹滅。「這場大疫犧牲了人類社會數百年來的創傷,做為代價,我們對他者的寬容、包容、想像,因為疫情的快速與無情而消失。這世界自從疫情發生後,那種二戰後所建構出來的左派的的對他者的尊重與人文精神,被自我恐懼的擴大與生存感的爭奪所取代,COVID19摧毀了冷戰後人類文明的寬容性,這是極端不幸的文明崩壞。」
即使悲觀若此,駱以軍在《大疫》中,仍舊近乎執著地描寫著某種關乎愛與美的救贖希望,一切死滅讎恨破碎醜陋邪惡,似乎都是向這份繫縛了人類的整體性的聖潔之情的朝拜。在這座我輩他者交互毀滅舞台上,那線拯救人心的微光,也許就是對某種純粹審美的天性嚮往。
駱氏小說中沿途瀰漫的迷魅靈光,極多是對純淨無瑕的少女之美的頌歌,亦並置了雄性與暴力的描繪,這種光譜上的極度拉鋸與對映,或許來自小說家所置身的臺北這座小碼頭,在近五十年間所吸收的各種摩登文化,從東京摩登、上海摩登、美兵摩登、六○年代搖滾與好萊塢文化,一路風靡至九○年代的巨大的消費文化與資本主義的甜美和創傷,如極暴烈又極精妙的雙生之身,「我們那世代見證過解嚴後的都會的世紀末華麗、也品嘗過最好的時光,但就像年輕時飢渴吮讀的《百年孤寂》等小說,當時並未意識到那是整個拉丁美洲的苦痛絕望,是人類歷史上的彼此傾軋絕滅,是預先毀滅、剝奪整個民族未來的幸福與想望,當文明的可能性被預先剝奪後,人就像剪去肺葉的鳥,失去了再度翻身立足的機會。」駱以軍說。
如今,被病毒驚嚇、恐嚇的人類社會,已然失去了某些至關鍵之物,駱以軍認為,這幾乎已被恐懼與貪婪所撲滅的人心微光,乃是「審美的降格」,「我在寫《匡超人》時,開啟了粉彩瓷、壽山石的著迷之路,這兩年,每在我心神低盪的最最痛苦的夜晚,甚麼理論、文學,都說服不了我自己心中那坎,但當我摸著那幾顆我最珍愛的壽山石,在燈下獨酌著石頭色澤的過渡、變幻、質地、丰采,那像女體般的美好透澈,如某少女臉頰一紅的微妙幸福時刻,透過石頭讓我全景式地感受、觀見,而《大疫》裏所寫的那些茶的極度講究與細節滋味,則是在楊澤老師的引領之下,我睜開另一雙眼睛、觀視昭和町裏或路邊常見的品茗老者的經驗──每一片烘乾的茶葉在滾水中花瓣般展開,像張愛玲筆下的少女孔雀展翼般綻放那癡情那心機那性情,一注茶的感覺便有了千滋百味。我想,最終能拯救我們的東西,或許就是來自人性裏對美的最原初強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