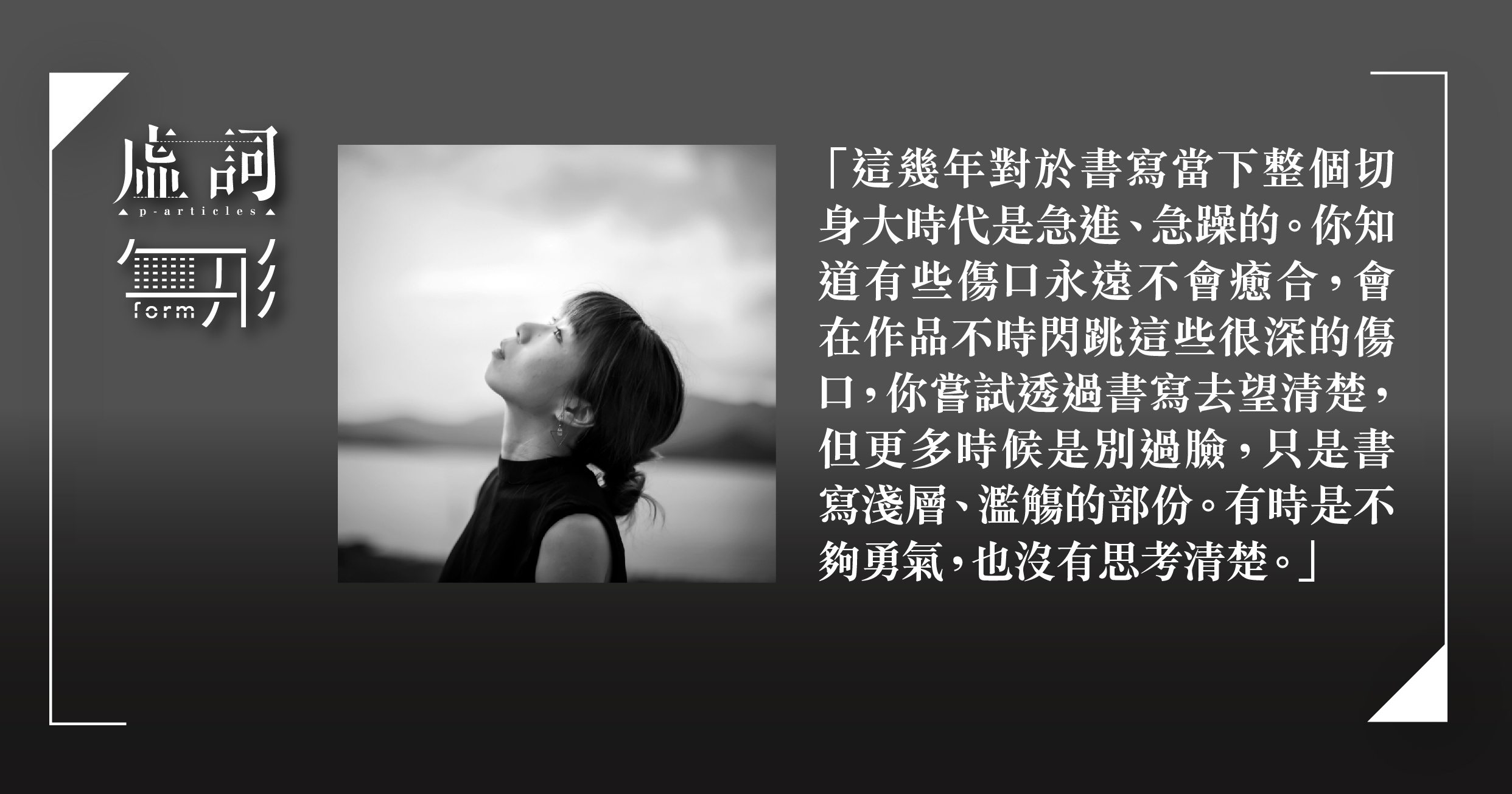【無形.某種通行證】在陰影覆蓋下,走過虛妄與窄路 —— 訪余婉蘭
早在余婉蘭的首部小說集《無一不野獸》,作者已經展現了自己廣闊而獨特的文字世界,然而,今年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卻不再是小說,而是詩集《島之肉》,像封面那顆以羽毛、樹木與人臉縫起來的心臟,把零散的血肉結集成詩。沒有某種堅定信仰的人,幾乎無法在這樣的時代裡繼續寫作,但對余婉蘭來說,無論寫作還是信仰,都是生命中難以擺脫的考驗。
余婉蘭打趣提到,《島之肉》的出版契機,原來是年前投稿到台灣周夢蝶詩獎。獎項落空,卻反而促成了這部詩集:「詩獎本身不是以單一作品參加,而是用一本詩集為單位,所以我整理了一些束之高閣的詩作,其實加加埋埋已有六十多首。當時沒做過什麼編輯功夫,也沒有詩集的概念,就這樣一整批寄過去,最終入圍了決選,而其中台灣詩人羅智成先生又在總評提過對這本詩集的欣賞和鼓勵。」雖然落選,但畢竟已整理了作品:「似乎有點信心,不如把它出版。」
企前少少,進擊一點
過去余婉蘭都比較低調,較少公開發表作品,對於出版,她自言也一直佛系隨緣。「以前我沒有太大所謂,反正作品寫了出來就等於存在,功德圓滿,出不出版都得。」轉念一想,她接著說:「但近幾年,對於出版這件事,我變得更『進擊』了,寫好作品會主動找出版社,以前是絕對不會的。其實以前我都很少做訪問,談自己的書。」她仍覺得礙於性格問題,自己聲音微弱,但用創作表達自己想法的慾望變得更強烈:「儘管我是偏向不活躍,也不熱衷用社交平台,但看見身邊其他本身比較低調的文字人,例如李顥謙,如今也開始有所改變,大家變得願意企前少少發聲,為自己爭取出版和創作空間。」
「書作為無數個時代的盛載物,紙是很脆弱的,木的性質,火燒就變灰,但樹比起幾代人更長壽,而圖書館是一直世世代代存在,只要有人,就會有圖書館。」抱著人不在、書還在的想法,余婉蘭開始肯定了出版的價值:「是因為書對於時代的必要性,或者是對於書這個載體的信任和尊重。所以近幾年,只要能寫下去,就希望它會變成書,從私密至公共而公開的表態,為這地方這個時代留下見證、想法。」
整理詩作期間,發現水煮魚出版的關天林跟自己有類似的想法,她便增刪了一些作品,再一次跟《無一不野獸》的設計師 Core 合作,完成了這部「偶然」得來的《島之肉》。「雖說出版艱難,但慶幸他和水煮魚願意幫忙,可能也是基於一些時代責任,我們都有些預感,是出得一本得一本的了。」
不是揚起抗爭旗幟的詩人
在《無一不野獸》和《島之肉》兩書之間,香港社會經歷了巨變,從蒙面抗爭到蒙面防疫,要思考故土的消失、鄉愁,或思考這座城市的命運:「這些題目,伴隨更大的崩塌消逝,過渡到一個全新的創作緯度。」余婉蘭坦言:「我自己都感受到這幾年對於書寫當下整個切身大時代是急進、急躁的。心裡面明明許多內部狀態未好好疏導,你知道有些傷口永遠不會癒合,會在作品不時閃跳這些很深的傷口,你嘗試透過書寫去望清楚,但更多時候是別過臉,只是書寫淺層、濫觴的部份。有時是不夠勇氣,也沒有思考清楚。」
余婉蘭形容,急於書寫的衝動換來更多內在掙扎,要容讓自己對書寫抗爭的逼切性,然後保持距離。「有些事情比起你急於表達自我是更重要的,有時我們會高估、濫用文學書寫那些『透視本質』的能力,變成了一種姿態。」
「我只知道還有事情想寫,但不一定是非抗爭文學不可,也不一定跟社會運動直接有關,它是重要,但不一定由你書寫,它自有相應的人去寫。近這些年,很多人努力找落腳點,暫時站得穩妥,但很多人都是咬緊牙關試圖活得稍微好一點。我也在摸索,學習如何繼續活下去,寫下去。」
於是余婉蘭選擇了出版詩集,《島之肉》就像對夢魘的描寫,也像其詩句,意象明滅之間,是一場召魂法事。一般認為,詩集會流露作者較私密與隱晦的個人情感,但余婉蘭有不一樣的想法,如她後記提到,詩是「比母語更接近內核的聲音」:「相比於寫小說,我覺得自己透過詩的聲音更大,無論寫得幾迂迴,在情感上,卻是更直接到達。」
綜觀這兩年,都有不同世代的香港作者陸續出版個人詩集,像陳子謙的《鬼火與人形》、李顥謙的《夢或者無明》、嚴瀚欽《碎與拍打之間》,好像大家都選擇了在這個時間點將詩作結集,變成某種具有共識發聲頻道,與世界接軌的媒介。
「或者你會覺得寫詩能避開潛在的危險,或者一些審查,但詩的本質並非如此。」余婉蘭續說:「於我而言,詩的隱晦和私密未必是作為對抗手段而產生,寫詩牽涉深遂的內在之眼、內在之聲音,而詩這個載體,它本身就是如此無以明狀,隱晦與私密,有其自由,獨立特行的特性。不論你寫什麼,它的語言和取向,就有一種對抗主流聲音的意味,是一種邊緣的異聲。」
接著,余婉蘭轉而提到其他同代詩人:「我有看過李顥謙的一些訪問,知道他很多詩集都是在社會運動期間完成,但我不是。我未必做到那種揚起某類抗爭旗幟的詩人。或者說,發聲言說是基於你的情感需要,而你選擇了寫詩,在這個時代,這種感受很強烈,但對於每個人的效果不一。」她說:「每一次大型的社會抗爭事件發生,我自己都有種很明確的意識,非常抗拒用作品去做回應,譬如那天經歷過什麼衝突場面,然後回去要寫一首詩,我不是這種運作方式的。那些水深火熱的時刻,或者置身大局之中自己什麼也不知道的時候,我都很少、幾乎不會寫詩,最多只是寫隨筆和日記作私人記錄,儘管每次去到現場,很快就會落入記者、寫作人那種旁觀游離的視覺。但我過去大部份的作品,都不是與社會、政治環境很大的關連。」
事實上,詩集《島之肉》裡面,只有點題作〈島之肉〉和〈少年〉是唯一兩首,於 2019 年社運時期當刻所寫。「兩篇寫下的時間點都是真切地發生一些事件,是一坐下就自然地開筆寫,很快地寫出來了,沒有思考太多倫理和糾結。只是想抒發、記錄,過濾一些雜亂的思考,寫完之後也沒再修改,是比較真誠的面貌。」而這本詩集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寫在社運之後、所謂新時代的香港:「離開了社運最熾熱的時間點,我覺得自己在這些位置,不遠不近、若隱若顯,情感上的安全距離下,我才會覺得是一個適合寫詩的距離。如果現在回憶到自己曾在當刻現場想過寫詩,我猜自己會反胃。」說著,余婉蘭答得十分平淡:「或者這就顯示了我不夠勇氣。情願擰轉面,不想把它看清楚。」
當然,詩作裡好些篇章亦隱含了一些深刻的社會觀照,並非搖旗吶喊,而是像暗號。「那些暗號,或者觀照,其實是集體傷痕的一種,也有包含對未來希冀的部分,是你有我有的東西。我始終覺得文學創作不一定需要在巨大的時代、政治名目之下才有價值,社會、政治、時代,意識形態,它們都不是最重要的,就像董啟章在小說《愛妻》裡說到『生命小說』,寫生命的作品、人的作品,需要時間、年歲和歷練去蘊釀。而那些大名目只是背景,但非中心。」
寫詩、小說與學佛
訪問前,誤以為過去兩三年香港社會的改變會是余婉蘭寫作心態轉變的最大關鍵,但正如剛才所說,政治、時代這些大名目只是背景,不過剛好應驗了她自身的內在變化:「應該是在 2018 年,其實已在經歷一些心境的轉變,而且預感到即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年,余婉蘭辭職成為自由撰稿人,其後信了佛教,開始憚修。
當然,早在《無一不野獸》看到的作品母題和句語之間,都不乏關於生死、血肉、夢與靈性的意象,余婉蘭形容:「以前我認為自己會是個沒宗教信仰的人,或者叫無神論者,傾向泛靈論,相信萬物有靈。我的很多作品都有此傾向,人類不是存在於宇宙、世界的唯一中心,尚有不少可知,或者不可知物的存在。」

在《無一不野獸》和《島之肉》裡,同樣輯錄了組詩〈瑪尼大海〉,這個自創的空間概念,或者便很接近余婉蘭透過作品傳遞的一些母題。「因為水是一個通往意識的媒介,當初我未有信仰,只覺得是跟神話的元素,潛意識與意識之間尚未分離清楚的混沌狀態有關。」
為《無一不野獸》寫推薦序的崑南跟余婉蘭討論過,認為瑪尼大海指向一個很「佛」、很「藏」的世界:「我沒有想過,純粹是把一些心眼見到的想像建構出來,以為那些都是集體潛意識,神話、古老世界、人類共有的想像。其實《無一不野獸》亦有一些佛學殘影,信仰思考,如思考愛情幻象,輪迥,痛苦與執迷的無明,基督教的聖潔、罪性等。但那時沒宗教信仰的知識和正知正見去理解自己為什麼有那些構想。」後來認真接觸佛教,余婉蘭覺得跟自己過去的許多想法都接近:「例如只要你留在人間,就會痛苦。但佛教信仰在我本身這些困惑、絕望的看法之上,又給了我一些新的想法、出口。」
像余婉蘭覺得比起小說,詩集《島之肉》是更直接、接近內核的聲音,回看她的小說《無一不野獸》,其實寫得更像詩,具備了詩的隱晦與抽象:「可能有些追求小說技法的人會不喜歡我那些像旁門左道的小說吧。我享受自己在底層幽暗,站在那個位置成為觀看者,想用小說在泥沼之中找到答案。就是這種慾望驅使你前進,用有限的肉身追求無限感覺。」
但余婉蘭認為,自己對寫作已有了不可逆轉的改變:「那種無限的慾望,原來你無法抵達,只會愈走愈窄。其實是堀頭路,愈找愈黑。我想自己未必能夠再回到(《無一不野獸》的)那種狀態。」
或者,先入為主覺得取而代之的宗教信仰,將會成為余婉蘭克服現實、繼續創作的新路向,但她就著這一點認真安靜了許久,怕自己說得不夠清楚或產生太多誤會,然後說:「寫作與學佛的某些本質是有所違背的。」
沉默過後,她解釋道:「你以為自己的文字能夠反映真實,覺得這個世界就是以你所相信的面貌呈現,讓自己沉進裡面。你會不斷相信、製造一些自己無法判斷真偽的幻覺,寫了出來讓它看似存在,讓自己和別人都去相信它。但這個問題我還未想清楚。」稍頓,余婉蘭提到寫作與佛教的生起概念:「生起就是所有煩惱的來源。如果不寫,我覺得一切便不會有生起,因為不斷製造生起的過程裡,你會相信自己創造出來的痛苦是真實存在,到頭來愈是將自己困住。」
有了宗教信仰後,余婉蘭一邊寫作,同時一邊開始禪修:「是感覺到自己的心仍未開放,執著太多。有編輯問我禪修之後對創作的影響,我想自己正在經歷這個階段。」她接著說:「禪修只是令我看清楚自己的真正狀態,不代表我因此得到解脫,獲得歡喜。問我是否信佛之後無法繼續寫作 我,也不是的,但創作期間會讓我多想,自己為何寫作?對我來說,寫作不再只是創作,還有其他,到底那是虛妄,還是製造幻覺令自己痛苦?我想自己接下來會有更多改變。」
寫作是條窮巷窄路
寫作說不定真是一條自尋痛苦,將自己困住的窄路,也可能是一條窮巷。有趣的是,余婉蘭沒因此想過放下寫作,反而用了更多時間,將寫作變成更純粹的生活。香港的文字工作者普遍身兼多職,文學創作以外,若不是從事教學或藝術行政工作,便多半是在生存環境愈來愈窄(現實意義上的窄)的傳媒行業打滾。
寫作煩惱何其多,余婉蘭難得苦笑:「我是從 2018 年 7 月開始成為自由工作者,最初的想法是想寫多一點深度、長篇的專題,也希望留下多點故事和紀錄,但從採集資料到採訪都佔用很多時間,付出與收入未必成正比,感覺是愈寫愈窮,愈寫愈沒有時間創作。但我想只要銀行戶口還有錢,都會繼續這樣生存下去。」
離散如潮,不少上一代作家都決定封筆,隱世或回歸山林,余婉蘭則反而看見不少年輕作家跟自己做著相同的事情:「或者是大家都不再相信這裡還會有長遠安穩的寫作模式了,我也想再嘗試下去。」
在社會紛亂與內心無以名狀的掙扎與頓悟中,余婉蘭卻提到自己接下來的第三本書《我是嬰》:「因為家中有一個嬰兒的出世,更是在一個所謂禍福難料的亂世,步入擦槍走火的戰爭年代,我開始想書寫生命的誕生,如果之前我是寫陰影,背面,陰影性質的東西 —— 他者、死亡、夢境、潛意識、女性某些經驗、陰影覆蓋之下的人,現在我嘗試寫叫作『月亮、太陽』本體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