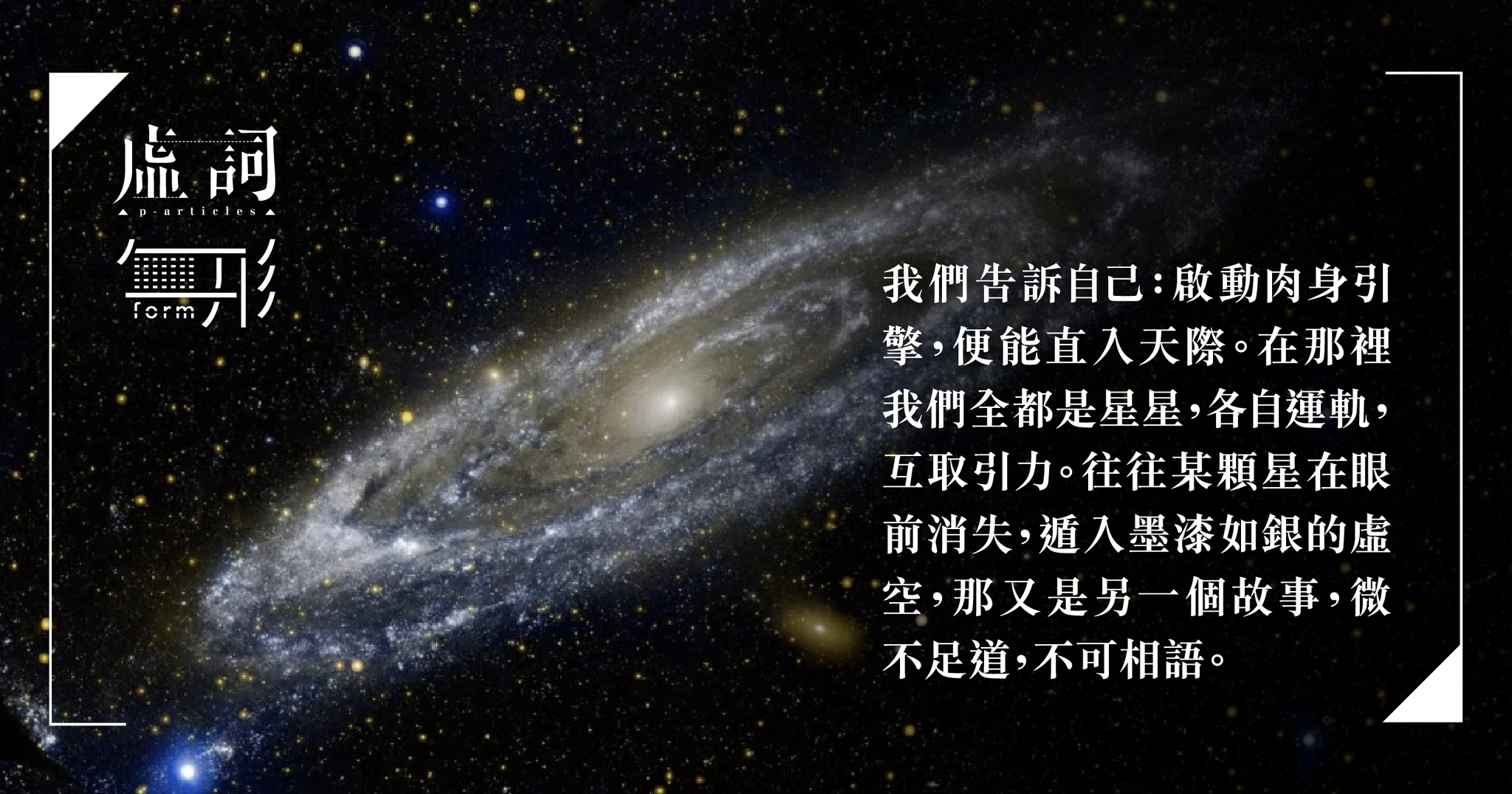【無形・每次冥王星靠近的時分】肉身做星
不知是何故,我竟突突地想起:我的身體上有著兩顆冥王星,一個紋在右耳骨廓,一個紋在右手小臂內側。
冥王星。天平動。進入水瓶座之月。春天。我只能說從春初開始我便過得一片混亂,生活不斷斷岐出我預行的軌道。我認識的陌生人比我喝過的酒更多,比我抽過的每支菸都更嗆濃。菸酒傷身,但愛人更如何?面對初識的好人們,我將他們一個個都視作我心愛的人那般對待,呵護地將男人的頭顱抱在胸前,用我的溫暖妥貼他的溫暖。
即便只有一夜,一次性的歡愉消耗,因為只發生過一次,那就成為在原地原夜恆質不變的畫面:燈光昏黃的房間。掛滿布畫的牆壁。向訪客撒著嬌不停嗅著氣味的貓。那愛撫貓背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們。那親吻我肩臂紋身的嘴唇們。
畫面重複,跳躍,我閉上眼。
臨近38歲的那個晚上,我撥了通電話給好友C。電話裡我胡亂一氣地哭,哭我一事無成的上半輩子,哭我即將一事無成的下半輩子。
許多人曾懷著溫柔告訴過我:妳不是一事無成的,妳寫過那麼多美麗的字,它們不是一事無成的。
但我是誰?我還能做甚麼?我還能愛上誰?我的心荒蕪我的喉乾渴,吞下一支又一支香菸,煙火經過肉體篩落後的殘霧,是黑空裏遮月的白手。
於是我將愛切分成了許多尖錐狀的甜蛋糕,來者得贈一隻。人們進入我一如身陷於愛的糖水奶油,我因此是一名眼睛虛無的泛愛論者。
於是妳的蛋糕一隻一隻地被拿捏,咀嚼,舔舐,吞嚥。這其間並沒有人愛上妳。妳看著他逐件揀起地板上的衣褲,一件件不疾不徐地合身套上。妳知道又是說再見的時刻,一切充滿暗示,暗示教妳猜疑又教妳寂寞。妳將貓低低地摟抱著,燒完一根菸時那人起身也走了。
他們掩上門離開,這時候天空總是出現兩顆冥王星,像是召喚著妳身上的兩枚星體刺青,月夜下那兩枚紋身竟兀自地微微灼痛起來。妳感到倦怠但體內還殘存著激情的興奮──妳覺得自己性感嗎?不妳且甚麼都不真正曉得:界線在何處?妳又在哪裏?貓依偎著攀上來睡在妳的肚腹上,那裏面有著另一顆蠢蠢欲動的心臟,蔭著暗暗的光如世上一切懷著秘密的心,見不得人且無可觸及。
但妳並不總是被周全對待的。整個月下來妳吃了好多藥,月經紊亂起來,妳想這就是愛的代價了:有人做出選擇,誰就必得承受。吞完藥妳盯著桌上網拍購來的小夜燈,玻璃球裏有一整座太陽系。我數了數:僅有八顆星球,比右手臂上刺繪的太陽系少了一顆。
少了一顆,那必是被除名的冥王星了。妳暗自地感到不祥,於是把那玻璃燈給捻了,妳還在妳的星系裏暈暈悠悠地兜轉著。
***
小時候我曾經著迷於星座,那時候書店暢銷著生日書,我攢著零用錢興沖沖地選了自己生日的日期:一本薄薄的精裝硬皮小冊子,銅皮紙彩印,說著性格特質幸運色幸運石等等,那生日冊子幾乎被我翻得頁頁捲起邊角,擁有它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特別的人。好似全世界只有我是紫水晶的代言人,好似我神秘而擁有靈性。
那樣的小書風行過一時,幾乎每個學生手裏都揣著一冊。我們就是從那時起迷上了無邏輯僅有直覺與感情的許多預言,這些預言一直流行到今天並沒有變。
我想,我們從幼年的時候開始,就被命運下了盬。──幼小的我們是多麼願意想像未來啊。後來,當我已經不再用星盤去命名自己與周遭的人,卻每逢談戀愛,在心底有了另一番定論:巨蟹男垃圾,獅子男難搞,天蠍男浪蕩,水瓶座的女人怎麼樣也難做人──即使我從未認真研究過月亮上升太陽,但水逆基本上是無從躲藏的。
水星逆行,諸事不宜,最適吸貓。
凌晨三點,我暈暈晃晃起身如廁,貓在枕上睡得黑甜。我打開筆電,螢幕亮起,鍵盤滑鼠捻捻,音樂從我的迷你音響遞送入虛空,像黑暗的房間裡一組發光的心器,兀自嚶嚶悠悠地哼著宇宙的心律。
這便是我經常的生活。有時床上有人熟睡,有時床是空的,只賸我以肉體重重織打過的被褥形狀,是一隻柔軟蜷曲的孤獨繭。我洗臉,服藥,按部就班地寫字,間或不斷地安撫貓的短咪長喵。這樣的時候我感覺快樂,愛人早已不再愛,我所愛者僅有寫作與貓咪。我輕柔捻著鍵盤打填格子,直至清晨暨臨有微光探入窗布,日尚未昇,日與夜纏綿交媾的分際整座天空瞬眼滿是鳶尾淫淫的紫光,天邊遠遠處有孤星仍然展示著它的芒刺。
昨夜呢──也許造了太多愛,也許飲了太多酒,也許抽了太多菸,也許做了太多孽──隔晚如隔世,昨日種種我皆一律拋諸腦後,今天便是一個新的好人。我打亮書桌邊的立燈,日光混合不知名的鳥聲,短短一陣吸引貓在窗前窺望。拖地,鏟砂,洗衣,餵貓,喝水,吸菸,有時踩著節奏向哪裡走,走去一杯冰沁的黑咖啡,一碗盛雪的菸灰缸子,然後枕著烈烈的白晝睡去。
***
且讓我說一下,關於身體。
遇見N的時候,我正要開始領略年輕肉膚的美好。值得探究的是:就算是年紀小我整整十多歲的男孩子,也對我感到奇異的興趣。
而N是第一個引發我巨大慾望的少年:青春的巨大的賀爾蒙啊,我貪婪地吸吮著男孩散發溫暖香氣的身體,纖瘦而結實的四肢,削瘦筆直的腰腹曲線,硬挺而炙手的勃起──
我第一次見到,某個人的身體可以如是燦爛豔美如初昇朝陽,他在我身上熠熠地發光,溫柔地動作,溫煦地高潮。我舔舐他頸窩處薄薄的汗水,那是世上最甜美的蜜糖。
經常(往往在白晝),因睡眠中斷而清晨醒轉,沖一場晨澡後,一股奇異的感受湧現:剛剛洗過澡的這具肉軀,肩乳鬆柔臀腿熟軟,髮梢濕漉且猶自蒸散著殘餘的水氣,物質的乾淨卻亦凸顯了另一部分的骯髒。我知道自己是個齷齪的女人,偏偏我不曉得這一切何時結束。
或許,或許我們都不想結束,或許我們就是該這樣繼續下去:夜夜歡愛,飲酒服藥,毫無忌憚,無以節制。或許,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我成為某一些人心脈搔癢時亟欲吞食品啖的一種食物:一片甜派(可能)?一張淋浸奶油與藍莓的熱脆鬆餅(亦非不可能)?或許,或許正是因為如此,我給過他們營養,我的身體所蘊藏的柔軟與豐腴,恰巧是他們需要的熱量與水糖。
我將其視作廣闊而輕薄的愛,如是,我也因故為眾生祭獻了許多愛。汗水與唾液混合為這份愛的氣味,同時摻著一股一如我記得某類蟲虫會特地從腺體分泌出蜜味,那本是引開天敵注意力的逃生之道,此刻成為我吮取吞嚥的隱喻的愛液。
我們告訴自己:啟動肉身引擎,便能直入天際。在那裏我們全都是星星,各自運軌,互取引力。往往某顆星在眼前消失,遁入墨漆如銀的虛空,那又是另一個故事,微不足道,不可相語。
我以肉身做星,等待灰飛湮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