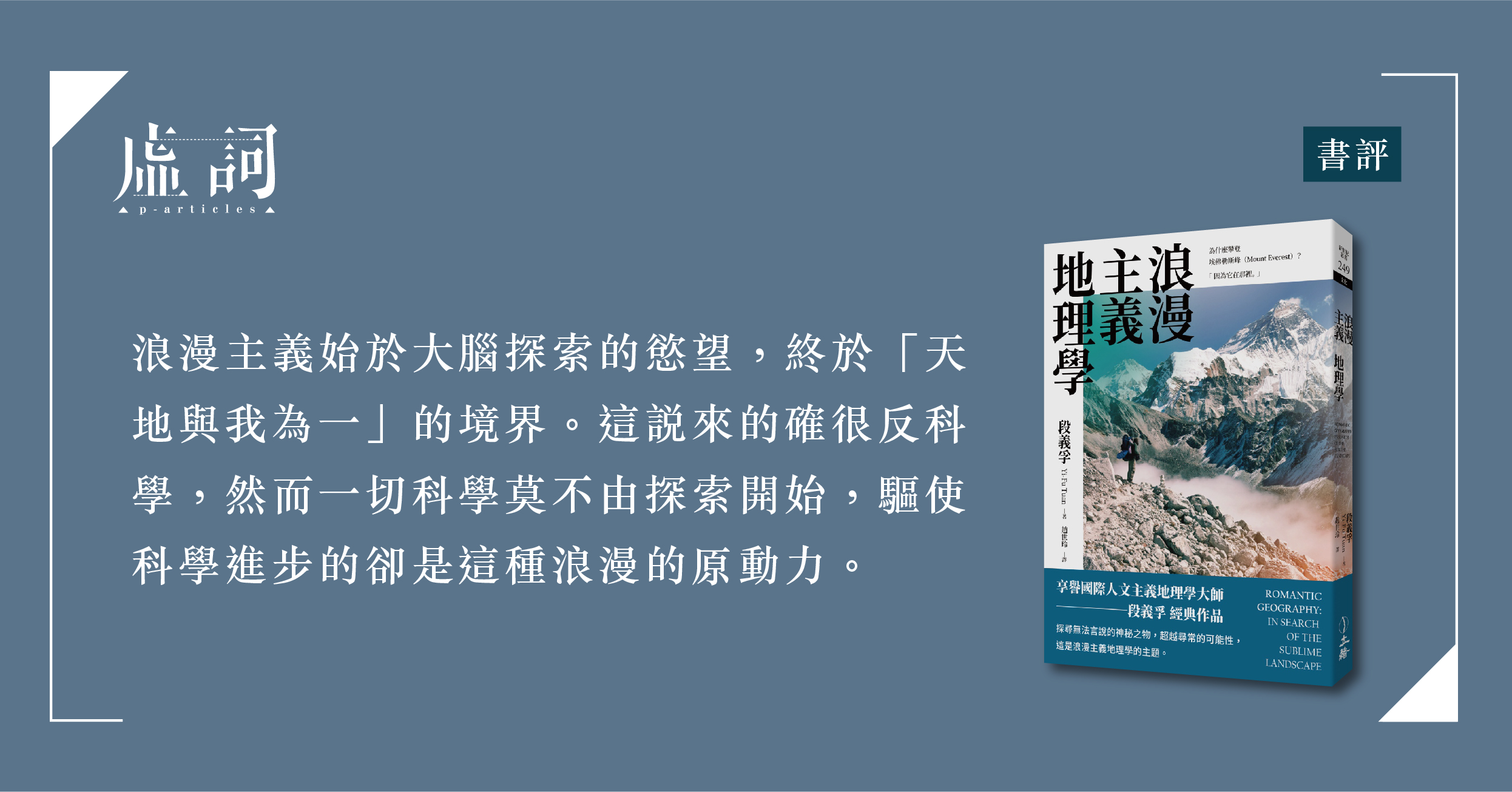如何浪漫地離「家」出走?——段義孚《浪漫主義地理學︰探索崇高卓越的景觀》
人總是喜歡奇異、異質的事物,不管那被稱為「恐怖之美」、「詭艷之美」抑或「高貴之美」,也不理衛道之士如何譴責這些驚奇駭俗的事物。這就是為何我們為「浪漫主義」深深著迷。德國思想家暨尼采及海德格傳記作者薩弗蘭斯基,在其著作《榮耀與醜聞︰思考德國浪漫主義》中,發現浪漫可以是對一個新開端的激情,如盧梭去萬塞納途中,在路邊樹下經歷靈感迸發的時刻;也可以是重建精神的盼望,如浪漫主義思想家赫爾德;它可以對於瞬間、恐懼和決斷的崇拜,如海德格、齊克果,甚至曾批判浪漫派的卡爾.施米特,都強調決斷的重要;它也強調超越,如十九世紀德國畫家弗利德里希一幅最著名的畫作,就是一人登上山頂觀看雲海的景色。但簡單地說,浪漫主義者總是要打破沉悶的日常規律,反對機械僵化的理性思維,認定想像力是最高精神並聲稱要恢復它的魔力。浪漫主義者歌頌夢幻、生命和神話,因為這些都與平庸市民世界中的經驗、生活和現實相對立。
浪漫主義可以放在不同的領域︰個人的浪漫主義,可以是藝術家和詩人一次逃避或凌越現實的旅程;可是一旦放諸政治,就會變質成危險的極端思想,如果政治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合流,又會衍生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這些消滅議會政治並任意挪用法律行使獨裁統治的災難。作為學術思想,浪漫主義可以清新那些久被實證科學僵化的腦袋,它的唯一問題欠缺論證。在地理學方面,隨著對傳統科學地理學的挑戰,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強調人類如何以主觀視角看待地理才是更重要的課題,他那本著名的《逃避主義》就將人類文明的地理景觀視作人類要逃避充滿危機的大自然,他的近期著作《浪漫主義地理學》則從文明回到大自然,看文明人視角下的大自然世界。
《浪漫主義地理學》不是一讀就令人產生棒喝感的書,書中內容不難理解,論述看似散漫,作者並沒有以清澈邏輯建構出理論,反而較像某種運用現象學論述方法的著作,就像巴舍拉書寫《空間詩學》一樣。另外,即便是作者本人也承認,「浪漫主義」和「地理學」兩者,根本搭不上腔,前者是虛構的、務虛的,後者是現實的、務實的。段義孚坦言受到艾可《醜的歷史》啟發,但不想只面對陰暗面的事情,於是就以既有光明面又有陰暗面的「浪漫主義地理學」作為素材。仔細閱讀此書的讀者不難發覺,作者希望一步一步建構出這種「浪漫主義地理學」,而且反對那些談論環境論(environmentalism)、生態學、可持續性,作者將這些講求實效的反浪漫流派稱之為「家政學」(home economics),詬病這些流派「無法使人激情澎湃、精神振奮」,而他的「浪漫主義地理學」就恰好相反。
不能重返的大自然
拿著薩弗蘭斯基和段義孚的書一起讀,基本上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浪漫主義是高度文明社會的藝術家、作家、思想家和學者觀看世界時的一種復古觀念,其始作俑者盧梭所歌頌的高貴野蠻人,或與「浪漫」(romantic)詞源相關的羅馬人(Romans)或流行羅馬式(Romanesque)風格或羅曼史傳奇(Romance)的中世紀人們,都不可能想到浪漫主義。相對於古代人渴望免於自然災害的文明渴望,現代人渴求浪漫的願望就是一種逆向的自我逃避︰現代人不可能永遠重返大自然,因為大自然不會像伊甸園般迎接他們,在這裡,海德格、齊克果或卡爾.施米特所強調的瞬間或恐懼,也許能夠幫助理解段義孚對於「浪漫主義地理學」所下的定義。
然而作者並沒有訴諸理念史論述,而是以一種印象式闡釋解讀浪漫主義,乍讀之下確實令人如墮五里霧中。我們知道,根本沒有一位浪漫主義作家聲言要創立一套「浪漫主義地理學」,然而浪漫主義詩人對於自然的頌揚的確建立出某種浪漫主義的地理學想像︰學者Michael
Wiley在其著作《浪漫主義地理學︰華滋華斯與英國——歐陸的空間》(Romantic Geography: Wordsworth and
Anglo-European Spaces)中指出,浪漫主義詩人華滋華斯對寫作的興趣,始於從動盪社會中書寫反面烏托邦(dystopia),漸漸轉向透過山林世界想像出一個烏托邦(utopia),即一個烏有之地(ou-topos)或優美之地(eu-topos)。
但段義孚所說的「浪漫主義地理學」卻與此相異。首先,它既是對崇高、超然的追求,又是對秩序的反叛。段義孚說,自人類文明伊始便有秩序,秩序以兩極對立的概念(如光明/黑暗、高/低),對人和事物作出區分,因應概念劃分的安排涉及了褒貶,例如從古到今,富人莫不是住在高處,窮人和貧民則相反,由此可見,人的住宅涉及了作者所說的「家政學」,而「浪漫主義地理學」必然反對這種秩序,但「浪漫主義」本身也追求崇高和凌越一切,那麼它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就好像神俯視世界時的超然位置,段義孚在書中說過︰「神是浪漫主義的。」因為祂並不囿於世界的秩序。段義孚還用了柏拉圖理想國中的身體譬喻︰四肢和腸胃受限於各自的活動,唯獨腦袋能夠思考,它牽動整個身體的活動,也探索外在於其需求的事物,故此書中上山下海、跋涉不毛之地的浪漫主義地理學,必然從大腦思維開始。
不易抵達的浪漫絕境
浪漫主義既嚮往極致,所慕及之處定必是不易抵達的絕境,包括畫家弗利德里希筆下的崇山峻嶺,與及不毛之地的沙漠和冰川,而浪漫主義的自然觀竟也深受兩極對立的影響。相對於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雷克寫過的詩句:「一沙見世界/一花窺天堂。」作者坦言地理學家甚少如此闡述如此「振奮精神」的道理,卻也有例外︰房龍寫給兒童的《地理學》就以大峽谷為範例寫出人類之渺小與大自然之浩瀚無情。作者也告訴讀者,中世紀人們認為地球與天體是球形的,而這象徵了人類靈魂的和諧,然而他們也認為垂直的高山破壞了這種和諧!傳統觀念中的高山,並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麼神聖,在早期基督教的觀念中,山上佈滿了女巫和盜賊。然而這種高/低的對立,卻也是我們認清星空為漆黑無物之後的極端性安慰!這也許真的說明了,浪漫主義對崇山峻嶺的歌頌,是一種對於「恐怖之美」的迷戀!
談到浪漫主義的概念,很難迴避「崇高」(sublime)的定義,對於這一美學名詞,很多哲學家和詩人都曾經討論過,如埃德蒙.柏克將其視為與柏拉圖對於美的觀念相對立,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將崇高分為高貴、華麗和恐怖,席勒則聯想到自然暴力和命運下人類行使自由意志有關,這些定義都和一般「美」的概念相反,意味著從耽美的層面提升,令人聯想到齊克果說過從唐璜式審美階段向倫理階段躍升,還有荷爾德林那被海德格討論的詩句︰「神在咫尺,難以企及,但哪裡有危險,哪裡也有救贖……」追求崇高體驗既是一種超越的經驗,自然是危險的,然而也被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昇華,就像阿拉伯的勞倫斯橫渡沙漠,或南森涉及南極冰川,既是對人世的厭倦(作者提到勞倫斯討厭人間,喜愛沙漠之純淨無人),也是一種「死亡之戀」。
既有大自然的險境,自然不乏探險者,在段義孚的概念中,只有這才能說明浪漫主義的意義。浪漫主義始於大腦探索的慾望,終於「神人合一」或「天地與我為一」的境界。這說來的確很反理性、反科學,然而一切科學莫不由探索開始,要探索就意味著要冒險,儘管科學是很理性的學問,驅使科學進步的卻是這種浪漫的原動力。讀到尾聲,讀者方才領略作者寫作意圖的全豹,那是對地理學知識的反思,及重新定義地理學的嘗試。在段義孚的重新定義下,地理學變成一種柏拉圖式崇高秩序的探求,人類像柏拉圖般把地理世界設想成身體的不同位階,同時又探索因未知而危機四伏,卻亦因此而凌越一切的領域,然後,人類將對大自然崇高秩序的想像,帶進城市設計的藍圖中,當城市變成徹底功利的「家」,我們又憧憬一種新的浪漫式逃離。這是很個人的闡釋,雖名為「浪漫主義地理學」,卻與華滋華斯等對大自然的想像不同。薩弗蘭斯基對浪漫主義的說法,也許能讓我們更謹慎地審視與自身、與自然,甚至與人類世界的關係︰「我們不能失去浪漫主義,因為政治理性和現實意識太少關注生命。浪漫主義是剩餘價值,是美麗的與世隔絕的充盈,是意味深長的豐富。」薩弗蘭斯基又引用了里爾克的一番話,可印證段義孚的想法︰「我們在家並不十分可靠/那是在被解釋的世界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