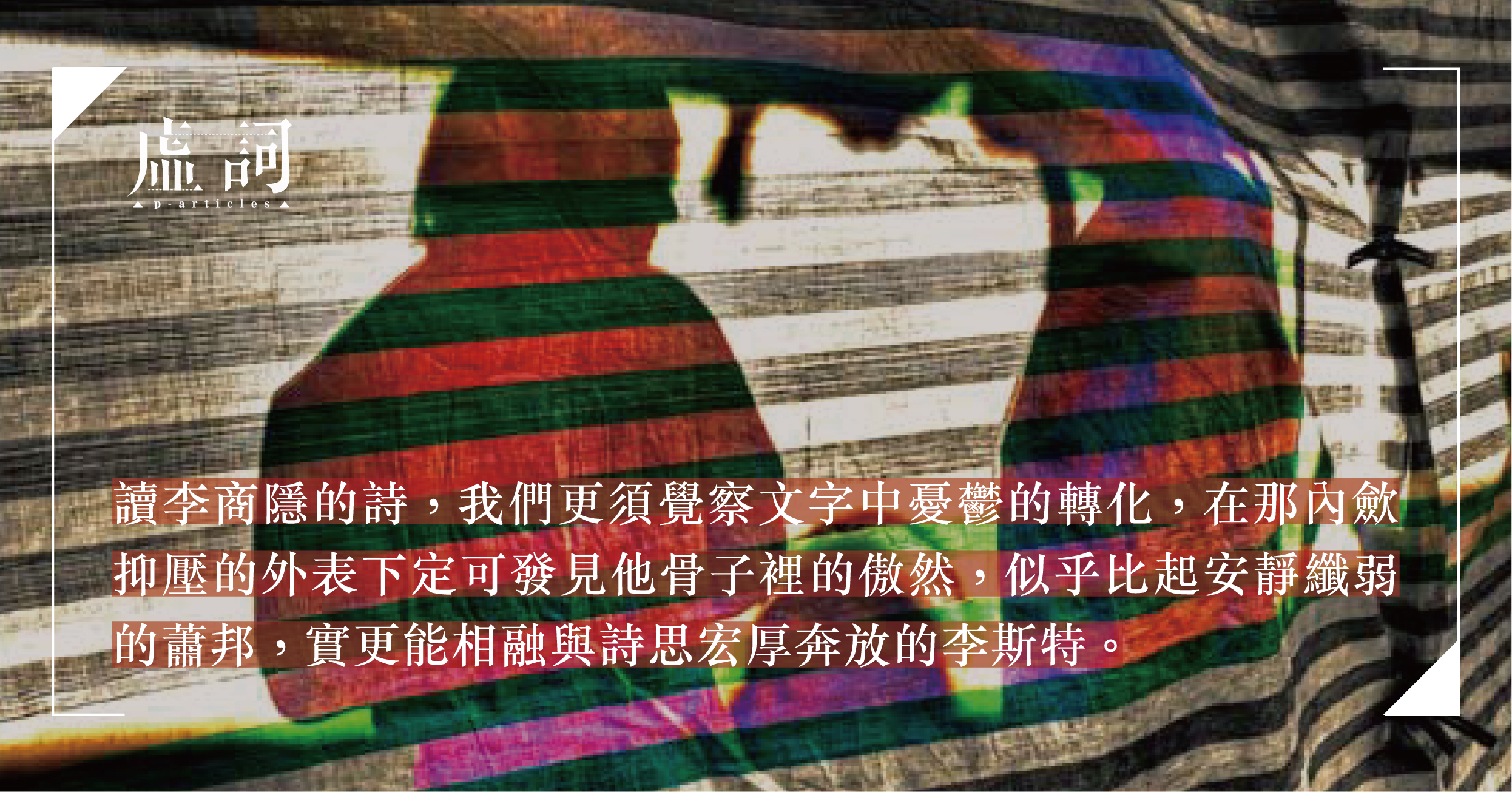千年一瞬來相遇——李商隱與李斯特的創作美學
慣於在深夜播古典音樂同時抄詩,某夜恰巧選了李斯特(Franz Liszt)的《巡禮之年.意大利》配李商隱的〈重過聖女祠〉,其意外產生夢幻般的混同令我驚異,其後試過兩位其他作品之組合,依然如墮迷醉夢幻。李商隱和李斯特素來都是我的深夜良伴,其奇妙處是每次分別抄寫或傾聽時,都能感受到一種全新的心靈相契以至人生領悟。而在同時傾聽與抄寫間,二者觸碰於相近的美學空間,進而充分表述各自的深邃以至融合,竟展現了一種幾像環迴立體聲般強烈的曖昧迷離與躁動哀切,實使人動容。以下粗談兩位在美學思想上的相類處以至相融之境,僅作拋磚引玉。
愛情路上的坎坷
錯愛與癡情成就美,大概是我對兩位最深刻重疊的直觀印象。早期德國浪漫詩人弗.施萊格爾提出「人生與詩合一」的審美,意指詩人的人生軼事具有與藝術作品本身幾乎同等重要的意義,因而首先了解一下兩位的情史,也許便能稍微對他們的美學思想有更深刻體會。
「我所有的歡樂都得自她。我所有的痛苦也總能在她那兒找到慰藉。」他這麼說過。李斯特一生愛過好幾個女人,其中愛得最轟烈的就是卡洛琳.桑.維根斯坦公爵夫人。年少時所遇過的情人,恐怕不少都對李斯特有著重要的啟蒙意義,引導他向某個範疇探索、成長,這些女人教會他很多,但都不是他的真愛。直到他36歲那年,步入音樂風格獨當一面的成熟時期,成了當代聲名顯赫的大音樂家,那時候有個貴族女人因欣賞他而額外花一千盧布買了義演的一席貴賓座,二人因而相識,一見鍾情。然礙於身份懸殊甚至沙皇的阻止,二人至死相愛而不得交往,於是李斯特把三十多年苦求不得的深愛與煎熬化成強烈的力量寫進音樂,締造出極具個人色彩的獨特風格,此見卡洛琳則成為了他在威瑪時期創作的宗教音樂甚至以後整個人生的繆思。我甚至以為,他的音樂,幾乎每一章一節都隱含了對這份愛情執念的紀錄,或是悼亡。
李商隱自也有不少為人津津樂道的風流史,然而我們知道沒有一段能夠白首偕老,那些女人與他總是以不同的形式被命運分隔開去。且說唐中晚期不少公主宮人盛服濃妝入道,因此道觀儼有宮殿色彩,而年少氣盛到玉陽山求道學術的李商隱自亦禁不住情竇初開,愛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個女人——宋華陽。據陳貽焮之考辨,〈曼倩辭〉、〈中元作〉等初期詩作俱記錄了他與宋氏相會定情之事,然似乎同是身份懸殊之故,在戀情曝光後二人強遭隔絕,難逃悲劇收場。(也曾聞是李商隱弄大了人家肚子被轟走,被罰永遠不得進山,不過恐怕這說法無甚實質根據?)至若後來的《碧城三首》以及「來是空言去絕跡」、「相見時難別亦難」等哀怨纏綿的《無題》名句亦是為她而寫,可見李商隱一生念念不忘、用情至深。
兩位的情史恰有不少相似處——離不開幾番極致地愛上不該愛的女人(至少在當其時社會處境),終致餘生段段「蓬山此去無多路」的情深嗟嘆。而至今卡洛琳、宋華陽這些名字,仍然在我們對兩位浪漫軼事的想像中揮之不去,同時造就了他們這些深具浪漫色彩的傳世名作。
浪漫精神的復興
談起浪漫。中國古典文學裡,浪漫感傷之辭起楚騷之九辯,建安始興至中唐乃盛,然自上承李白的浪漫精神衰退,而主張寫實描摹社會現況的新樂府運動被白居易、元禛等推動興起;至若在西方,工業革命人權宣言為文學、哲學、藝術等範疇開拓浪漫自由的領域,受其薰陶的貝多芬畢生創作大量高水準的樂章,既繼承古典傳統美學,同時為浪漫派開宗立祖,但後來即如極具魅力的舒伯特亦無法真正在他的陰影下更闢蹊徑,先聲既發而幾無有力回音。彼時,李商隱和李斯特的作品,或許就起了復興浪漫派的意義,把作品提升到比前人更複雜深邃的層次,同時成為開啟後世作品全新格局的鑰匙:前者奠定宋詩以至花間西崑一系柔情婉約、意象穿梭的風骨,後者則成為後世鋼琴獨奏、史詩式交響詩與民族樂派的先聲。
從對浪漫派的復興這點切入,不難觀察到兩位作品的共通點:以回到個體內在的記憶徜徉作為情感本源,傷嘆時間流逝,並以極其飛躍夢幻的想像,突破殘酷的外在世界帶來的鬱悶,描繪心靈中夢幻的風景。又或,他們不過是像本雅明,以其睥睨現實的眼光,刻意追求有別現實的另一種本真理性來直面整個世界,進而將人引導向那些被忽略的世界之真實與完整。
積極/消極的情深氣傲
李斯特和李商隱所表現的浪漫精神都是情深且氣傲的。在整個巴洛克、古典時期以至浪漫主義前期,像李斯特這樣孤獨而自由奔放的聲音(例如開創狂想曲的形式風格),可謂從未有過。李斯特為總結自己畢生的樂章冠以The Years Of Pilgrimage之名(譯作「巡禮之年」),pilgrimage實蘊含「朝聖」之意(據聞啟發自拜倫的《朝聖記》),此指他對自己藝術理想的一種極致追求,如此明言對藝術至上的貫徹傾心也是前無古人。舒曼亦曾以「詩意」、「印象的手法」解釋李斯特的《超技練習曲.第11曲︰黃昏的曲調》,這樣深具個人特色的熱情浪漫色彩在「巡禮之年」得以重整提升,我認為那種詩情以及音樂敍事的完整性也可算是空前絕後的了。擁有極高創作才情,自然處處散發狂傲之氣,李斯特的確敢於打破許多前人訂下的規範,例如從前鋼琴幾乎必須有伴奏的定制,他往往只一人一琴便在台上演奏全程,獲得當時名流貴族與音樂家大為驚異賞識。李斯特把他對情人、對普世、對藝術真理的那份近乎宗教狂熱的深愛,表現在他所刻意追求的音響音量的極端境界之中。試想像一個神情陶醉的俊朗男人,在台上揮灑著強勁有力的手指,兩小時無間斷演奏甚至不時敲垮鋼琴的狂傲,是何等叫人無話可說,只能留著淚讚歎。
如果說李斯特在諸多作品中所展現的人文情懷,是一種熱情灑脫的積極浪漫主義,那麼李商隱的詩人形象在相較之下則似乎顯得消極,說他病態得有點像蕭邦也不為過。在〈送臻師〉中早已表現了李商隱對世界的看法:一個「情」障,即是苦海迷途,不見出口。迦陵先生曾以大李杜「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句中或對於改正社會的純樸理想、或對於排解孤獨的自我幻想,比對李商隱「碧海青天夜夜心」那揮之不去的寂寞冷落。此詩前句「長河漸落曉星沉」揭示一切物象終會消失虛無,另有「天池遼闊誰相待,日日虛乘九萬風」句,道出自己發現一切追求都不過是枉然徒勞、無人相待的失落感。乍讀李商隱詩經常表現柔弱、委屈、絕望之情,與李斯特對藝術理想那種熱情奔放的追求似乎有著南轅北轍之別。
然而讀李商隱的詩,我們更須覺察文字中憂鬱的轉化,在那內歛抑壓的外表下定可發見他骨子裡的傲然,似乎比起安靜纖弱的蕭邦,實更能相融與詩思宏厚奔放的李斯特。〈昨夜〉有「不辭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塵暗觸房」句,《楚辭》寫每當鶗鴂這種鳥啼叫時,春天便會離去,百花就要零落。李商隱在這裡寫出塵世花謝花飛、離別老死的必然,他卻「不辭」奮然直面,甚至在「桂花吹斷」事過境遷、永不復返的悲哀中,進一步揭示人生一切前期落空的無從解決,而依然是毫不逃避、睜目相對,此中掩藏不了的正是一份情深氣傲。他所惋惜的是塵土把燃燒的燭光遮暗了,是世人心中的光明被無常俗事所蒙蔽,他呼喚著我們應堅持那份本初的光明與熱情,直面生命之無常。在這裡我們試圖從僅僅的美感性感知,進演成具反思性地讀詩,或能更理解那種「憂鬱的轉化」,其實不無晦暗之積極浪漫傾向。
典故作為重要元素
浪漫主義一大特色乃是高度承續前人作品精神,再從個人體悟將其重新演繹並抒懷,在李商隱與李斯特尤見一斑。兩位作品中所展現的一個重要美學元素,便是極大量地改編或化用典故,以超越時空的多意象串連,加上精緻技巧之堆疊相映,為前人作品賦予更深刻意義,表現複雜迷離的情感。
李斯特是各種音樂形式的集大成者,其中表演尤以鋼琴獨奏及管弦樂聞名,而編作方面則以對歌劇音樂的貢獻見稱。在旅行表演時期(1839-1847),他改編貝利尼的歌劇成名,即始展現並確立他喜對前人作品重新演繹的傾向,而且那些作品往往更能成為經典。如後來巴德爾松的《仲夏夜之夢》為李斯特提供了豐富靈感,被改編成更出色的《婚禮進行曲》及《小精靈之舞釋義曲》,廣為傳頌;而在《梅菲斯特圓舞曲》中則能見李斯特已能嫻熟借用前人作品,具體表現《浮士德》莊嚴的氣氛,更進一步把其時而壯闊磅礡、時而輕靈幽深的節奏,以及華麗朦朧得使人心神激盪的主氣氛表露無遺。至於在遺珠作《史特拉斯大教堂之鐘》裡,李斯特試圖描繪天使與惡靈雙聲道的激烈爭戰,能見他在剪接並化用詩人朗法羅的大量名篇時所表現的極高超堆疊技巧(其實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亦隨處可見化用但丁、海涅、雨果等詩人作品之痕跡),加上其對呈現藝術感染力的天賦觸覺,巧用豐富的調性與和聲,令敍事與抒情在音階中統一,演成極具個人色彩的奔放聲音,可見他成功對典故的善用把詠嘆調、交響詩、歌劇等音樂形式的內涵提升到更深邃奔放的嶄新層次。
至若李商隱詩中用典之冷僻絕倫則是路人皆知。像〈錦瑟〉一詩,小學時讀唐詩三百它便最得我喜愛,直覺它堪謂集中最卓絕精妙者(也是最難解者,蓋因其典故之指涉繁疊且模糊不清),現在回看依然如此認為。〈錦瑟〉與《巡禮之年》俱有回憶平生的創作意圖,同樣在描寫美麗的過去,最後暗示人生的短暫虛幻,教人悵然若失。此詩頷頸二聯化用典故:詩人過去一直癡迷在短暫易碎的破曉夢中,就像莊周夢蝶,描繪回憶之真假難辨,又借杜宇之典,抒發那份萬千留戀悔恨複雜交融,以至無法直言的深情;至於「滄海月明」不過是人們對過去美麗的想像,往事早已迷濛,而在現實裡一切所珍愛的,卻總是被命運分隔到萬里以外,不堪追憶。在這一連串意象交疊之下,李商隱像把我們帶到一個神秘朦朧的夢境裡,把一切不能直接言說的感情,透過悠遠的典故意象向我們抒訴。最後他憂怨地點出:不僅在追憶的時候才悔恨,就是失去的當時,已是無限哀傷悵惘。在此詩例中我們可了解到,情愈深邃壓抑者,則愈是無法把那些內心的躁動澎湃向人明言,因此典故意象成為了浪漫詩人一道重要的橋樑,把無法真正經歷那些往事的我們帶進他們的夢境裡試圖去感受。
審美的誤解
可是兩位的美學思想也不是誰都能接受,蓋因他們作品中偶有刻意表現藝術至上原則及技巧極度精緻複雜的傾向,有異於主流審美,因而曾受一些批評與誤解。
如劉福元、楊新我曾批評李商隱詩「濫用典故」,有故作高深之嫌,而早於南朝的學者鍾嶸亦曾提出「古今勝語,自非補假,皆由直尋」的審美,指出偉大作品所具備原創性、探索性之必要。只是,大量運用典故就等於無個人創作力嗎?以高深技巧表現對藝術至上的追求就是狹隘嗎?顯然不是的。丘瓊蓀稱李商隱詩「殊幽晦僻澀」,除了是因他喜用僻典之外,或許亦因其詩偶有把敍事主題與所指模糊化的印象式描繪手法,加上精煉雕琢的一字一句,的確虛渺難解。但此可是濫用典故,可是故作高深?非也。如上文所言,李商隱刻意以詩的語言把我們帶到他所創造出來的充滿典故意象的夢幻境界,是為了讓我們感受那些永遠不能直言的深邃情感,曲婉朦朧以見義,而這種夢幻手法以及藝術理念在前人可未曾有過,足見李商隱詩實則還是極具原創性、探索性的。
亦有論者批評李斯特作品的缺點,乃是盡其所能把最大量的音符塞進最短的時程空間內,而這不過是種毫無意義的炫技行為。但我認為李斯特對於音樂所抱持那份狂熱奔放、充滿詩意的藝術理念,應當配合其首創的果敢魅惑的技巧展現,而在實際觀感上亦是同樣,這些包含極高技巧的樂章,才是最適合李斯特表現個人魅力與才情的表現形式。舒曼曾稱他為「詮釋的天才」,指出李斯特作品中所展現的情感比技巧更高,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改編自莫扎特歌劇的《唐璜的回憶》以及《嘆息》,當中包含極具李斯特個人風格的長串琶音,以描繪記憶之回溯、夢的意識狀態、幻象之絢麗,當中的激情縱橫早已奪去了我們對於技巧的注意。炫技不過是他藝術至上理念的其中一種表述,它還有另一種面向,就是完全靜默。在李斯特的名作《愛之夢》夜曲的最後一段,是長達數分鐘的休止符,意在賦予宗教默想一種神聖的純樸性,難道這又是炫技行為?其實李斯特作品中的激情波動以及藝術至上理念,比起精湛技巧,都更值得我們去觀察體味。更何況浪漫主義本來就鼓吹形式與精神的開放,如此追求技巧之極致倒具先鋒意味,深具意義。
而迄今更有不少研究者在兩位蘊含諸多隱喻的作品中,試圖勘察其對於政治及歷史的看法,然大多卻顯然是過度詮釋,歪曲作品原意。在浪漫精神啟蒙以來,藝術作品性質走向個人內在之情感抒發,實已再無以藝術回應歷史之必要,就算對外在世界有所回應,聲音也必比以往更為自由,或是幽微。是的,詩與音樂之為藝術媒介本就應是最自由無拘的情感載體,藝術家生存在甚麼時代,就擁有甚麼時代的共同記憶與私密意象,而作品亦不過是透過極富想像力與藝術張力的形式以表述內心的聲音。因此,我們不能因其中的隱喻複雜難解而直接指出這些就不是好作品,而應該更深刻衡量這些手法的意義與實際感觀。至於作為受眾,我想,若他們不尊重藝術之為藝術的價值,並僅以回應前人作品、歷史觀點、甚至政治意味等的先設角度來解讀作品,則可謂一種無知。
千古流芳的魅力
李商隱與李斯特的作品都是座似是而非、魔幻莫辨、而深情奔放的龐大象徵森林,實讓人無法全然理解。我想這正是他們的魅力所在吧。尤在其氣韻與境界之相融間,我彷彿感受到他們在用另一個夢幻世界的方言,傾吐自己對生命的感悟,以殘雪語是竭誠描繪「心靈純粹的風景」,如楊照言則是「無防備、無計算的真情流露」。更可貴的是,他們的作品都對惟能以藝術媒介表現的,那一切超越理性思維而對自身存有作出深摰的敲問,顯露出無上的珍惜。就這份自我意識(幾乎是現代意識)之覺醒,加上致力開闢晦澀深邃的唯美藝術之路,二人可謂時代之集大成者。這也是我對他們欣賞珍愛如斯的原因。
寫到這裡我不禁擱筆浮想:假如這兩個人相遇,或許就會像羅曼.羅蘭筆下的歌德與貝多芬那樣,挽手並行、相惜相憐;又或二人如故囈語,沉醉在各自的精神故鄉,照樣完成那些超越時空而迴音不滅的驚艷作品,最後向彼此露出意味深長的回眸一笑。但願他們真的相遇,即便是在我的夢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