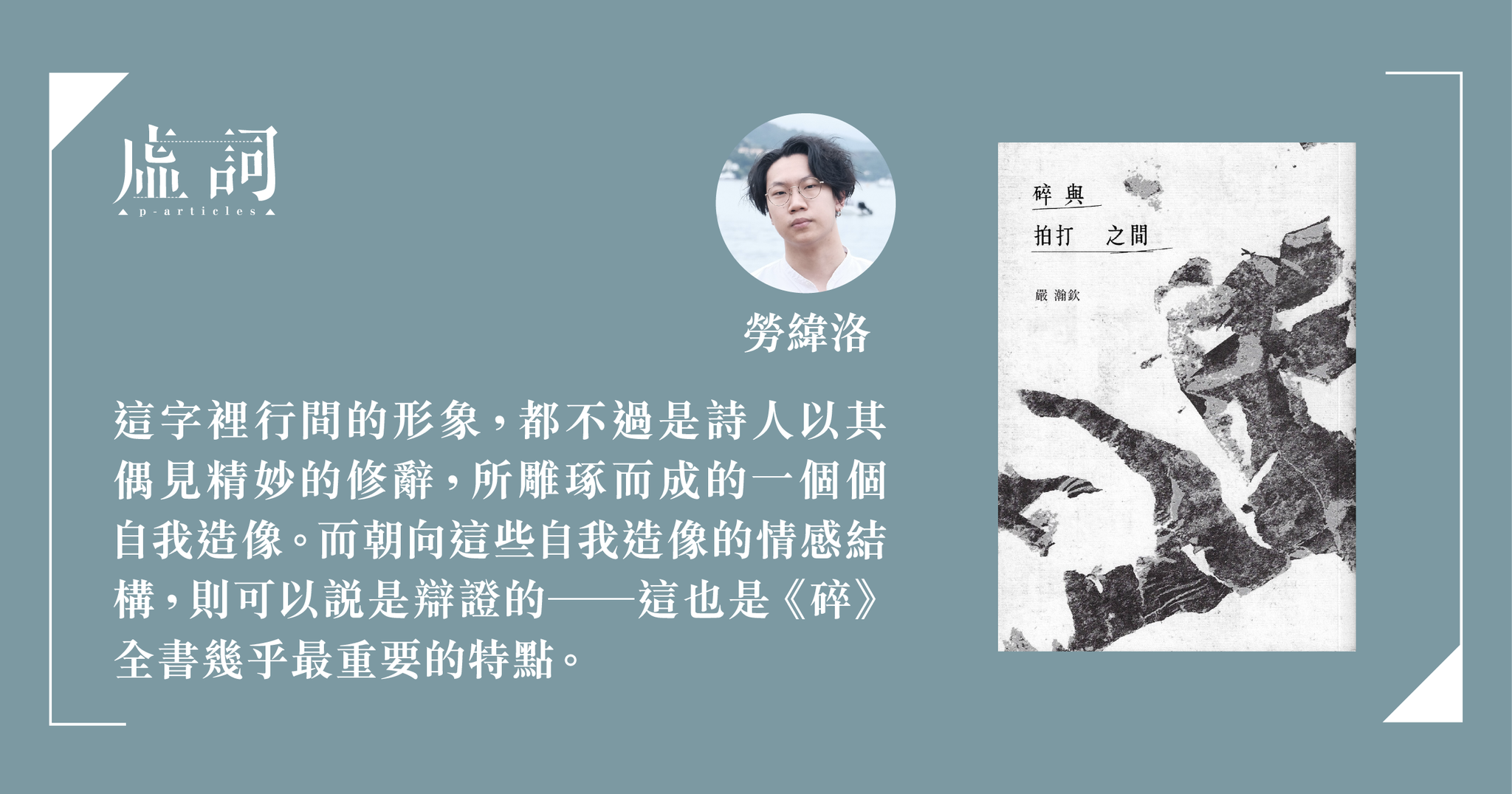修辭與戀像:評嚴瀚欽詩集《碎與拍打之間》
近這幾年,香港詩集出版頗盛,且尤多青年詩人交出首部結集,可謂各顯風采。現年26歲的嚴瀚欽在2022年出版處女作《碎與拍打之間》(下稱《碎》),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按我所見,瀚欽的寫作較之於其同儕,在詩藝上,確實相對嫻熟並迷人,而就詩的觀念本身,也有著相對豐富的省思。然則,假如《碎》並非僅僅一部編年結集,而是別具某種問題結構而選成的話,我認為,這部詩集首先是在發出,關於詩的對象的問題。這個問題所引申的,一些基本追問還包括:詩人在詩中所感知、所思考、所情動,以至所書寫的對象,是生活世界裡的實存,還是幻想世界裡的空中樓閣?詩人與其詩中對象的距離,又該如何定奪?
這其實劈頭就是個嚴格的問題:瀚欽身為詩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詩,以及寫詩?我認為《碎》給予讀者的其中一道關鍵提示,就是「修辭」。《碎》總共分為六輯,幾乎是每輯的詩中,都出現了「修辭」一詞。例子如下:
裂變出更多浪漫的修辭格(序詩:〈致讀者〉)
誰都不曾讀懂充滿悖論的修辭(輯一:〈壞日記:四年〉)
吞下一千種修辭(輯一:〈壞日記:坦白〉)
添加一點點不過分的修辭(輯二:〈荷蘭小孩堤防風車村〉)
一千個罪有一千種良美的修辭(輯四:〈我們要做的事〉)
一種發燙的修辭(輯四:〈夜話九則〉)
在樹蔭下動用各種修辭(輯五:〈夜樹〉)
動用太多修辭(輯五:〈夜飲亂談〉)
當時間之爐把所有修辭焚盡(輯六:〈悟空〉)
重複出現的,不像「夜」、「海」、「雪」與「月」等等,這些常見於詩歌的自然意象(瀚欽固然也寫了不少),而是直指詩歌語言的核心:「修辭」。若非出於詞窮,這大概應被理解為詩人有意無意,宕穿全書的強調:他在寫「修辭」;寫詩,就是寫「修辭」。當然,這不是要將《碎》讀成一部形式主義文本。所謂修辭,在這裡並不是純粹的(甚至可以完全無關)語詞之間的排列置換,不是「文學性」,而仍是瀚欽所理解的「文學」本體論之體現。而既然修辭成為了其詩作的本色,成為了寫詩的最大任務,甚至非修辭無以成詩,那麼,上面提過的問題或可先如此簡要地回答:瀚欽的詩的對象,並不實指這個生活世界,而是在世界中指認幻想的,他之為詩人的修辭手勢與造像;若然如此,詩人與他的修辭——他的修辭之心,也是他所修辭之物——之間的距離,就只須、亦只能是詩人獨斷的「美學距離」。「美學距離」畢竟是重要的,應說是必要的,如他在〈劇〉中所寫,於黑暗時代裡,「這是間離之必要/一點點布萊希特之必要」——當然,在這本詩集裡若真的存在布萊希特,也就真的只是一點點而已。
我絕不是因而批評瀚欽的詩不過「虛有其辭」,而是相反,我其實頗為欣賞這種理解詩的法門。正如上述,若《碎》中的「修辭」並不(只)是形式主義意義的文學技巧,而是作為詩歌本體論的話,它其實就很可能還指示著某種價值,某種詩人所選取的形態與聲線,甚至(假如存在的)某種寫作倫理——我將之稱為:誠立其修辭。假如我們跟隨儒家道統的解釋,將「修辭立其誠」理解為某種道德心意先行,文辭佐附的立場;那麼,這裡的倒置式就是為了強調修辭本身的純粹唯物特性,甚至能夠驅動出某種使人足以信之的「誠」的虛構強度。由是,詩人本身一旦發聲,那就必然是已經修飾的辭章,是對於自身不足夠「誠」的坦露,甚至擺明車馬、有意為之,藉此倒過來博取讀者在詩學意義上的信任——詩人與讀者之間唯一的連繫:詩。
這種取態在序詩〈致讀者〉中,就宏觀地、幾乎有點過於簡淨地寫出:「我們甚至不會/有過一次像樣的對談」,至少在表面上,這裡是在說明詩人與讀者的關係。對談並不可能顯得像樣,因為當中隔了一座以詩為名的修辭之海,而詩人近乎自憐地訴說,「刻意營造的小世界/就會慢慢攤涼」,讀者也許曾經訝異,或有剎那歡喜,但這些在詩人眼中都是無必的、註定走離的,唯有讀者離去後的餘溫可以慰藉,讓詩人繼續「騙騙還在相信海的傻子」。這裡就清楚表達了,詩人從來就不認為自己的心意能夠傳達,能夠傳達的只有這些修辭,是詞語被遣用和生成的那種糙度,能夠讓人誠以信之者,也只有這些修辭。問題是,詩人並不冀望讀者能夠久留,因為這不過是「騙騙」的話而已,到最後,詩人只是騙得了自己留下,在寫出「不再執意於寫詩」這行詩句的矛盾修辭之中。
以此角度開啟整本詩集的話,我們或許就能這樣說:這字裡行間的形象,都不過是詩人以其偶見精妙的修辭,所雕琢而成的一個個自我造像。而朝向這些自我造像的情感結構,則可以說是辯證的——這也是《碎》全書幾乎最重要的特點。在最基本的層次,詩人以其修辭為自我造像,就率先呈現了自戀的結構。所謂自戀,是個古老的文學主題,來源於古希臘神話中臨水自照的納西斯,這個典故相信不必冗述。書中瀚欽或明或暗地,數番召喚了相近的意象,例如〈葬海——寫給H〉:「每做一次傷人的事/水裡的人就替我/變得更老一些」;〈國王湖〉:「我們在水波裡瞥見即將離去的彼此」;〈雙子星的閃耀——再致讀者〉:「而我躲在水仙花的河畔/凝視倒影,擺出一副有待破讀的神情/每寫一首詩,水裡的人就推擠更多的皺紋」。瀚欽的詩常常展露出孤獨,甚至孤僻的自我體認,而在經受現實的迷惘與挫傷後,一再寫詩,如同一再望向水裡自己的倒影,某意義上就是為了在這個夢幻造像之中,重新找尋自我的肯定。
而這種意義上的自戀,也許並沒無構成危害的病症,甚至可被理解為詩歌的體式之一。一方面,尼采早就曾援引古希臘悲劇的誕生,提示造像藝術本就屬於幻想世界,是個體化原則的世界;另一方面,佛洛依德認為,生性「逃避現實」的詩人應能藉其特殊的稟賦,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恣意造像,並且將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塑造成另一種「新的現實」,藉此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而假如文學反映論的觀點,到今天還沒被汰除的話,我們可以問:在瀚欽的詩裡,表達了對現實怎樣的不滿?或反過來問,他實際上想要形塑的,是怎樣的現實?當然,就我閱讀《碎》一書,對於以上這兩個問題若有任何答覆,都將顯得匱乏。然而,這樣就奇怪了,詩人自戀,因自戀而沉溺於造像——不時也包含著對這種造像的自嘲——他的目的到底是甚麼?我的理解是,他詩中的自戀,僅僅建基於獲得他人認同,然後自己予以反對的弔詭處境上。
也就是說,詩人的自我注視,唯須透過揚棄他人的注視,才能成立;而就在該種艱難的成立之中,他就心滿意足地將其丟棄,使詩風化成像,得以完成——自我注視,於焉成為自我的地獄,而詩人所迷戀的其實是這孤獨的地獄。在此公式裡,這個象徵「他人的注視」的角色,在《碎》之中常常呈現為詩人的(舊)戀人。〈思春〉是則典例,以下引錄兩節:
而昨夜,在我凌晨三時
某個易被誤認為思春的夢裡
她褪去僅餘的衣物
向我展示尚還嬌嫵的疤痕
以及雪白的頸間
那座行將墜下的城市
橄欖風遂自佛洛依德身後揚起
這便是我選擇哭的原因一種泛性論的說辭
讓我錯失逃出夢的良機
把赤裸,歸結為時代的隱喻
在詩人「思春的夢」的幻想世界中,臉目模糊的戀人成為了陰柔、傷害與情慾展示的象徵物,以供詩人因而得以獨顯憂鬱、得以主動「選擇哭」的雙眼所觀看,尤其證明戀愛關係本身的荒敗,甚至,也是隱隱指向詩人與讀者之間,註定互不理解。然而,縱然註定互不理解,詩人卻依然渴求獲得被注視的一夕溫存,渴求展示自身的不被理解,從而引動出,對於自己這種展示的憐愛。廣義的「愛情」對詩人來說,也許亦是同樣作用,比如在〈壞日記:舊照片〉他寫到這麼一段「解構主義的愛情」:「我總是無法選擇合適的站位/無法進入方寸的世界/成為另一個自己/ [......] /不會記住褪色的情人」,可見詩人在愛情中,從未躍出自身,甚至愛情只是反過來為了證明自我的造像。又如〈壞日記:倒帶〉中寫道:「美學距離,我們與世界之間/長出一道堅硬的隔音墻//失效的票根,那些一次性的愛情/ [......] /我們都需要無傷大雅的小哀傷/以便在過於安適的日子裡,無端地憂鬱起來」,詩人追求「一次性的愛情」以便自己「無端地憂鬱起來」,殊不知以自我說明與開解為目標的情緒結構,其實就不復是(從佛洛依德到本雅明意義的)憂鬱,而仍然是自戀。
也是因此,這些戀人形象,也只是詩人藉其精湛修辭所造的詩的配角。這點瀚欽瞭然於心,正如在〈壞日記:坦白〉中他寫:「言語無從著落之地,我們/吞下一千種修辭/喊出愛人的形狀」,又或〈布拉格——給久尋不遇的K〉中:「成為你,必須尋找不到你/ [......] /而我從此就睡了在這裡/堅持對你最浪漫的誤解」。這位臨水的納西斯需要回聲,更需要著迷於,自己對回聲充耳不聞的這個場景——關於此,瀚欽同樣有著相當自覺,而且顯得情深不悔。在〈注視記憶——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中他寫:「當我說我們的時候/只有我」,而詩人動用其修辭,一個又一個戀人影子過場,到最後不過為證明詩人的「擅長斷尾、逆行/誤認自己」。至此,再次令人聯想起序詩中的那一句:「我們甚至不會/有過一次像樣的對談」,此中緣由,或許可以借書中的另一句詩作補充說明,在〈壞日記:星空〉中他如此寫:「我與我寄居在宇宙的洞穴,對談——/存在與毀滅擁有同樣的闃寂」,假如將這場對談理解為與讀者之間的對談,那當然無法像樣,因為由始至終,詩人其實都只是在與自己——與自己的修辭——對談。
這樣看來,宋子江為《碎》所寫的序言,其實不無道理:「既是愛情,就免不了與他人深層地接觸。可是,過於純粹的詩人常常會回到自我中去, [......] 過於純粹的詩人容易走火入魔, [......] 我在此處所說的『純粹』則是指,詩人的生活中只有詩,或者說,詩是他唯一最終遁逸之處。」尤其我們知道,實際上納西斯所情迷的,其實不是他自己,而是那個從破碎中藉由想像組合起來的,在水波的碎與拍打之間,只存在於鏡子對面的造像——可謂該種託名「修辭」的文學本體論的誤指。到頭來,詩人並沒有透過寫詩,真正地建立自己、肯定自己,所謂「自戀」終究是種僅僅指向其修辭的純粹唯物特性的「異戀」;但這種「異戀」卻又弔詭地,因為詩人總是在它得以岌岌確立之際,就將其一把棄絕,僅留下自己蒼茫的詩人形象,而終究成為了他寫詩非此不可的起手勢,同時宣告已是「過去完成」的殘骸。
至此,讓我們嘗試周折地答覆起始的問題:就《碎》一書而言,詩的對象,就是詩人的修辭和造像;而這些修辭和造像,最後都是為了一個精心雕琢自身的詩人形象。(詩人形象也許是個特別深刻地見於現代詩的重要命題,在古代的經典作品,比如荷馬史詩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裡,根本並不重要。)在《碎》之中,瀚欽近乎露骨地表現出對其詩人形象的想像,乃見於〈自述〉一詩。尤其是第一節,在「我」與「戀人」之間,流變了各種稱呼,「大西洋深處的一隻扁貝」、「神」、「萊辛」、「慕林」、「喪失了氣味的狗」、「困頓難行的士兵」、「小策蘭」、「為詩所誤的布羅茨基」和「櫻桃似血的戀人」,這些毋庸置疑,都是詩人過於誇張的自我想像。
至〈自述〉的第四節,他寫:「如今已經到了惜淚的年紀/於是我也寫詩——孤獨/的另一種叫法,較為委婉/卻不見得優雅些,就像這些年/我已經可以穿越如海的隱喻/將整個夜晚的哽咽熟練地/安置成有礙吟讀的斷行」,可見他有自覺,假若理解到流淚已經不能改變現實命運的挫傷,那麼寫詩(自我造像)就成為了他排解孤獨的唯一窄門,至此完全符合佛洛依德對詩人的定義。至第五節,他轉身寫到與戀人關係中所感到的唐突與厭倦,同時不無透露著不被理解的自憐與傲慢,卻又驚覺他的戀人們(其實即是為了詩而存在的造像們)「恰巧被我的詩句所傷」。唯獨是,他將她們(以及與她們的回憶)揚棄如此:「回憶裡雲霞嫵媚,如賤賣韶華的娼妓/此起彼伏而開始老去」,戀人們終究沒能挪動或重新分配詩人自我世界的感知疆域(因此其實並不成戀人),於是成就了詩的第七節,也是重新自我定義的最後一行:「又或者——神」,讓修辭本身被煉淨,得以拒絕它自身轉瞬即逝的造像,落成為最純粹的自我拜物祭儀。
在〈夜飲亂談〉一詩有句:「那些以詩為生的男人/有時只需一句弔詭的語法/便可以隱匿一生的罪行」,大概就可被解讀為,瀚欽對自身作為詩人的定位(並旁及其他詩人,也許,尤其是男性詩人),關於上面提到的自我拜物祭儀的反省與自嘲——前面就提過,瀚欽的自戀總是建基於他人(女性的戀人形象)肯定以後,自我的再次否定和棄絕之上,因此,詩中的自嘲情結也是常常可見。至此,詩集中的詩人形象再被翻轉成另種矛盾修辭,一方面詩人以詩放逐現實,卻又因為對「純粹的詩」本身的動搖,就像在冥途潛行的奧菲瑟斯,回望生活現實的瞬間,便永恆背叛了「詩的純粹」。然而——詩人需要切記:成也自戀,敗也自戀——這位奧菲瑟斯的回頭,也許並不真的因為身後傳來呼喚,而有可能,是出於生怕腳下踩空。關於詩人形象,《碎》中最耐人尋味的,也許是〈釐清〉的這幾句:「後來我滿懷絕望/學習那位決心不關心人類的詩人/才發現面朝大海是一回事/而春暖花開,卻是另一回事」。佛洛依德的啟示是:在詩人死去之前,人類並不會死去;而假若詩人不再關心人類,他只能是個死去的詩人了——當然,這已是另一回事。
近來無意讀到一段讓我很深刻的詩論,來自日本明治時代的詩人兼詩評家石川啄木:「最簡捷的來說,我否定所謂詩人這種特殊的存在。 [......] 寫詩的人本人如果認為自己是詩人, [......] 他所寫的詩就要墮落,就成了我們所不需要的東西。」確實,就如廖偉棠的推薦語所言,瀚欽此書絕對是他在這階段所交出的極為漂亮的答卷,「風華正茂」、「充滿氣血」,且憑此足以坦然對讀者宣告:「我,嚴瀚欽,詩人」。唯獨在日後的寫作之路上,如何從沉溺自戀的詩人流變成更為柔軟而清醒的人,從詩歌世界折返生活和生命,在更漫長的磨礪與流放時光裡,相信文學所應許的繞道歸回,記憶與事件的一再重啟,石川啄木這番話也許就可以是其中一道指引。然而,瀚欽有其至少在同代香港詩人間罕見的才情,他自己的靈魂,將會以他自己的方式默默鍛造,讓《碎》同樣化為被揚棄的環節,在可期的未來,大概就會交出更讓人意想不到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