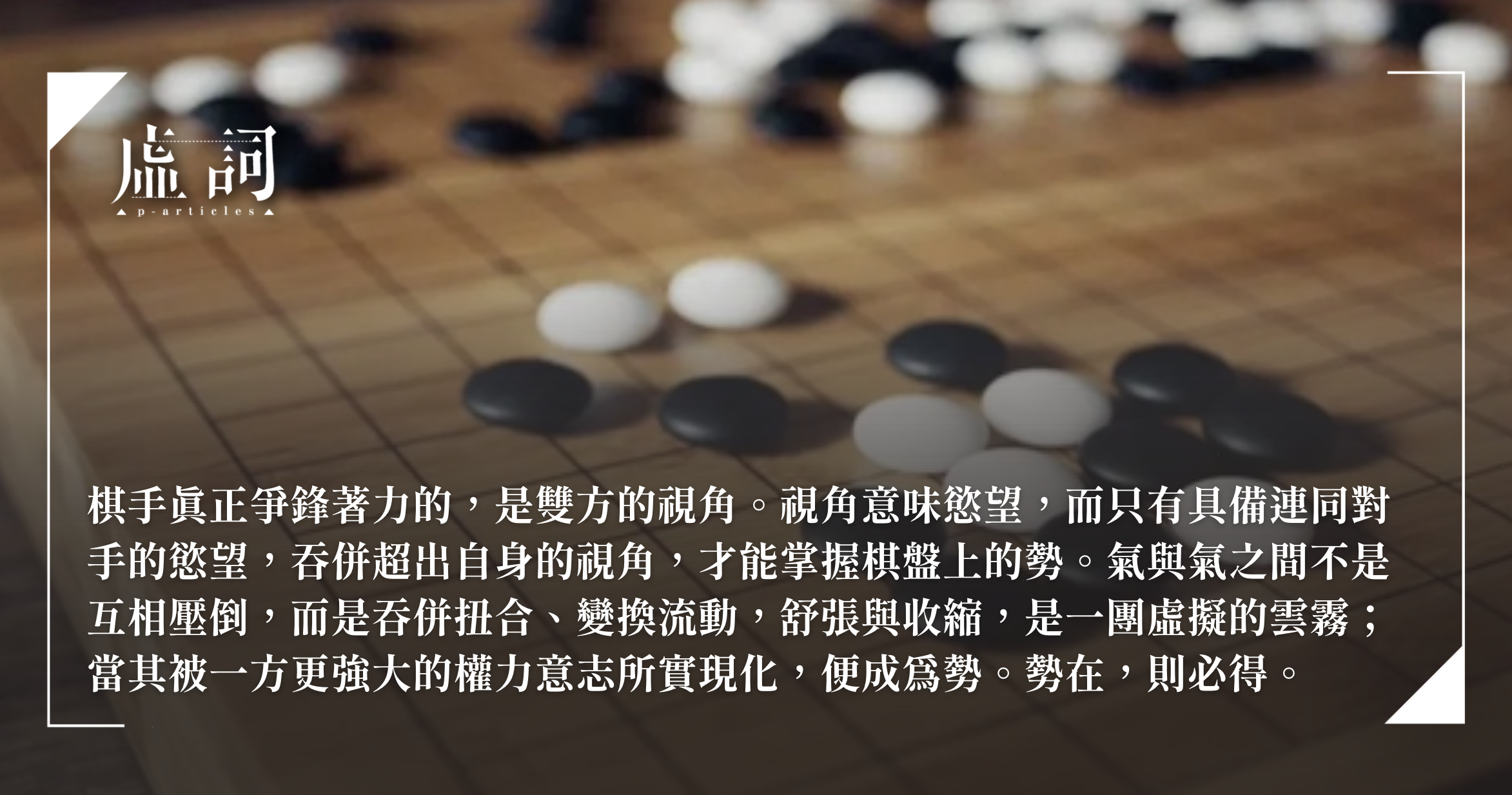圍棋思想教程:十個關鍵詞
我習圍棋,已有十六、七年之久。在圍棋這事上花耗過的時間,也算是目前活過的生命中,除了讀書寫作,數一數二的長。意想不到,最初那個把棋子當飛鏢亂丟的小孩,如今也教了五、六年棋,跑過不同棋院兼職,也斷續地當過私教,遇過一批又一批學生。我始終覺得,教圍棋是我生命中極為寶貴的經驗。在香港學棋的學生,大多都是小學、中學的歲數,他們對棋的想像力,遠比我來得豐富。在這些學生身上所感受到的生命力,於我而言,至少應與圍棋的魅力相等。從最初,會因為一對一而尷尬,一對多又不懂安排應對,到現在,總算漸漸掌握,怎樣與學生相處。我知道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因此,這些年與學生相處的時間,反而,是我最能體會謙卑的時間,聽他們說,與他們說。我始終難忘某個晴好的星期六早上,那個最愛搗蛋的學生(就像十多年前的我),笑得很燦爛,對我說:「我真的覺得很開心。」上圍棋課,原來會是最開心的事。
教棋自然不是陪玩。這些年來補習班風氣盛行,好些棋院也似變成托兒所,要求的不是棋藝,而是哄著小孩,讓家長續報,小孩面試升學時,則又多一分堂皇的證書,雙贏。我理解,但始終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從小就看《棋靈王》,後來一次又一次重看,有句話一直銘記:技近乎道。當技藝修煉到某個地步,就離道不遠了。習棋應如修道。我難以理解這種境界,大概因為我的技藝從來沒有真的升過上去,最應該發力的階段,我始終不夠勤奮。但這道,我或多或少,未算參悟,也是有些感想。尤其我本業與哲學、文學相關,有時與學生聊起一些圍棋概念和術語,講談間不覺就把這統統互相參雜,變成圍棋老師不會教的哲學,哲學老師不會教的圍棋。忽發奇想,這些想法其實可以紀錄下來,以供我們以某種從未想像的方式,重新想像:技近乎道。
凡有基本概念者,都知道圍棋最重要的一個詞,是「氣」。我們就從氣談起。所有由我教第一堂的學生,我都會問一個無聊的問題:一個士兵,他要生存在戰場上,必須的是甚麼?答案不是軍械,不是領地,不是夥伴,而只是一口氣。只要有氣,就能生存。從倫理學的傳統,我們於是可以說,氣,就是可能性本身。學了氣,之後就會教到不同的吃子方法,如何判斷棋堆死活等等,彷彿氣是第一課,之後我們就建築在氣的概念上,學不同的招法——一般老師都是這樣教。但習棋以來,我的理解未盡如此。比起作為基本概念,讓其他範疇在其上架床疊屋,不如說,氣的運作本身是個內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所有一切,都是氣的組聚與表現,而無框架或範疇可言。
所以可說,圍棋,就是關於氣的運動。事實上,周易就有掛氣理數之學,莊子亦有陰陽氣之大者之說,六朝文論有文氣才情、以志氣統神居之關鍵的論述,傳統中醫與中國武術俱以氣為基本單位,圍棋實也可放在此脈絡中理解。這也讓我們更易理解,其他與氣相關的概念,比如氣合。這個詞固然是圍棋傳到日本後,方始有的說法。在日本文化傳統中,氣首先是生命力、精神力。氣也是意氣(いき),是身體之氣,通行進之意,粹審美之道,與物哀、侘寂、幽玄同為日本美學的核心——無獨有偶,在日本比較高級的對弈室,就稱為「幽玄之間」。九鬼周造曾指,氣還可以引伸作意氣地(いくじ),是底氣、骨氣,也是武士道的義氣。在行棋之際,存一口氣,就是以自身的氣性、氣度、氣魄,與對手的氣交鋒纏繞,貫徹判斷,八風不動為之氣合。
第二個我想談的概念,是「劫」。許慎道: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故有逼迫、糾纏之意。然在圍棋,劫更是借自印度教與佛教的宇宙觀:它是一種極長的時間概念,抵達終末便將回歸重啟。一盤棋中,如果說編年時間(Chronos)與生機時間(Aeon)本不相悖,劫就是兩者交會隨時發生的事件(event)。實際而言,在棋盤上出現黑白雙方的「假眼」相貼,在同一地方可以反覆吃子,而棋盤其他地方毫無變化的話,劫就會發生。它會阻止棋局演成失去意義的「千日戰爭」,要求棋手必須尋找劫材、彼此「打劫」,以劃出差異的痕跡,只有在差異中,劫的重複才被允許發生。這樣理解,圍棋本身就呈現了某種差異與重複互相扭結的宇宙觀。有時我教學生劫,會提起尼采有名的思想實驗,如何讓小孩理解在絕對的重複之中,仍能劃出肯定的差異,則是後話了。
第三個概念是「斷」。圍棋諺語有云:棋從斷處生。圍棋既然是以氣交流的運動,如何堵截、分拆、中止對方的氣的運作,就是致勝的首要之道。有些學生剛學棋時,因怕子死,總是一隻連一隻地走,行成圍棋術語中的「愚形」,我有時會打趣說這些是「蝸牛棋」。可是學較久的學生,反而總是嗜攻,一味游剿對方,而忘記自身棋形弱點。棋行過緩則重而無當,行之過急則輕而易折。我們說這裡「有棋」、可以「出棋」,往往就是把握對方的斷點,生出變化。在圍棋的世界裡,斷就是戰鬥的開端,而戰鬥就是打開更多可能性的惟一手段。斷也是對於形勢的一切價值重估:它非但是判斷,更是對過去的中斷。往往只有劣勢者,會破釜沈舟地分斷對手,將局勢重新導入混沌。斷,是弱勢者與被壓迫者的精神形態,以「互破」中斷「互圍」,乘勢扭轉乾坤;斷裂之線,就是擺脫一切過去框限的逃逸之線。
第四個概念是「根」。既知攻守之道,不足取勝,因為圍棋不以吃子為首要,而是在終盤之際,佔據比對手更廣闊空間者勝。當氣凝聚,似就生根落地,成為實空,使對手難以入侵。圍棋老師故一般都要求學生在下棋時,一邊注意自己棋形的根,一邊搜刮對方的根。然而有趣的是,圍棋每一手的順序,毫無必然關係,可以一子右上,一子左下,如骰子放手一擲,全屬賭博,卻又總是遙相呼應。落子,即朝向未來。既無必然關係,就無恆定結構:沒有根的真正形成,只有根的變形(transformation)或解形(deformation);在佈局中,沒有一塊棋真正被紮根長成,而是在隨處落子之中,始終流動不居。棋堆是感覺的團塊,根則是感覺的坍塌;一旦執著於根,存主客得失之分,便難以展開真正的遊牧路徑。棋盤不可建築,只是蔓延、感染,供氣變化流行的內在性平面。圍棋驅動我們思考與感受的,是空間,是自由,是逃逸路線,而不是牢固的地盤。
第五個概念是「應」。學生習棋到某階段,掌握了空間的大小判斷,卻總是各有各走。於是,我常說甚麼招法全部忘記都可以,但切記一點:回應對手。圍棋是無盡的對話。我們不僅僅,甚或完全不是在以圍棋比喻符號,說我們正以象徵的方法對話。而是,氣本身的運作,就是力量的迭韻(refrain)。在棋盤上,雙方一言不發,甚至必須沉默,卻不是以棋子代言,而是以沉默逼出彼此真正的責任。對弈的唯一責任(responsibility),就是踐行回應(response)的能力(ability)。棋盤成為了充滿情動(affect)的肉身,對弈的主體性不是發生在任何一方棋手身上,而是僅在棋盤這個中間之褶。落子間與對手兩忘,才是真正的對弈。如此看來,所有落子,無非都是「試應手」。這是圍棋更深刻的倫理學意義:在回應中,我們總是打開著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能性。
第六個概念是「先」。既然理解回應,下一步就是在無盡對話中,始終爭先。這裡所謂的先,不總是時間或順序上的首先;先,是氣所生成的強度(intensity)。如果先只是順序上的先行,則其實無所謂爭先,因為黑棋總是先手(除非讓子或座子,由白棋先手),在無子死亡的情況下,它總是佔據先行(數量始終等同於白棋或白棋+1)。因此,先是順序的翻轉,即是脫序。真正的先手,總是源自「脫先」,意即脫離現存結構,尋找新的落子點,它所承載的是向對手意圖的背叛和解構。故也許,脫先無關先後,而是反抗的力量,是逃逸的強度;先手者,就是不合時宜的手勢。按此推想,其實在每次回應對手的過程中,我們都總在脫先,意義始終寄失,但唯有在此反而生出了差異。差異並非否定,而是邀請對方一同思考,一同創造。在對弈中彼此爭先,其實就是爭取創造的強度。
第七個概念是「勢」。勢幾乎是圍棋最抽象的一個概念:勢就是氣的結晶化。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按一般圍棋老師說法,勢首先是外勢,相對於實地。但在上面我們早已消弭了兩者的對立結構,事實上,這點自 AI 圍棋橫空出世更是顯然:地可以是勢,勢可以是地,從前常謂「裡外交換」,到今日不過是無所謂裡外的流變。勢也是形勢判斷,圍棋有一組組非常曖昧的形容詞:大小、厚薄、輕重、快慢、緩急,全都是勢。按孫子言:大小強弱為形,虛實奇正為勢;形勢卻無常道。我的理解是,勢就是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棋手真正爭鋒著力的,是雙方的視角。視角意味慾望,而只有具備連同對手的慾望,吞併超出自身的視角,才能掌握棋盤上的勢。氣與氣之間不是互相壓倒,而是吞併扭合、變換流動,舒張與收縮,是一團虛擬的雲霧;當其被一方更強大的權力意志所實現化,便成為勢。勢在,則必得。
第八個概念是「味」。習棋一段日子,往往就如飲醇醪、品香茗,不覺而知其趣味。在圍棋裡,味還具體地表現在某些局部,我們稱之為「味道」、「餘味」,實則歸結為四字:保留變化。何以味道與變化相關?在拉丁文傳統中就有 sensus communis 一詞,相當於今日的 common sense,指的是邏輯與藝術教育意義的共同感,也是品味(taste)。而近現代的英國與中國文學評論術語,無獨有偶都有味道之說。圍棋之味也可放在此中對照。由於圍棋總是在迭韻中發生,它要求雙方品味相當,才能締造真正的創造。因此味攸關判斷,妙手與俗手,則又全是攸關變化。能夠保留變化、保留想像,而與對手共振,即掌握了味。對味的判斷,是可能性的複褶(complication)。味,是認知的剩餘物,是溢出自身的味外之味。味總是立足在意義的邊界上,表現不可見者之不可見;在邊界上交鋒,就是圍棋的意義的邏輯。
第九個概念是「殺」。圍棋取勝,可殺可不殺:殺之道,是野獸之道;不殺之道,是王者之道。殺所邁向的,是相對於不殺的外邊思維與少數思維,是酒神精神,是成為野獸的意志。也就是說,殺比起不殺,更輕易撥亂勢,因為殺總是要求在混沌中的一切價值重估。我又常與學生提到,圍棋本身蘊含許多與天象相關的智慧,單從棋盤上的「星」、「天元」等已可略知。按中國古代觀星術語,殺者七殺,變動繼生之象,征伐陷陣之志,殺機的或藏或露,都是星叢的突變;殺破狼,即成為複數的野獸,棋局必改易其主。殺既複數,即多重皺褶(multiplicity),是流變的團塊。而當雙方都起了殺心,局面則成「對殺」。殺,意味主動地投身氣勢的鬥爭,此即圍棋中最為極致的情動。
最後一個概念是「變」。圍棋的最高境界,有人說是天道、宇宙、陰陽、無我、不動,各有深悟,而我到目前領略到的,惟變一字。圍棋有所謂「定石」或「定式」,可理解為前人琢磨而得的一些招法套路,老師往往要求學生背熟。然而,兵無常定之理,所謂「棋理」到底並非重複,而是在芸芸定勢之中,尋出變化的生機。則理非理,非理亦理,故為道。孫子故謂: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棋若抵達神之境界,即因應對手而生生不息地流變,與進退之象齊一;「神之一手」,不是絕殺之著,而是所有可能性的重啟,是時間的懸置。所以為神,在其萬變,把每一手棋從本來的因果限制中解放,還原為一顆顆單子(monad),每一手本身即「手割」。從道策、秀策、吳清源,到當世眾多強手,每有閃爍靈著,無不如此。如如不動,變而不變,則心性修為,亦無心無性,習技通變,則幾近道。論之知不如,惟心之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