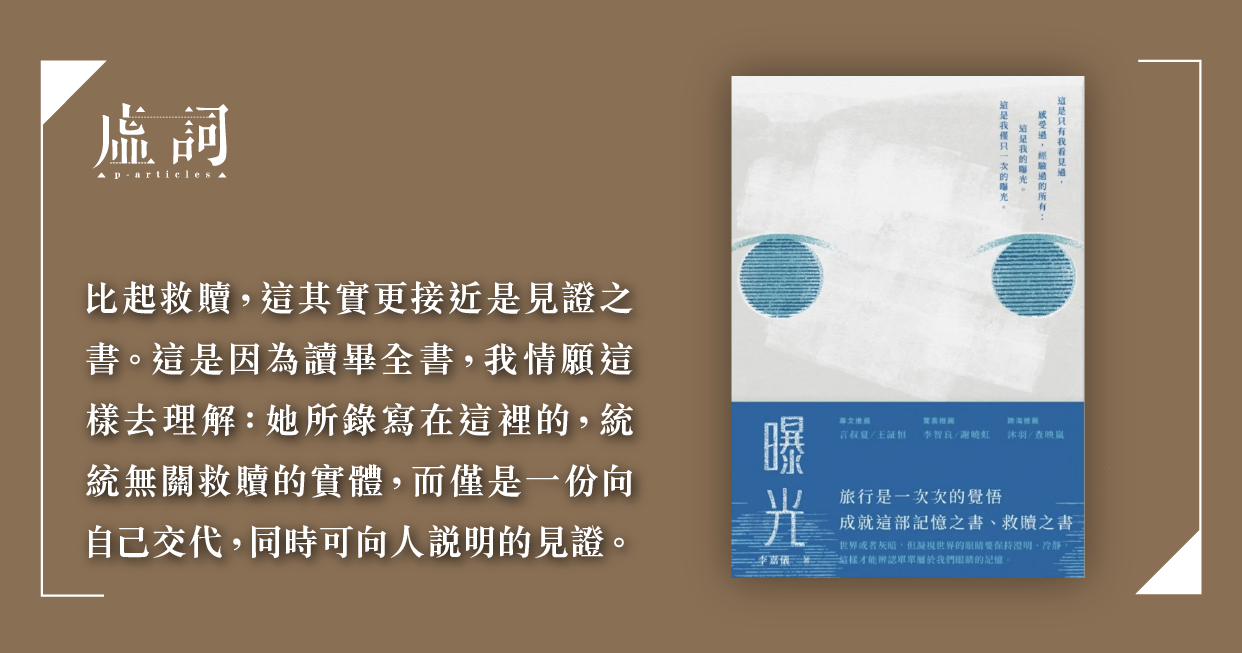見證之書:繞道與痕跡——評李嘉儀散文集《曝光》
我想肯定,動作與書寫不是虛妄的, [......] ,即使到了最後,我們得不到救贖, [......] ,因為這是我們的曝光。
——李嘉儀〈曝光〉
李嘉儀近來出版散文集《曝光》,在文友之間頗受討論讚賞。嘉儀本是寫作的多面手,在詩、散文、小說等題材上俱有佳作,見於不同平台,一直以其近乎攝人的敏銳、深澀與敬虔,獲得讀者喜愛。《曝光》是她的第一本書,選擇出版散文集,並至少出乎我所意料的寫得簡單、清煉與溫柔,此中大概自有深意。要嘗試為《曝光》定性,謝曉虹在推薦語中寫道:「這是一本救贖之書。」我或會說,比起救贖,這其實更接近是見證之書。這是因為讀畢全書,我情願這樣去理解:她所錄寫在這裡的,統統無關救贖的實體,而僅是一份向自己交代,同時可向人說明的見證。
就我所知,嘉儀是基督徒。那麼在基督宗教語境裡,甚麼是見證?在耶穌降世為人,道成肉身為他的父作證之同時,吩咐門徒所要行的誡命,就是為神自己的將臨作見證,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可以確信的救贖時刻。然而,尤其在當時耶穌被判處為政治犯,送上最恥辱的刑具上受死,門徒們各自離散,為主作見證其實並非看起來那麼大義凜然的事情,更不是現在主流教會很習慣那種茶餘飯後的見證分享,而是隱密的、蒙羞的,最令人可笑的事情。因此,使徒保羅才會這樣說:「我不以福音為恥」,就是那些在世人所看為恥辱與無知的事情,他要以此為標竿,要在徹底坦承自己的軟弱之中,見證神的聖潔與大能,亦即為救贖作見證。
唯獨是,見證必須抵達最遠的他方。耶穌升天前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並非純粹的虛耗或出於某種世界主義的野心,而是耶穌應許在見證之途上,持續地建立門徒的靈性生命。也就是說,唯有遠行、繞道,直至「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才能體會這份見證的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曝光》即是見證之書。這於是也不難理解,為何書中八篇全是旅行遊記,是離香港經驗最遙遠、看似最不相關的彼方,這一切是嘉儀要為將臨的救贖作見證的自我說服:「通過回述來橫越自己」。這其實也可被演繹成,對文學本身的某種後現代手勢:唯有藉由繞道,才得以乍見道之痕跡。
於是《曝光》首先體現出來的,其實是繞道在外的「旅情」精神。作者書寫其走訪拉斯維加斯、溫哥華、維多利亞島與泰國的經歷,彷彿是一再抽離己身,投入另個陌異他方的風景,只為重新觀照、整理、洗練、撿拾並說明,那個本就破碎不堪、深受困惑的自己,猶如光之折射的差異與重複。不忘柄谷行人的斷言:「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畢竟一場場的書寫下來,為的純粹是展現作者對他方的興趣嗎?《曝光》是關於這些他方的旅遊指南嗎?並不。《曝光》所曝光的,僅是作者的內心,除此無他。嘉儀這樣寫道:「被我們稱之為『風景』的這種平凡東西,是一個巨大且不能擊倒的存在:它包攬了我們所有的細節與污垢,與我們的言說緊緊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說,繞道外部而得見的風景,因而成為了作者內心最珍視的某份憑據,足以支撐其言說下去、寫作下去和存活下去的憑據。
換句話說,其實作者遊歷何處,畢竟並不那麼重要。這些被錄寫的他方,只是作者為了達到「旅情」境界而在因緣際遇之下,碰巧外借的中域(milieu)。這種結構一再出現,比如〈曝光〉的天窗、〈橫越〉的公路、〈後台〉的公園燈塔、〈木屋〉的泰國女人們、〈每當你看見渡鴉飛過〉的渡鴉和女孩、〈鳥體〉的煙火、〈賭城散步〉的車外遊民、〈她〉的姐姐與姐夫的臉容,全是作者書寫繞道的中域,是語詞非此不可地經受橫越的唯物性,最後只能曝現而成一段段模糊、消散,同時深蝕的,難以辨清意義的光度——「曝光」,這是我所理解書名的意義。尤其〈曝光〉中一再強調的「滯漫的時間流」、「時間與光度上的錯開感」,這種光度乃是某種「追尋逝去時光」的綿延(la durée)的光度,即時間被寫作還原成了摺疊在此刻的內在性,更具體來說,大概就等同作者提到的杉本博司攝影技術。於是,她得以如此寫出:「彷彿我只要站在那裡,就不會有所損毀,是一片我恆久珍愛的光之風景。」
至於,在這樣的「光之風景」之中,嘉儀呈現了怎樣的,讓她足以相信能向自己交代,同時可向讀者說明的覺悟?要回應這問題,我認為〈鳥體〉是表現的比較具體的其中一篇。〈鳥體〉寫到作者在七月一日這個對香港人而言的特別日子,到訪維多利亞島,而那恰巧就是加拿大的國慶日。當煙火綻放,全城紛紛高歌,作者卻將自己托印成了局外人、異鄉人,托印成了他者。然而弔詭的是,這麼個他者在對其而言的他國慶典中,才得以釋放那鄭重其事的懷念與哀悼,如陷飛鳥般的幻想,溢出其疲憊的身軀,最後又落成自己所親手撿拾的情感殘屍。藉由這片風景之光的流轉,彼此折射、承接,抵達與離逝,作者彷彿就從原先的解離之中,重新尋回自己。
而也許顯得過於嚴格了——我的問題是,當嘉儀寫道:「將屬於自己的光轉化成文字,轉化成每一個書寫手勢」,究竟是書寫其中的「我」是光的中介,抑或「我」以光為書寫的中介?所謂「大寫的書」(le Livre),畢竟成事在於文學可期的終末(telos)嗎?更具體而言,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是:《曝光》這本書,對作者本人而言,真正地完成了的是甚麼?最表層的,也可能即最深邃的是,她期望這樣的書寫所能給予自己的,是最低限度的理直氣壯:「因為我們是存活下來的人,所以我們可以言說,可以沉默;所以我們可以瘋言瘋語,可以歌唱。」也就是說,最低限度的,對於倖存者書寫的無上肯定。
在光之中,一旦察覺自身從往日的創傷,甚至他人之死中走了過來,一切真正深刻的書寫,都只能是倖存者書寫。這裡牽涉的,不單是、甚至完全不是文學技巧的問題,而是倫理學的問題,是政治學的問題。假如「我」是被這光所拯救過來的,「我」能因為見證之故,一再重述那些創傷嗎?如同嘉儀的自我拷問:「我們是否具備資格,可以在現在與未來挪用回憶的言說,來覆蓋往昔回憶發出的聲音?」在《曝光》中,嘉儀小心地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她畢竟只是寫出自己內在的風景,似乎與人無尤。有趣的是,在八篇散文之間穿插了一些閱讀筆記,其中一篇提到普利摩.李維對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的觀點,將從「最無助的人」到作者,再轉到讀者的傳導過程,交付予一塊象徵的布簾,以抵抗徹底的非人化。這實是值得更多深思的文學的生命政治問題,卻是在八篇散文之外,才被點明來說——或許亦是另種繞道,德希達所說的「痕跡的痕跡」?
但是這種似乎過於簡樸的自我肯定,到全書的末篇〈她〉,畢竟被重新提出,並動搖。〈她〉寫到寫作者到拉斯維加斯探望姐姐與姐夫,在姐姐駕車送她到家的途上,反覆回想起從小被姐姐欺負的細節。此篇最後寫到許多年後,仍然態度冷傲的姐姐對作者說:「不要寫我」,而作者答應了:「放心,我甚麼都不會寫的。」結果,是在同一刻,她心裡就升起了非寫不可的欲望,當然,即成就了〈她〉這篇。這是向姐姐的復仇嗎?抑或單方面的和解?還是告訴自己,能夠寫出來,大概就能跨越創傷?作者並無正面回答,而這樣收尾:「在某種意義下,我很像妳,甚至在行文之間變成了妳,擁有一個施暴者與獨裁者的模樣。」這是否某種在書的「臨終」時刻裡,為了寫作行為本身的認罪?
假如是這樣,出版這些寫作的唯一原因,只能夠是作者相信這樣的認罪——如此羞恥,但堅持不以為恥的見證——能夠成就往日創傷的和解,同時指向某個可期而未至的救贖。《曝光》的寫作於是被鑲嵌為從本雅明到鄂蘭的政治神學命題,即假如能夠衷心認為自己成為了從前人的彌賽亞,這份對於他人說出「你曾經透過詞組抵達了我」之未來的「預先允諾此刻」的確信,究竟從何以來?亦即是說,《曝光》若被讀成見證之書,這份見證的基體是甚麼?回到基督宗教的理解,我認為見證的基體就是基督的死,是神性放棄的瞬間,自願投入被父所「離棄」、一無所有的深淵——當然,也包括基督的復活。而若《聖經》不寫基督的死,它就將會毫無意義,耶穌登山在門徒面前神顯綻光,亦不過是虛妄笨拙的自欺。
身為書寫者,且僅從象徵意義來說,若有所以虔信的基督,究竟是基督受死這一事件作為起源(Ursprung),還是後來聖徒們談起基督復活時,顯在臉容上那種複雜斑駁之光度?我認為嘉儀,至少在《曝光》裡所呈現的,更傾向於後者。只因起源,原是最蠻荒、最可怖的神蹟;而《曝光》所趨之沐浴的,乃是約旦河的施浸之水,甚或是聖徒的眼淚,而非吞滅世界,而仍有神之應許與奧秘運行其中的遠古洪水。也許嘉儀自有察覺:「每當我們開始言說『往昔』,便能真正意識到:不管如何,人類無法終止時間,也無法切斷時間的痕跡。這是一種對人類的詛咒,也是創作者賴以維生的恩寵。」背負著劫後餘生的詛咒與恩寵,在如此的「見證之書」其後,有無可能進一步接觸到、並成為事件(événement),或至少劃出更生動、更差異化的痕跡?
費爾曼指出作為見證(testimony)的文學書寫,注定是種述行寫作,是穿透他者而折返的孤獨任務。這讓我想起嘉儀另一篇沒有收在《曝光》的作品篇名,引用自《聖經.約伯記》的句子:「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但是,這種「報信」所真正見證得了的,畢竟是從前人(甚或包括作者自己)的創傷與和解嗎?如德希達認為,文學更應該是對一般理解之見證的解構,要指向的並非「我因此得救」的肯定式和完成式,而是始終挖掘並曝現各種無以驗證之真實(le réel)作為見證,甘心招弄虛構性的纏繞、延異與永不抵達——也唯獨如此,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協議才不是述行的,而是秘密的,一種純粹閉合、同時向上敞開的名為「文學空間」(l’espace littéraire)的體驗。
言叔夏的序文寫得最為精準、敏銳,且也溫柔,她指出《曝光》某程度上其實就具現了社會運動創傷發生其後的「精神後遺狀態」,從而寫出了「所有物體長曝的軌跡」,而這種曝光畢竟可以為繼,因此,她願意「祝福這本書裡的一切,永遠有明天。」也就是說,這本書在該意義上,成功地作為了後來寫作的前提。在後記〈寫作的祭品〉中,嘉儀花了出奇長的篇幅解釋書中的人稱調度,乍看是「我—你」(I-Thou)關係的複寫思索,但事實不然。正因這是散文,如她寫道的是「救贖『我的救贖』的存在」,對作者來說只是救贖的前提,其所回應、所真正完成的,全不過是那個曾被掩埋的「我」(而不是「他」),是作者對於自身所經歷時光的某種敘述治療;也唯有如此解釋,「你」才心安理得地被換回成為「我」的祭品。於焉,身為「失敗的賦予者」、「失格的無言者」寫作下去,書寫者仍須投放更長等待與思考的是,有沒有可能在困頓的餘生裡,習得這樣的自我說服:在最彼遠之所在留下痕跡,只為證明自己,從未真正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