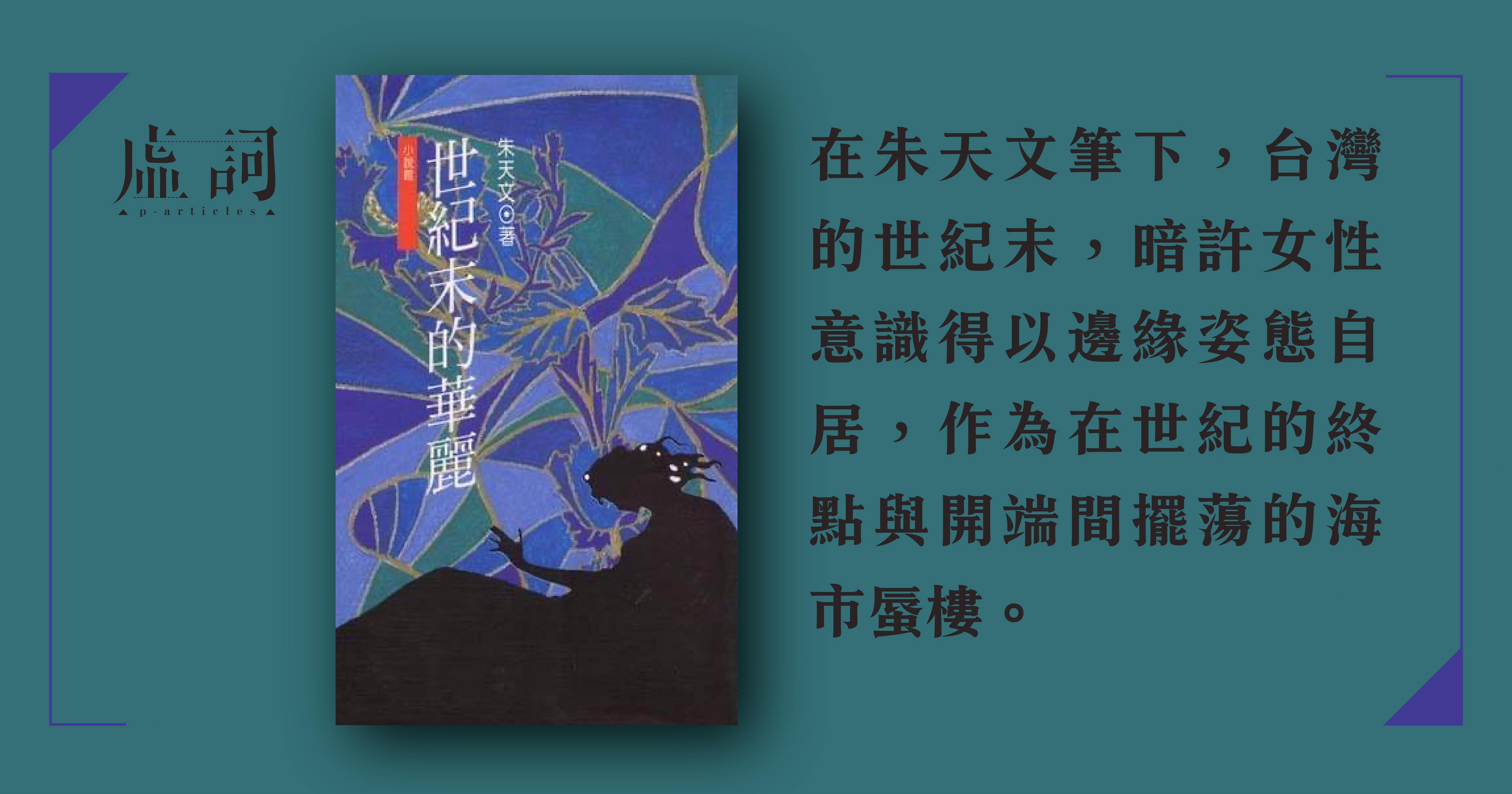女性的瑣碎時間——讀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
〈世紀末的華麗〉體現出「瑣碎時間」(detail-times)作為書寫策略,是當代台灣文學中女性主義的重要面向。世紀末(fin de siècle)本就作為時間概念,始源於西方十九世紀末,多見於歷史與政治相關的論述場域。在一百年後的二十世紀末再度興起,多有著名論者關注,例如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以撒亞.柏林(Isaiah Berlin)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當然,這種思潮在文學場域亦影響甚深。朱天文以此為題,暗示小說關於時間。世紀末是雙面的:既是盛年不再、事事將休的末世論觀點,也是風華萬千、急切加速的新時代期許。朱天文只取華麗而隱略荒敗,正是其小說欲語還休的用心所在。就如王斑在〈呼喚靈韻的美學〉中指出:「它以冷凝的驚人意象做為時間遁止的象徵,以對抗黑暗混亂之歷史劇變。」小說於焉即深刻地作為攸關時間與歷史的政治學。
在朱天文筆下,台灣的世紀末,暗許女性意識得以邊緣姿態自居,作為在世紀的終點與開端間擺蕩的海市蜃樓,如王德威所指出:「表達了台北(以及台灣)在二十世紀末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及無所依憑的地位。」這種曖昧的擺蕩姿態,暗地流露強行摹仿的種種腐跡,使得王德威認為難以斷定米亞(也是朱天文)「究竟是特立獨行的女權主義者,還是莫名其妙的寄生蟲。」這樣的女性意識體現在小說中的「瑣碎時間」。整篇小說以近乎科學或指南的描述性(descriptive)筆觸,描畫時裝、植物、建築、手作品等流行知識,而這些物事統統又被視為瑣碎的,易逝的,邊緣的——複數形式存在「如衣服」的,在朱天文筆下,卻從女人的隱喻經由概念賦形化(conceptual figuration)成為自足現實,反倒起了諷刺男人中心意識形態的作用。
在此杜撰「瑣碎時間」論說朱天文的小說,由來有三:周蕾提出的「瑣碎政治」(detail-politics)、王德威承之提出的「『瑣碎』的歷史感」,與及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婦女的時間」(Women’s Time)。〈世紀末的華麗〉避談政治,著意描寫細碎、感性的墮落與浮華,一如張愛玲的〈更衣記〉,以日常細節抗衡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正正擊中了時代的要害,在綾羅綢緞間編織出頹靡的政治寓言;在台灣終可當家作主的歷史時機,朱天文斷然流退瑣碎的暗礁,嗟歎時不我予而自囓其身,卻也潛藏不無挑釁的側目注視,以令人炫目的、瑣碎鋪張的詩學,堆疊映襯歷史中不能承受之輕;在世紀末裡書寫瑣碎之物,正是屬於女性主義的,主觀與週期的時間,則時間本身由此便作複數羅列的狀貌,是為後現代的「times」。詹宏志在代序裡描述得極為精妙,他指出〈世紀末的華麗〉正是「好一座遍灑香水妝點鮮花的所多瑪!」以最華麗的末後舞姿,隨同時間荒涼毀壞,凝蝕成永恆墮落的岩柱,瞳孔亦因為重複漂染而終將暗啞褪色。
因此,若然小說裡體現出某種女性主義的面向,那亦必然攸關世紀末的時間形態:還魅女性的官能瑣碎呈現(presentation in neurotic detail),消解男性的理性符號敘述(narration in rational symbols)。關於〈世紀末的華麗〉不事情節的特點,王德威就曾在多篇文章指出,朱天文正是期望藉由專寫氣味,寫衣裳,寫氛圍,出離於男性主導的符號敘事法規,而這種風韻披及之浪流與虛無的形態,恰恰是屬於典型的(甚至是略顯平面的)世紀末色彩:「米亞是個訂做的世紀末人物,一個金光璀璨、千變萬化卻又空無一物的衣架子。而朱的小說自身,未嘗不可作如是觀。」這裡並非作為男性的王德威在判斷小說上有所偏視。白先勇也曾指〈世紀末的華麗〉非必是事實與現實的抄錄,更是感覺與感官的記載;朱天文自身亦承認,在《巫言》及之前的作品,她是有意迴絕以「說故事」(story-telling)為創作方式——而〈世紀末的華麗〉的目的,更只為小說的末句:「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跟制度所建立的世界是要崩壞的,到時候女人將以嗅覺跟感官重建這世界。」意謂它本身就是抽空了內容的,作為理念——更準確來說,是純粹情緒和感覺——先行的寫作。
談到官能與時間的關係,〈世紀末的華麗〉裡不可忽略的,還有關於女性的身體描寫。「去性化性癮」(desexualizes sex addiction)一詞可以指稱小說中以抽象代替具體,以荒蕪犒賞刺激的身體描寫與性場景。小說裡這樣描寫米亞與情人老段之間,性愛的懸置(aporia):「他們過分耽美,在漫長的賞歎過程中耗盡精力,或被異象震懾得心神俱裂,往往竟無法做情人們該做的愛情事。」由是可見,米亞企圖在性(抑或其他種種瑣碎物事)尋找自身與時間的殘存關聯,迎接她的卻是教人感歎迷惘、孤寂與無奈的斜陽景色。一如王斑指出:「所謂性烏托邦的烏托邦,事實上是一處無人性的所在。」小說中欲蓋彌彰的荒敗,終究如同風乾玫瑰,凋萎無常:「她目睹花香日漸枯淡,色澤深深黯去,最後它們已轉變為另外一種事物。」小說追懷無有,卻又難以彌補,暗示著世紀末的女性一如台灣的現代化,註定過於早熟與遲暮,生鮮骨肉所承載的卻是老靈魂。然則這份情懷尚未待人追憶,只是當時已見惘惘的威脅:世紀末的華麗,就是新時代的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