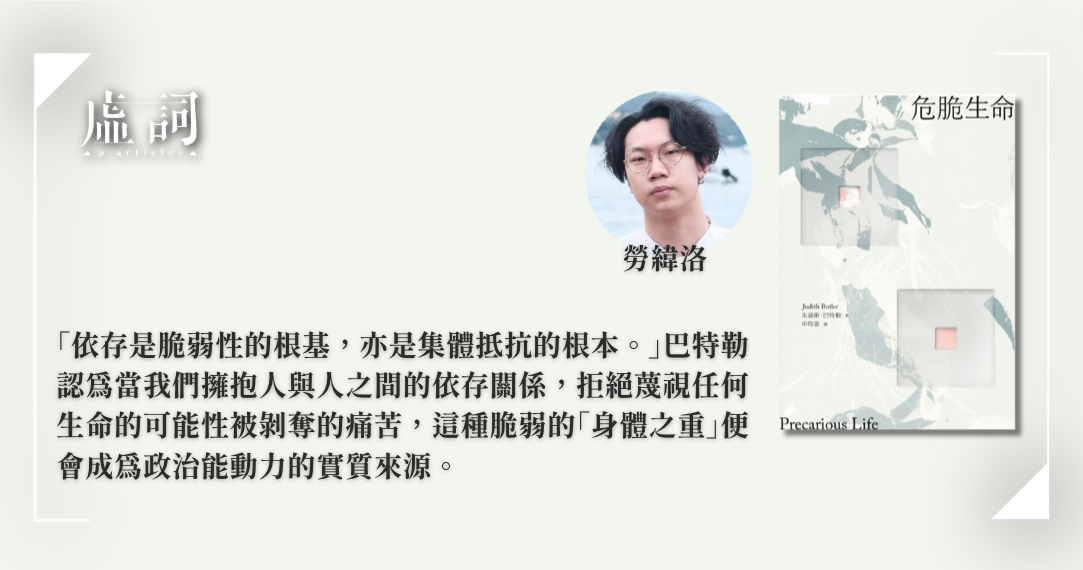情動身體、哀悼與脆弱政治:試談巴特勒《危脆生命》
你是否願意,幫我用這隻手把屍首抬起來?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安蒂岡妮》(Antigone)
弔唁並讓弔唁本身成為政治資源,並非退縮或不採取行動;我們能夠將其理解為認同苦痛的緩慢過程。弔唁所帶來的迷失感——「我究竟成了甚麼?」或「我還剩下甚麼?」、「我從他者之中失去了甚麼?」——把這個「我」放置在「不知道」的處境之中。
——朱迪斯ㆍ巴特勒(Judith Butler),《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我們必須守護我們的脆弱,誠如我們必須拯救無用。⋯⋯因為脆弱讓我們彼此靠近,力量卻使我們彼此遠離。
——尚—克洛德ㆍ卡里耶爾(Jean-Claude Carrière),《與脆弱同行》(Fragilité)
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迄今已近兩年尚未止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進入大規模戰爭狀態;敘利亞、阿富汗與非洲某些部落之間的武裝衝突與內戰頻仍;中國與其周邊地區乃至與美國的關係持續緊張⋯⋯在硝煙撲鼻的今天,我們到底應如何理解戰爭?又應如何理解在戰亂中,那些離散失喪的生命?我們還能懷著怎樣的理想,立足人文學科的視野批判思考,從而尋覓立身處世的行動綱領?長年關注性別議題的政治哲學知識份子巴特勒在經歷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衝擊後,寫成《危脆生命》一書,著意探討戰爭、暴力、哀悼與生命的脆弱等主題,放諸今天再讀,並未顯得過時。手民出版社今年推出此書首度繁體中譯,我便藉此機會試談一些切入此書的方法,並稍梳理巴特勒的洞見,尋索其於當今世界意義深重的靈光。
危脆(precarious / precarity)是本書最重要的關鍵詞。所謂危脆,是指生命的脆弱、易損與岌岌可危的特質,巴特勒期望以此概念出發,重新思索共同體的基礎。顯然受影響於拉岡(Jacques Lacan)學說,巴特勒認為在人臨到世界之初,社會關係就已存在,是故主體不可能脫離社會規範而被承認作主體,也就是說,即使不是極端的宰制,與他者的關係至少總已決定著主體的存有根基。因此,主體不可能在與他者的關係中,尋求完全獨立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於是,危脆性(precariousness)就可謂是存有的前結構:生命總是在流動不居的社會關係中,隨時隨地被形構、定奪或排除。而值戰亂環境,實際發生或隱然將臨的傷害(injuries)都讓人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脆弱(vulnerability),以及主體與他者之間無法擺脫的依存關係。
建基於此,巴特勒探問的是,社會上各種暴行乃至戰爭,是如何將某些生命進一步納入危脆化的處境,使其彷彿不再被視為生命?她指出,暴力、正義與戰爭這些概念,都是在框架(frames)之中被理解和被詮釋的。框架意味資訊的限制和篩選,亦往往存在溢出個體的交涉和協同。這些框架可以是性別、身分、階級、國族、種族、宗教經濟利益、政治意識形態與歷史位置等,比起從主體意志出發的視角(perspective),更接近某種從外部框構的視域(horizon),總是決定著我們接收得到甚麼。而戰爭的框架,就是關於差別化評估的控制,它總是嘗試操控框架內的生命,將特定生命視為較低級、較不重要,甚至不成生命——我們理解到,戰爭問題,就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問題。當某些生命陷入這種被排除的威脅中,就成為了所謂危脆生命。
戰爭與暴力的框架都在控制人的感官(sensation),並企圖捍護某些生命,而排除另些生命,或不再將其視為生命。按此理解,所謂正義戰爭(just war)或正義暴力(just violence)只是相對的,因為正義本身也總已在框架之中被詮釋。巴特勒指出,這些框架時常納入在國家的話語統識文法(hegemonic grammar)。在國家需要「出師有名」地行使暴力或發動戰爭時,往往會運用其權力大加渲染、操作和界定這些框架,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保障社會安定繁榮」、「維護國家安全」云云,或以「黑暴」、「恐怖主義」這種話語套在反抗者頭上,總是操演著反抗者罪證確鑿的敘事。不願越出框架思考的人在耳濡目染之下,自然會深信自身或國家行使暴力或發動戰爭,都已具備充足的道德正當性,彷彿敵我之間壁壘分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要命是,總覺得自己就是正義的一方。
巴特勒點明,正是這些框架,造成了大量危脆生命。要抵抗這些框架以挽救危脆生命,她認為關鍵在於激發社會上更豐沛的情動(affect),扭轉人們對危脆生命的冷漠(indifference)。這裡所謂激發情動,不是簡單一句「動之以情」,就相信不平等的現況能被改易。我們必須回到危脆性作為存有的前結構這個洞見,循序漸進展開深思,才能理解巴特勒語境下的情動,具備何種積極的政治意義。所謂生命的危脆性在於,主體總是暴露自身,依附於他者的承認(recognition)才得以存在。而來自他者的承認所形構的規範(norms)乃至制約(regulations),同時生產和消解著「人」的概念,於是出現不同框架,將某些生命排除在承認之外,使其遭受無效化(unlive)和非人化(dehumanize)。
誠如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所說:「唯有危險之處才有拯救。」傷害能夠發生,固然得益於生命的危脆性;但挽救危脆生命的契機,也正在於擁抱生命的危脆性。在社會中,與他者之間不可逃避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總在鬆動自我的邊界,而這種連結關係的最基本方式就是身體。是故當巴特勒談到(危脆)生命時,它就總是身體性生命(bodily life)。生命無法脫離身體被理解,但這身體卻不僅是佔據特定物理空間的自然實體——當然,從這個由細胞、血肉、骨頭等組成的實體,我們都能察知其脆弱,並總是暴露在隨時可能遭受他者傷害的危險處境——我認為巴特勒談的身體,更是情動身體(affective body)。身體總是發出和接收著情動,是某種難以辨識我他邊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狀態。巴特勒就曾與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共同指出,自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以來那個尋求承認的主體,其實總已先向他者訴說著:「成為我的身體」。
若再推進下去,不難讓我們想起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肉身(flesh)的界定:肉身並非主體,而是我他之間那片中間性(inbetweenness)的領域;主體性並不建立於特定實體,而是潛藏於這個情動流變的肉身之內。回到巴特勒的理解,由於身體不再歸屬任一主體,而總是在社會關係中揭露其危脆性和關係性的本質,我們不難想像,對任何他者行使暴力,其實都是同時在對自己行使暴力。於是《聖經》中「愛鄰如己」的誡命,甚至不再是難題,只是我們往往尚未發現「愛鄰」就等於「愛己」,他者與自我總是共享著「一個身體」。
按照這種理解,擁抱生命的危脆性,絕非等於主張懦弱、消極或「認命」。當強調生命總是在社會關係網絡中被承認的本質(而不必建立於任何先驗道德基礎),是他者先於我並支撐著我的存有得以延續,我在體會到自身生命的危脆性之同時,也就體會到他者生命具備同樣的危脆性。於是當我將他者的生命軌跡置放於時間中理解,則察覺其無常(ephemeral),極為輕易便會逝離。這時,藉由擁抱危脆性,我們察覺到的其實是所有生命都具備可弔唁性(grievability)的本質,即總是值得我們為著其生機勃發的可能性(Möglichkeit)之逝去而感到哀慟,故可弔唁性亦作為生命潛能被理解。
在此除了施賓諾莎(Baruch Spinoza)倫理學的影子,更明顯可見的是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他者哲學,事實上在同名章節〈危脆生命〉中巴特勒就大幅引用並解釋之。列維納斯認為當我們面對脆弱並痛苦的他者臉容(visage)之際,(作為情動身體)就總已不可抵抗地被激發了某種責任(responsibility),亦即無盡的回應能力(response-ability)。自我被納入傾聽的位置,而他者則總是先作為語言向我表達其痛苦,然而來自他者臉容的痛苦表達卻又注定難以辨清,亦無法言明——在此巴特勒有機地連接了列維納斯與拉岡的他者理論。而既然從出生起人就活在必須回應他者的託付關係中,即其存有前提就已是脆弱的倖存餘生。臉容「作為他者的極端危脆性」不可窮盡也不可涵括或再現,總是保持神秘地阻擾和摧毀我的意志,以自身的脆弱暴露於我,引誘我謀殺它的暴力與我必須保護它的情動之間始終存在張力,構成我的焦慮不安,終止我的自戀迴圈——我從最初就是他者的人質。
這種列維納斯稱為「主體際身體關係」(inter-subjective bodily relation)的「他者>自我」不等式,是故懸置了施賓諾莎式的生命慾力(conatus),自我總是落入被動位置。我們或許可以說,巴特勒在接受列維納斯的觀點後,身體的意義就被改寫成:首先被觸動然後在他者迫脅下富於觸動地回應的潛能(capacity of first being affected then responding affectively under the persecution of the other)——或用書中的話:「身體從一開始便被託付給滿是他者的世界,留下他者的印記,並在社會生活的種種交錯之中形構而成。」這種潛能讓「我」可與「你」共情,並能夠「在『你』之中表現出超越於『我』」。
巴特勒將從康德(Immanuel Kant)到鄂蘭(Hannah Arendt)一直強調的「人的尊嚴」扭轉成某種被動表達:人總是首先被脆弱易碎的有限模態所觸動,然後給予回應。我們也許沒有道德義務尊重他者(雖然生命的危脆性總是向我們施予義務),卻必然有責任回應他者,這種責任就內在於這個總是為他者所先決建構及重新劃分的「我」——哪怕這種回應有時只能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式的沉默,但無論如何,都總是在知悉著(knowing)危脆生命,或說,感受著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戰爭的框架總是決定著某些生命不值得活,故也不值得哀悼,比如巴特勒書中提到在「九一一事件」後僅十天美國政府便宣布公共弔唁已然結束,必須以「反恐怖主義」行動取代之,隨之而來是牽連數以千計的秘密拘留、逮捕、查問與監禁。
當公開弔唁竟變成對國家政權所框構之公共領域的冒犯行為,當中的危脆生命就再難被人們看見。巴特勒指這種手段可稱為去現實化(derealization),即將本來鮮活的生命變成無所謂生死的空洞數字(甚至數字也沒有),彷彿他們不曾在現實活過。我們對此暴力並不陌生,如今在某些特定日子,只須身穿黑衣、手持燭光哀悼逝者都可能成為「違法」的證據,又比如在前幾年的疫政之中,多少珍貴人命都以林林總總的原因,遭受軟埋封鎖。巴特勒寫道:「這類禁止,以軍事目標與實踐堆砌出某種民族主義,與此同時壓抑任何可能揭露此暴力帶來的具體效果之內部異議。」禁止公共弔唁,就是政權只為鞏固其民族主義框架,選擇蔑視人命的鐵證。而選擇擁抱生命的危脆性,就是主張恢復人承接哀悼債務的能力,將「平反」從「復仇」中區別出來,再次弔唁那不可弔唁者,以真誠的生命情動,對抗與極權同謀的冷漠。
在〈無限期拘留〉一章,巴特勒展示了國家以去現實化手段造成危脆生命的另一面向。「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在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大規模濫捕與盤問大多非屬於美國公民的阿拉伯、穆斯林及來自中東的男性,當中部分被無限期拘留至今。這種未審訊先還押的刑事拘留,實際上就是國家操行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模型。現代主權底下的官僚(甚至蔓延至與特定民間勢力合作),得到實行片面決策的權力,同時不受法律問責,巴特勒指,這正是無法可言的流氓權力(rouge power)。當政權任意釋法,實則就懸置了法,讓其成為主權本體的純粹表達,效果是「無限制地結構未來」。而若認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洞見,即學生運動的核心立場就是將未來從過去的框架中解放出來,讓青年本身完成形而上學,那就不難理解,為何某些政權會特別打壓學生運動,也不難理解在特定框架中那種「教仔」論述與開槍射殺反抗者,竟顯得並不矛盾。
「依存是脆弱性的根基,亦是集體抵抗的根本。」巴特勒認為當我們擁抱人與人之間的依存關係,拒絕蔑視任何生命的可能性被剝奪的痛苦,這種脆弱的「身體之重」(bodies that matters)便會成為政治能動力的實質來源。從情動身體本質上的組配(assemblage)到人們的集會(assembly),都是權力意志的交涉場域,亦是政治的場域;而脆弱的身體性生命,確實也往往造就或展演(perform)了各種充滿生機的政治反抗手段。巴特勒指,立足生命的危脆性所展開的政治反抗,就是「非暴力的力量」。這並非指一般語境「和理非非」中的「非暴力」,即並非暴力的缺席——而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質疑,這是否等同本雅明提出的神聖暴力(divine violence)也有待商榷——在近年著作《非暴力的力量》(The Force of Nonviolence: The Ethical in the Political)中她劈頭指出「非暴力」應被理解為「抵抗的實踐」與「戰鬥的和平主義」,是堅韌流動的基進纏繞運動。
我們可以說,這種力量是源於情動身體的力量,總是作為「流變—非暴力」(becoming-non-violence),即總是在趨近、傾向並通往非暴力的中間狀態表現(expression),總是隨時、隨處、隨意的,總是未完成而朝向未來的皺褶開展(explication)。巴特勒點出,非暴力是「義憤」力量的實踐,緣由他者臉容呼喚我「以他人為名、為他人感到憤怒」。我想起我老師黃國鉅在《酒神的抗爭》中寫到:「(對不義的)憤怒會慢慢轉化為關懷、愛,愛知識、愛理性、愛我們的地方,這種憤怒是值得長期保留的。」對巴特勒而言,非暴力的「義憤」固然亦指向上文提到的愛,且這種愛必然是對生命與對世界的愛。
面對戰爭的框架,巴特勒主張反戰。反戰不是犬儒式的避戰或非戰,而是反對就生命等級的劃分本身,即反對某些生命比另些生命更值得死。對巴特勒而言,反戰的前提就是某種意義的平等主義,是始終尋求更適當地平等分配社會上所有生命維持其生活的條件與資源的政治倫理願想。如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主張,不可傷害他者的要求總是與平等理念並置理解:「誰才算一個我們不能傷害的他人?這裡,基本平等的理念再一次發揮了作用。它要求任何人都被視為同等重要的。」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加害者—受害者」的對立邏輯,理解生命總是共住(cohabitation),從而「想像一個暴力能被極小化的世界」。
是故,比如公共弔唁、遊行示威、街頭抗爭,或重劃城市空間的涵義,這些非暴力的勇氣,都是生命之危脆性的身體性展演(bodily performance)——誠如列維納斯點明,身體總是蘊藏著不可蔑視的流變力量——繼而尋求安那其式共同體的勇氣。每次擁抱危脆性的公共行動,都在激發著社會的情動,是情動身體冒上風險以小博大:它一方面無盡地承擔本雅明所謂被壓迫者的趨光特質或列維納斯所謂的他者臉容;一方面不斷動員蔓延,總是邀請著更多生命不再冷漠,加入對抗從個體到國家的自戀主義。這種發乎情動的脆弱政治,洋溢著列維納斯所謂超出自身的激動(émotion),卻不流於情緒化(emotional)的宣洩,而是以甘願捨己之赤誠竭力保存社會上的「異議狀況」(the status of dissent),不懈揭露任何被剝削的危脆生命。而如何對待不同異議,並主動提出異議,觸發人們的熱烈情感與清醒反思,這正是人文學科長久訓練的「修養與批判」,也是處身當代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ies)精神,一如巴特勒所寄望:「回應當前特定的時代,更是回應前所未有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