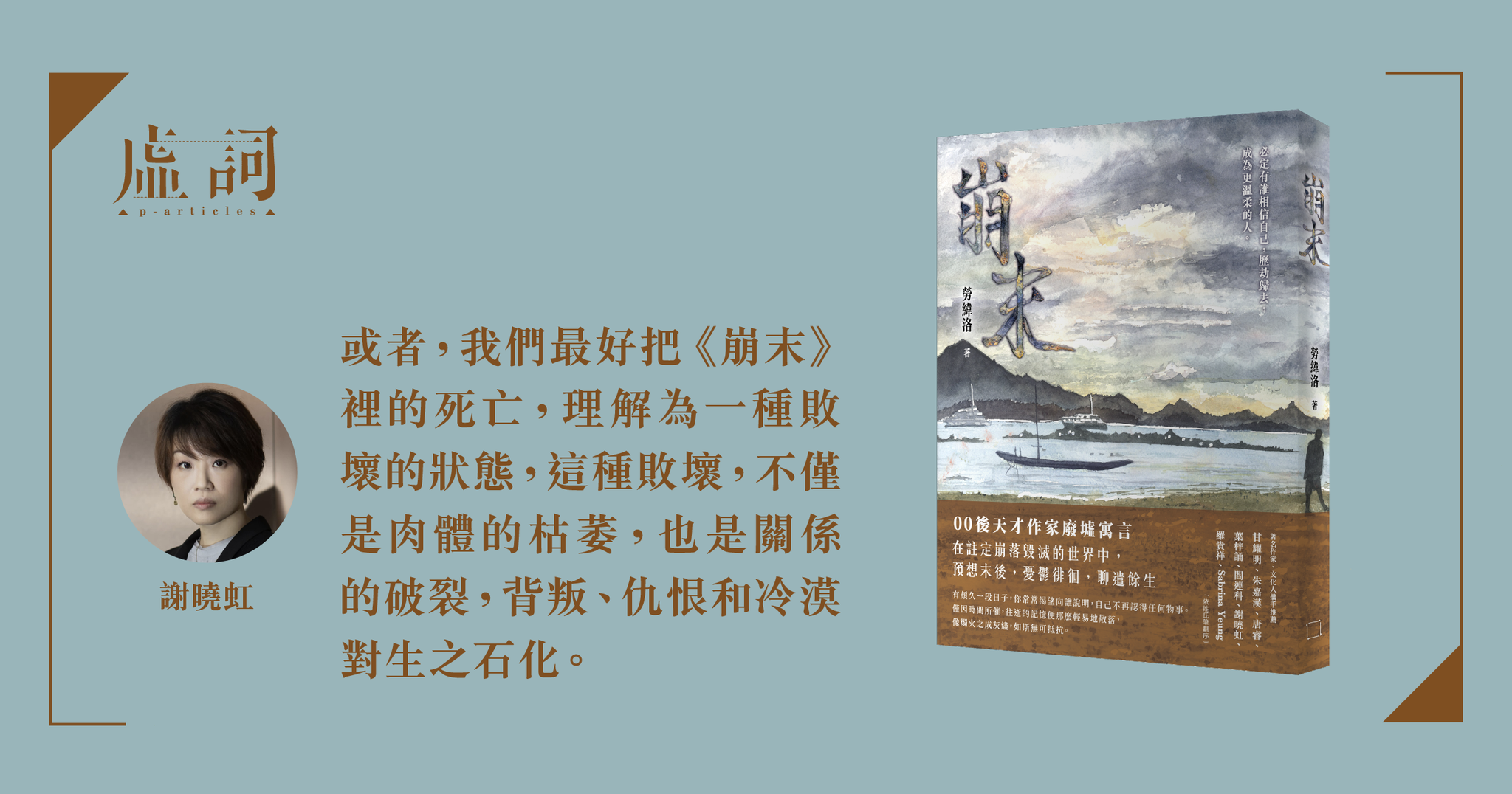【新書】一種史詩英雄的征(歸)途——讀勞緯洛的《崩末》
《崩末》是一個具野心的文本,其實驗性的文體抗拒被界定。但我決意把它讀成一部史詩,不僅因為它詩化文字所追求的莊嚴與神聖,也因為其中半人半神的英雄,以及祂/他在自身所連結的文明歷史及其崩壞裡,渴求的救贖與超越。如果我們認同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視「豪壯」(heroism)為史詩的核心,它的氣質是不懈的意志與叛逆,則《崩末》完全可以放在此一傳統中閱讀。
緯洛下筆皆是廢墟,死亡的陰影處處,直透出頹唐與虛無。全書分成四部,第二部〈古老的索引〉寫及一場少年與怪物的大戰。少年英雄身披金色鎧甲,一把金刀懸在腰際,然而,理應壯烈的場面,讀者還未分辨出敵我,大戰還未開始,竟然便已悄然結束。我不禁想起余華寫於八十年代後期的短篇〈鮮血梅花〉——武俠小說裡的復仇者被寫成一個喪失意志的空殼,只有行動沒有靈魂。借由一種古老的文體,余華突出了後文革時期的價值真空;劍上暗淡的梅花,指向一個失落的文化傳統。然而,勞緯洛並非余華,《崩末》出現的歷史語境也不是一個價值信念被完全摧毀的社會。在一片廢墟之中,緯洛反而突出了一種精神意志,傳達出強烈的意義渴求。
《崩末》勾勒怪物和少年對陣,「金光閃動,黝黑的爪」,一個印象式影像過後,筆鋒隨即轉入更為內在的叩問:
該是這裡了。你知道嗎?只因此更裡面的殺生之心,我們已經不可能,回到原來屬於生者的世界了。
在這場決戰之中,究竟是少年還是怪物被殘酷地殺死?生與死、勝與敗,甚或怪物與英雄的界限,在「他」的追憶裡,竟變得異常模糊。
《崩末》的英雄原型可以追溯到緯洛在十八歲以前出版的第一本小說,《卷施》中的孤獨少年,一個複疊著太宰治、郁達夫等作家印記的零餘者。在〈作家〉一篇裡,來自破碎家庭的少年同時開展了肉身與精神層次的旅程,他從城市乘火車返鄉,但他的精神故鄉,卻似乎只存在於他偶然看見的一幅畫裡:
我想起了老家,想起了夢——一些早已忘記,如歲月依稀的夢。
那裡有山、有海,有彩色的雲和天空,有日出、也有夕陽。那裡有微風在低歌,有花兒、有鳥兒,還有一個面向大海、孤獨佇立的背影。
這個指向精神故鄉的夢中之海,在《崩末》裡以更夢幻更奇異的形象出現——「海會迷人,祂懂得呼吸,會疼痛,像抱著你哭泣的她。」「海是海神的身體,靜對礁石度度轉還,是未被旁人追認的故鄉。」而朝向它的孤獨背影,那個自卑的零餘者形象,則脫胎出一種英雄亮光;被排擠的少年,體現出西西弗斯(Sisyphus)的精神意志——「就好像,我在兩邊都是高山的,一條很窄的路,太陽很毒熱,而我只有一個人,推著車,把石頭推上山頂。」
只是,不同於我們印象中的西西弗斯,《崩末》裡的少年並未被拋擲到完全孤絕的世界。在他推石上山的回憶裡,竟出現了想要與他同行的母親。而〈作家〉裡,少年對母親殘缺不全的記憶,他與冷漠父親的疏離對立,以及情人對他的背叛,幾乎都在《崩末》裡,得以重返與修補,彷彿回應了緯洛在《卷施》另一篇〈畫家〉裡提及的,有關救贖的問題:
單單從眾我尋求至自我,其實是不可能得到救贖的〔⋯⋯〕真正的救贖,除了需要抽離於眾我而進入自我境界——你作為畫家所說的詩境畫界之中沉思默想,更重要的是要本著救贖之理,拔心重生,再次進入眾我之中,而永不倒退於故在。
緯洛曾經表示,如果他沒有選擇寫作,很可能會修讀神學,成為牧師。從《卷施》到《崩末》,緯洛關心的始終是宗教性的主題:人類的救贖。而從他近年的文章看來,他所思及救贖的關鍵,正是如何與(已逝、不在場的)他者連結,如何使「愛」變得可能。
緯洛曾撰寫長文,引介被稱為「有神論存在主義者」的加百列.馬賽爾(Gabriel Marcel)。雖然緯洛對他的一些觀點不無質疑,但卻肯定了其建基於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愛的形上學」:
馬賽爾帶領我們認識到,現象學並非必定是冰冷的主體意識,存在哲學亦非必定將鄰人看成地獄,而是出於對光的渴慕,我們或就得以邁向一種強調愛與忠信的主體際性奇蹟,由此真實地體會他人於我生命中不死的臨在。
馬賽爾思想回應的是兩次大戰的殘酷滅絕,而《崩末》同樣隱晦地提到一場波及沿海小國的戰爭。只是,書中提及的死亡,並不僅僅來自戰亂。《崩末》反覆書寫少年家人老去的垂死時刻,而他生命的重責,似乎就是為了背負這些死亡的記憶,帶同所有逝者存活下去。我權宜把《崩末》的男主角稱為少年,但在作品曖昧的時空結構裡,「他」(以及其他角色)的反覆出現,卻如輾轉多世。讀者閱讀《崩末》的經驗,正如他對處身迷宮裡自身的觀照:
不知從哪個節點開始,瞥眼間,他察覺自己能夠看見有些影子,若即若離在追隨身後,有時是佝僂緩行的老人,有時是僅及腰高的小孩,有時是風塵僕僕的中年人,有時是與他年紀相約的少年⋯⋯而若細察容貌,該會發現,那全是他自己。
事實上,我們很難把《崩末》裡出現的諸眾,看成傳統意義上的人物。令人物邊界更為模糊的是作品裡頻繁的人稱轉換。緯洛鍾情高行健的《靈山》,而《崩末》的人稱處理,的確可以看到《靈山》的一些影響。危令敦在《一生二,二生三:高行健小說研究》一書裡討論《靈山》的「多人稱敘述」(muti-personnarration)時,指出其法國新小說的根源。它們關心的不再是「人物」,而是要「呈現無名或匿名的主要角色——特別是它們無法界定、難以捉摸的主觀意識與視點。」在《靈山》裡,這種難以捉摸的意識,僅屬於小說中的男主角,而「男性角色想像之異性,在敘述層面的功能位居次要。」在《崩末》的多人稱敘述裡,女性的「她」卻不僅是男性主角思想的派生物,不純然是「他」幻想的「她」者。就像以下這段描寫情人親密互動的片段,人稱的轉換,促成了變向他/她者的流動意識:
仔細為她抹拭身體時,你低著頭,用一種很沉的聲音說,有一瞬間,我覺得我幾乎成為了妳。看見窗外,好像有海鳥飛過,她知道夜晚就要下雨。成為了我,他說,那是不是我們能夠互換肉身,感受彼此傷痛。
《崩末》變幻莫測的時空結合人稱的轉換,使得情人一下子幻化成母親、英雄轉眼換成了怪物,而少年能一躍成為父親。擺盪於不同人稱之間的,並非某一主觀意識的流動,而是眾多不同意識之間的震盪與和鳴。或者,我們最好把《崩末》裡的死亡,理解為一種敗壞的狀態,這種敗壞,不僅是肉體的枯萎,也是關係的破裂,背叛、仇恨和冷漠對生之石化。而真正的英雄,並非立在怪物對面的「他」,而是書中如海浪一般,低吟掙扎著想要把生者與死者連結起來的流動意識。
我認為緯洛的文體實驗,終極目標乃是一種哲學/神學(如何回應此一時代)的探問。正如馬賽爾「愛的形上學」,它關心的是如何衝破主體的界限,在「我」裡面看見潛在的「我們」,邀請(已逝、不在場的)客體成為「你」而臨在。
〈古老的索引〉一章裡出現的海神、怪物、少女(公主?)和少年形象,他們的糾纏關係,很可能脫胎自有關海怪(海神?)利維坦(Leviathan)的傳說,或更早的迪阿馬特(Tiamat)創世神話——屬於深海的雌性混沌力量被降服、其身體被砍殺,化成天地,雄性的文明秩序才得以建立。在《崩末》幻影般的敘述裡,讀者不易辨識,在海神、少年和怪物之間,究竟是誰揮動金刀、誰被殺死。然而女性的她,正是在此際告別赴海,在雄性的世界裡退場消失。《崩末》同時也是對此一神話的質詢與改寫:時間不能理解為由混沌到文明的直線行進,相反,「在這裡,故事無可避免地,需要歧裂成了兩段時間。」
迎戰怪物的英雄,曾抱著「為了自由」的信念,想要「以一人的死亡」,換取他人之生。但《崩末》的真正英雄,顯然並非此一捨身之人。如果就像海神所說,「戰爭一旦開始,哪怕只要有一個人死去,就永遠不會終結。」那麼戰爭的勝算,不在於擊敗敵方,而在於把時間撥回到戰爭開始以前。少年手執金刀,其理想並非殺生,為血腥的歷史多添一朵梅花;而是要消滅戰爭本身。因此,我們的英雄需要的不是行動,而是沉默停駐,「以他琥珀色的雙眼,像孩童般專注地,凝視著金刀」,看清楚刀面上所銘刻的「世界原樣」。
而對「世界原樣」、永生與愛最深的威脅,正是一種馴服於雄性文明的線性時間觀。《崩末》的英雄少年從小學開始便沉醉於迷宮的建造,為的是要在其中放置「每一個他想見的人。」通過迷宮對時空的重組,他能「抵抗時光的風暴,重臨在他們身邊。」重臨,正是要回到故事分裂前的原初——「要建設的這座迷宮,各種出其不意的路線,最終都指歸起點」。
這種返回原初的渴望,體現在《崩末》自由穿梭於回憶與夢的流動敘述,已經破裂的關係因而有機會被回溯與修復。而關係和解的終極,即「我」和神的相遇。《崩末》第一章〈神〉開始於「淵面幽暗」的創世場景。在此,創世卻並非指向神開天闢地,而是在「我」意識內部進行重新啟動:
當我再次醒來,我會挾帶著上一次睜開眼的時候,所看見的最後一個畫面,就好像剛誕生的嬰雛,在海的至深處,重新習認這個廣邈世界的一小角落,隨浪濤推擁,徐緩地浮近水面,長出四肢,仰頭指向繁星。
《崩末》引領讀者體驗的「原初」,總是已經帶有它的前世記憶。回歸,也就是重新出發,背負著另一段「永被截割、被捨棄,作為交換而墮入迴圈,被永遠遺忘」的故事時間;在記憶中召喚,已經沒入了海中的她,或曰潛在的眾數的「我」。

◤勞緯洛《崩末》
勞緯洛以敘事構築《崩末》的環形迷宮,在其中所有已逝的人和事能夠再次相遇。當世間注定崩末,過去注定無法捕捉,唯有在文學裡我們能想像一種永恆的時間,讓沉默和傷害得以安放。唯有遠離現實,才能更貼接現實。將寫作還原為一種手勢。《崩末》是勞緯洛貫徹其餘生書寫的一次重要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