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像西西這樣的一個女子】象是笨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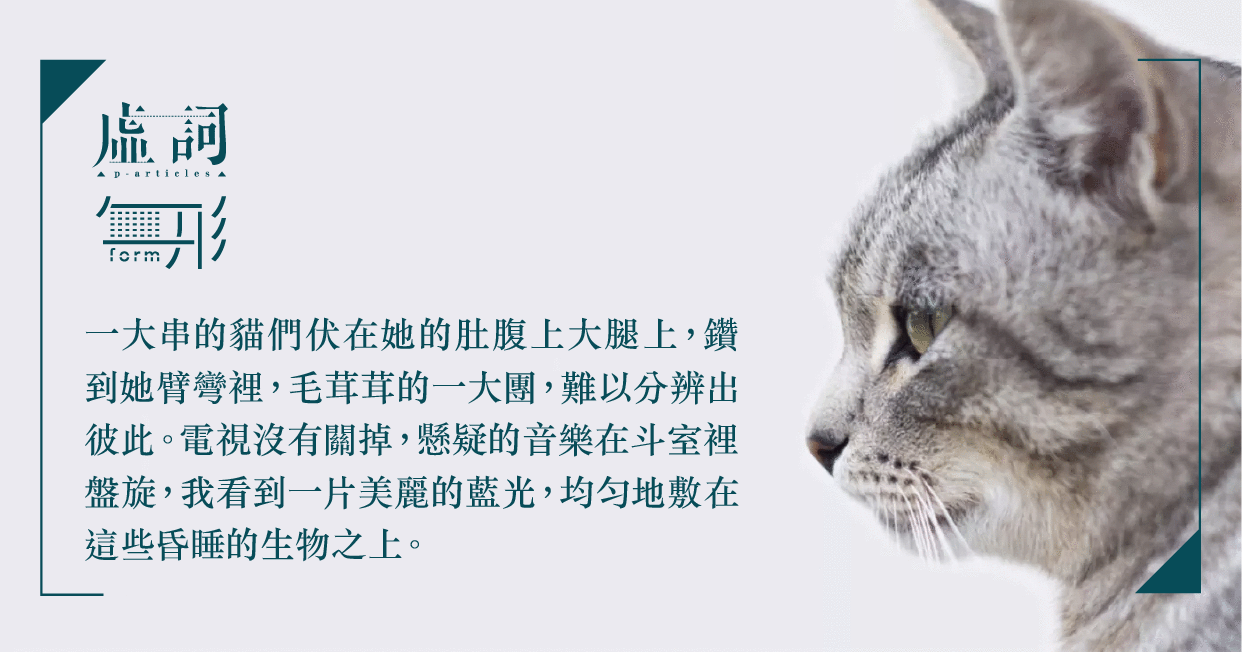
329051086_869533114338520_5396843835796230438_n (1).png
我叫阿象,今年二十二歲。警察問我,我就這樣回答。為什麼到這裡來?我其實也不太清楚。我不應該再走上這條路的。這條我在動物管理局工作時,常走的路。辭職的時候,我便下定過決心。這倒不是因為,我有多麼討厭我的工作。只是,走在那條路上時,我不免聽到一些令人悲傷的聲音。他們拿了我的證件,低下頭在一本筆記本上抄寫,彷彿正在做著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我知道,他們什麼都沒聽見。
你回來了?坐在接待處的阿豆沒把他的臉從電腦熒幕前移開。我們從前非常要好,我以為看到我回來,他會更興奮一點。
──可以進去看一下麼?
──既然都離開了,為什麼呢?
我在阿豆面前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來,想起了兔子——或者,其實是因為兔子,我才決意不再回。我記得,有一天,兔子像往常一樣,給我買了貓糧,蹲下來,和我一起逗貓。她低著頭,專心地搔弄著貓的脖子。「你說,我們的孩子出生以後——」兔子後面的說話,我沒有聽清楚。我知道兔子沒有懷孕。但我的腦裡剎時出現了一個畫面。背景是掛在露台上,一列正在等待晾乾的衣衫,前景是一個腹大便便的女人。那女人朝我露出一個太美好的微笑。一定是在哪齣電影裡看見過的畫面,但我竟嗅得到洗衣液的氣味。我估計,在那個地方裡,我和兔子應該可以養一到兩隻貓,最多三隻,但絕對不能是七隻。
是的,我養了七隻貓,就在那個不到三百呎的房子裡。每天回到家,我就會聽到此起彼落的叫聲,牠們一個個從暗處冒現。紅燈黃綠青藍紫。那是我幫牠們起的名字。如果再來第八隻貓,我應該給牠起個怎樣的名字?你這樣喜歡貓啊?兔子第一次到我家裡來時這樣問。我苦笑了一下,在動物管理局工作之初,我其實連一隻貓也沒有。在那裡,我的工作是點算每天被送進來的流浪貓狗,有時也會有野豬、猴子、蛇和不能飛的鳥類。我走近牠們,嘗試給牠們餵食,記錄牠們的反應,判斷牠們是否有攻擊性。對於受了重傷或患了重病的動物,獸醫很快便會來把牠們帶走。剩下來的,如果被判斷具有攻擊性,也就是不適合被飼養的話,在來到這裡的第四天,就會被「人道毁滅」。
什麼生物不會對陌生者抱有戒心?尤其那些在街上流浪,或曾經飽受殘酷對待的動物,除非失去了生存的意志,怎麼會不盡力顯示牠們的攻擊性──即使牠們本身早已不堪一擊?我沒有像其他同事那樣,急著向牠們餵食,要牠們立即馴服。那頭新送進來的芝娃娃,似乎兇得不得了。我只是蹲下來,伸出手掌,等牠來嗅。牠猶豫了好久,但嗅過我的氣味後,我餵牠什麼,牠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們覺得很奇妙,以為我是什麼馴獸師。事實上,只要能交換互信,誰想要冒險進擊?只是,四天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被判定具有攻擊性的動物,會被帶到另一個房間,由獸醫往牠們的脖子裡注射毒藥。那一次,不遲不早,那隻牧羊犬的主人剛好來到,看到了牠的屍體。牠那些金黃的毛髮也太漂亮了。那怎麼可能?她掩著面。我後悔沒有說,讓我來收養牠吧,就像我收養那些貓們,即使我只有一個不到三百呎的房子。如果你早來一步就好了。他們這樣對狗主人說。我走出房間,不想聽見她的哭聲,但那種悲傷的聲音,其實早已經刻進附近的空氣裡——或者,確實是因為不想再聽到這些聲音,我才決意不再回來的。
現在,我每天聽著冷氣房裡機器震動的聲音,同事們快速打字的聲音,偶爾有人伸個懶腰,問我們午飯吃些什麼才好?我很高興,吃飯的時候,我沒有想起那些動物變得冷硬的身體。而我的同事都說我太幸運了,剛好趕及在大流行前換了工作。那些流浪貓狗會傳播病毒,動物管理局是高危的地方。是因為這樣,阿豆才生氣了的吧?在大流行的時候,我拋下了他。
阿豆似乎沒有打算和我談話,我終於起身,走進了那些動物被暫時囚禁的地方。甫踏進去,近門處籠子裡的兩隻狗就朝我狂叫起來。我沒有嘗試去安撫牠們,因為我注意到第二個籠子裡,除了三隻貓外,還有一隻黑色的龐然大物,縮在一個角落。我走近去,才意識到那是個穿著一身黑衣的女孩。有一刻,我以為她是職員,但她的手腕上,卻套著和其他動物一樣的號碼帶。
──噓——你——怎麼會在這裡?
那個女孩抬起頭來,但散亂的頭髮讓我無法看清楚她的臉。
我把阿豆叫進來,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能把人關進籠裡?阿豆看了一下籠子,好像不明白我在說什麼似的。我不得不指著那個女孩說:她!我說的是她!她能是貓麼?阿豆臉上露出模稜兩可的表情。他偏了一下頭,彷彿在認真考慮。她確實是貓啊。如果你有看最近局裡推出的小冊子,你就知道,她是其中最危險的貓類之一。那一刻,我覺得阿豆或者在故意報復我。我不再跟他爭辯,而是回過頭去對那女孩說:你為什麼不自己開聲說話,如果你說話,他就知道你並非一隻貓。然而,那女孩只是搖了一下頭,我甚至不知道,在那些散亂的頭髪之下,她的眼睛有沒有張開來,有沒有在看我們。
回到家裡,我跟我的貓們抱怨這件事。在牠們喵喵的叫聲中,我心血來潮,到動物管理局的網頁上去查看,才發現那裡列出受監管的流浪動物,種類多了不少。有許多動物的名字,我根本連聽都沒有聽過,那些簡介裡,對牠們的描述也很含糊。第二天我再到局裡去,女孩已經被判斷為具有攻擊性。阿豆那天並沒有當值,一個我不認識的,叫做小菇的職員伸出了手來,讓我看她手臂上的爪痕。這樣吧,把「她」交給我。我說。你看看紀錄,就知道過去我收養過不少具有攻擊性的貓。小菇狐疑地看了我好一陣子,又自言自語說了些什麼,但終於還是把「她」交給了我。臨行前,我要求小菇把「她」手腕上的號碼帶子解下來。小菇搖了搖頭,辦不到啊。師兄,你沒有回來太久了,一切都改了啦。在這樣的大流行時期,我們不能放棄追蹤。
有好幾天,我擔心如果兔子到我家裡來,我該怎樣向她解釋,但我同時很期待她的到來,如果她看見「她」,或者就能證明,「她」明明不是什麼危險的動物。
我讓「她」睡在我房間裡,跟「她」說明放衣服和毛巾的地方;廚房有些什麼可以吃的熱水怎樣用,「她」既沒有點頭,也沒有似任何方式表示明白。廚房偶爾有被翻過的痕跡,餅乾盒子打開了,動物餅乾散落在盥洗盆裡;水滴滴的毛巾丟在地上,卻不確定是「她」,還是其他貓們。當我偶爾瞥進房間裡去,總是發現床鋪得好好的,似乎從沒有人在上面睡過。
兔子到我家裡來,已經是一整個星期以後。我們一面在廳裡吃著她外賣來的漢堡包,一面看著電影。那是一齣偵探片,在好幾個細節上我分了心,開始搞不清楚情節。我擔心兔子發現了會生悶氣,不過過了一陣,卻是兔子先說對不起,她太累了,實在看不下去。我到你房間裡去睡一下。她說。我來不及,也想不到怎樣可以阻止她,只是任由她自己推門進去。
兔子再次從我房間裡走出來時,臉上果然有些不悅,但卻沒有說些什麼,還滿足地伸了伸懶腰,似乎睡了一個好覺。我給她泡了茶,端到她跟前,她才問我:這件事還有什麼人知道嗎?
——你看出來有什麼不妥了吧?
——當然不妥,這樣的大流行時期。你居然還領新的動物回來。
——動物?你看得出她是什麼動物?
就是新納入被監管的動物。兔子言之鑿鑿地說。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兔子臨行時還再一次吩咐我,千萬不能讓鄰居看見「她」。
兔子走了以後,我推走進房間裡去。我看到「她」就坐在地上,手抱在胸前,冷眼看著我。我拾起地上那根釣魚竿似的貓玩具(它的一端吊著一隻毛茸茸的假老鼠),故意朝著「她」來回地揮動,表演著空中飛鼠。好一陣子過後,「她」果然伸出了貓掌,狠狠地撥打了它一下。看到我的玩具跌落在地上了,「她」終於笑了一下。此時,「她」站了起來,轉過身去,從我床頭那書架,挑了一本詩集,然後又重新坐在地上,似乎是津津有味地讀起來。
我本來想問「她」:所以,你現在並不是一頭貓了?但我沒有,只是打量著「她」白得泛青的臉,「她」的嘴唇脫皮,腳趾甲太久沒有修剪了,藏了不少污垢。「她」看起來確實就像是一頭受過殘酷對待的貓。
第二天,我如常換上襯衣,穿上皮鞋到公司裡去。午飯的時候,同事們提議到附近一家新開的日式料理店去吃午飯。我想也沒有想便點了烤魚套餐。或者太餓了,我把每一根魚骨都舔得乾乾淨淨。有一刻,覺得自己比「她」更像一隻貓,或者有天也會被列為被監管的動物。回到家裡,我想向貓們發表我的看法。不過,這天牠們對我的興趣缺缺。「她」似乎終於洗了個澡,坐在沙發上時,看起來比我更人模人樣。貓們居然都在沙發上一排坐好。電視上正播放希治閣的《鳥》,「她」和牠們的臉上都有著驚訝的神色。
我回到自己的房中,只想好好睡上一覺,半夜電話卻突然響起來。
──你老爸不是有一輛可以跨境行走的貨車嗎?
──是又怎樣?阿豆跟我說話的語氣,居然又像是老朋友一樣。
──內部消息,明天市裡就要宣佈了——你新收養的那隻貓必須被『人道毁滅』。目前,只是提到要毁滅這個品種的,但誰知道之後會怎樣⋯⋯
我下了床,腳一下子被什麼硌痛了。我覺得自己的腦袋還沒有完全清醒,瞳孔卻漸漸適應了黑暗。地上散佈著貓的玩具和幾雙髒袜子,但貓們都不在房間。我走出廳,發現「她」在沙發上睡著了。一大串的貓們伏在她的肚腹上大腿上,鑽到她臂彎裡,毛茸茸的一大團,難以分辨出彼此。電視沒有關掉,懸疑的音樂在斗室裡盤旋,我看到一片美麗的藍光,均勻地敷在這些昏睡的生物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