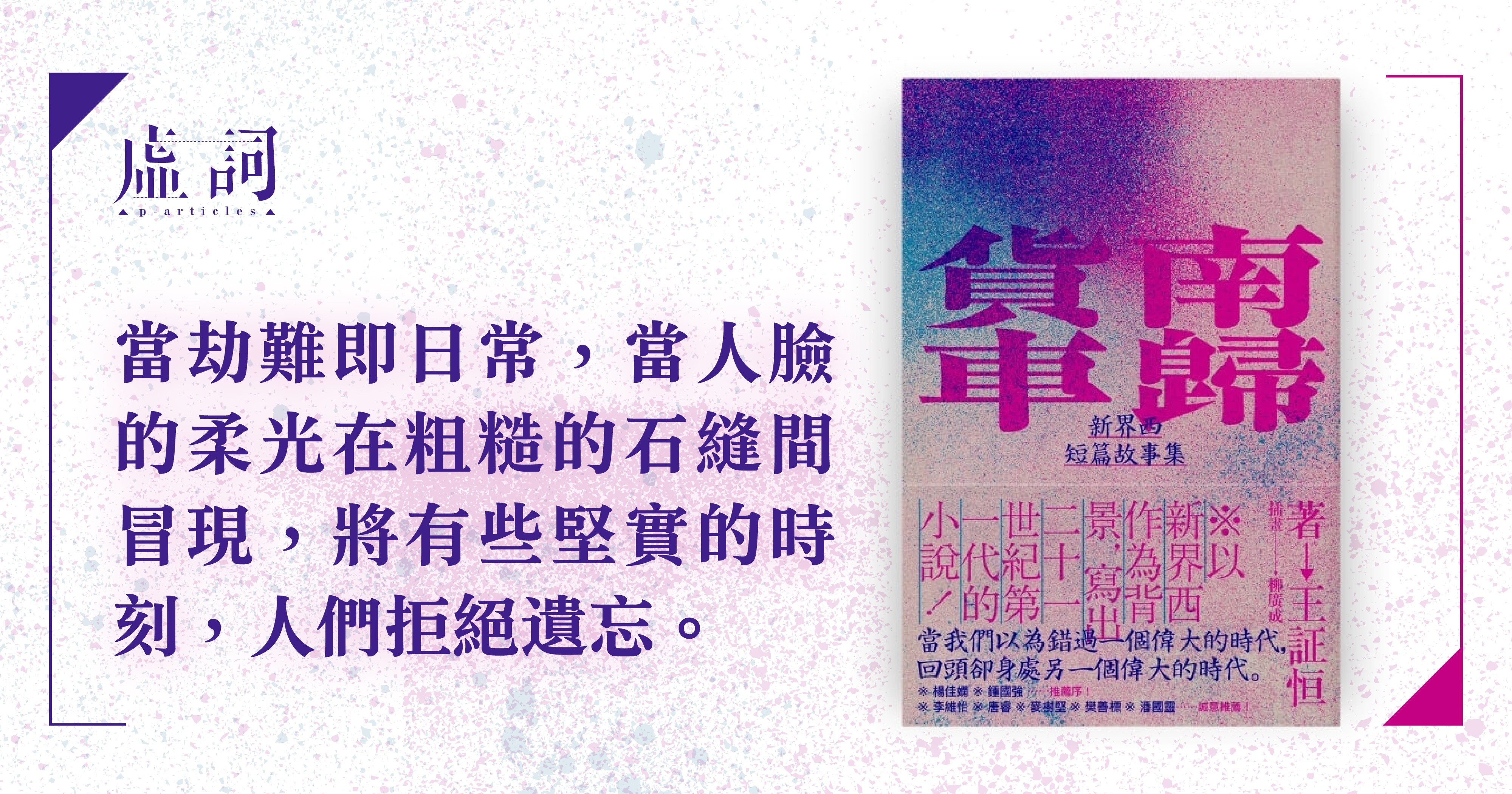暗礁時代.柔光之愛──讀王証恒《南歸貨車》
「他沒有看她的眼,打開了扣,低頭細心撫著她扁平的乳房,一陣荒謬的憐惜湧至胸中,他感到自己想哭,他撫著她。她又撫著他扁平的頭,像撫著一隻狗。」
——〈沉默的淤傷〉
「我隔著鐵閘吻她的額,將手伸進她的褲揑她的臀,沒太多肉,可以摸到盤骨的形狀。她也伸手到我的下身,以帶英泥的掌心撫著。」
——〈燒掉一棵綠樹〉
王証恒的《南歸貨車》讓我想起某個時期的賈樟柯──《任逍遙》裡到酒店偷情的小濟與巧巧,戲擬美國電影《危險人物》的色欲片刻,閃亮衣服脫下來,卻是貧瘠、令人哀傷的身體。社會虛幻的承諾,以一種荒腔走板的方式再現於灰暗人物身上,最令人震動的卻是,在一個山寨版的世界裡,我們竟還是看到了一絲還未被壓斷的溫柔,如此堅實,不容否認。
我在《南歸貨車》裡感受到的力量,正是來自人物都被壓到了骨頭扁瘦,但仍柔靭的情意;來自暴虐與瘋狂的邊緣,那抒情的微光。賈樟柯的抒情常得力於他綿長、一鏡到底,在遠鏡裡慢慢充盈的哀傷;《南歸貨車》的抒情卻不依仗遠景,相反,它的人物總是像昆蟲葉脈那樣,被放在顯微鏡下觀看。「震驚」是現代主義關鍵的美學經驗,那是資本主義時代裡麻木人群中難得的深情一瞥,但震驚召喚的與其說是愛,更多的是距離,在未接近前先意識失去與遺忘;《南歸貨車》的微觀美學背向它。
城市的異化,仍是《南歸貨車》的底色。異化意味著愛的剝奪──病危的哥哥,同時是市場裡「一個不再生產的人」,因此你再無法養育他(〈綠牆〉);你的母親養育你,但必須以兩個手提電話與兩種不同的謊言,活在婚姻中介與保險經紀的身分之間,並把你的號碼分配到一組客人之列(〈鼠〉);〈鼻敏感〉裡的妻、情人與「我」漸漸喪失曾經有過的親密感,正如他們作為報刊工作者,不得不懷疑自身的文字,不得不背向本來所執著的,企求成為公關、地產經紀,來為自己「贖罪」。然而,在連呼吸也失去真實感的世界裡,王証恒真正要注視的,卻是那些突然脫序、卸去皮毛,情感飽滿的秘密時光。情感的突擊,在堅硬的日常裡,分裂成歧路,使人物得以彼此逼視,並沿此為對方被否認的生命,重新灌注意義。
「如果遠方有一棵樹倒下,無人知悉,那麼這棵樹是否存在?」〈時光凝滯〉裡,兩個「偷」閑與「偷」情的教師,走到學校後山的荒野廢屋,對存在的懷疑,由一棵樹,返回自身──那個暑假的日常,他們被認可的存在,本是填充、虛構缺漏的課堂與會議紀錄,以供教育局檢視。偷來的時光稍縱即逝,小說時間卻讓它接近永恆──《南歸貨車》總是有那麼一個視點,沿著綿長的追憶,想要緊緊抓住情感遺跡的細節,致力銘刻那一點點由卑賤者共同創造,微小卻又巨大的柔情。
王証恒自成風格的短句被形容為「匕首」(鍾國強)、「乾脆而硬朗」(唐睿)。短句拒絕以連詞簡化事物的關係,拒絕為紛沓的世界匆促下註,卻區別於跳躍式令人驚詫的拼貼。《南歸貨車》的語言是一種高密度、低反差的運作。它的短句鋼硬,卻也柔軟,一絲一線,把爬蟲那樣被抹煞的人物,他們的氣息呑吐與風乾成鹽末的汗,重新編成一張參差對照的織錦,邀請讀者貼近來細看,卻也重拳出擊,以反向透視法,像阿然背上的天使紋身,向觀者步步進逼(〈虫豸〉)。在這張編織物上,新界西是一個交會點,匯聚湖北、福建、東莞……不同地域之間飄移的求生者。城市有時被稍稍推向後景,荒野生態卻被拉近,與卑賤的人物並置,成為「互為映照的廢棄共相」(潘國靈)。被廢棄者的生存狀態,卻又彷如異托邦式的鏡子,反照文明的殘缺──「我們的嗅覺就像螞蟻的智慧一樣弱」(〈狗哥〉)。《南歸貨車》的構圖法,把讀者的目光帶到資本主義邏輯的邊界上,那裡潛伏反抗的意志與生機,與文明的深嚴秩序對峙。
鍾國強在王証恒小說裡,讀到現實主義在香港「低調的一脈傳承」,卻讓他「心頭一震」。如果現實主義是辨認這種風格的起點,他顯然也意識到,《南歸貨車》正在解構某種刻板的「現實」。《南歸貨車》叛逆,然而它的視點卻始終沿雙面的人物分途,在毁滅與生存之間,在抵抗與妥協之間,保持著跨界的視野與矛盾。現實在這種視界裡被軟化為一種流動的狀態。《南歸貨車》的人物不能被他們的階級定義,沒有被釘死在固態的處境裡。小說並不容許讀者以俯視與廉價的同情來看待他們。這些人物尚存柔情卻並不天真,貧瘠卻並未被剝除慾望。他們憤怒、掙扎,把卑賤的處境,反向定義為力量所在。狗哥如是說:「又黑又瘦仍能在狗群中生存,證明他有智慧」。(〈狗哥〉)
王証恒在一篇訪問裡說,他想要結合「浪漫的抒情」與「現實的批判」。我理解這種浪漫與中國大陸某個時期裡的革命加愛情公式背道而馳。《南歸貨車》的浪漫,無論革命或愛情,皆不追逐宏大而不免空洞的理想,那是被踐踏到底後的反撲,是疲憊肉身逼近時的互相凝視。〈綠牆〉裡,在運動頹敗後瘋掉並死去的哥哥,或者是小說集裡唯一的理想主義者。他如燈,讓人們在窮巷裡幻想雨雪的首都,讓人在蒼蠅身上看到了螢火蟲,讓敘述者仰視與懷念。然而,理想如此容易被擊潰,鬥爭終止,「我不敢想像如果哥哥沒有瘋狂,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小說並沒有把希望寄托於一堵遠觀的、恆久的牆,而是爬在其上,枯黃的蕨類植物,那是靜候雨季再來,一點一點殘存的沁綠苔蘚。在另一篇小說〈虫豸〉裡,是曾在「我」耳邊響起,蒼蠅的低頻聲音(不是想像裡的螢火蟲,或首都),使「我」與安逸的日常拉開距離,使「我」無法忘記,順滑亮麗的體制掀開來,每個人同樣卑屈的粗礪真實。《南歸貨車》有一股蓄勢待發的自由能量,孕育於對殘酷真實的直觀。如是,在與狗哥結伴的日子裡,援交少女的新視野,竟在最黑暗處滋長(〈狗哥〉)。
我記憶中某個香港,是電影院椅子的塑膠臭味,在可疑的光影裡,人們集體地向著濫情故事爆笑。那笑是冷的,意義戳破,流泄出它的空洞。那裡有一種拒絕相信,對於價值,以及深度情感的否認。那是一個時代裡的清醒與智慧,卻不無殘忍。我在王証恒小說裡讀到的,是清醒的冷漠與天真的投入之間,另外的進路;一種置諸死地而後生的認知,以及對城市牢獄裡被隔絕的人進行的深度觀看。《南歸貨車》的出版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它不單見證了一個作者的敏銳與天賦,也見證了他如何抓住一座城市的變化。當刧難即日常,當人臉的柔光在粗糙的石縫間冒現,將有些堅實的時刻,人們拒絕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