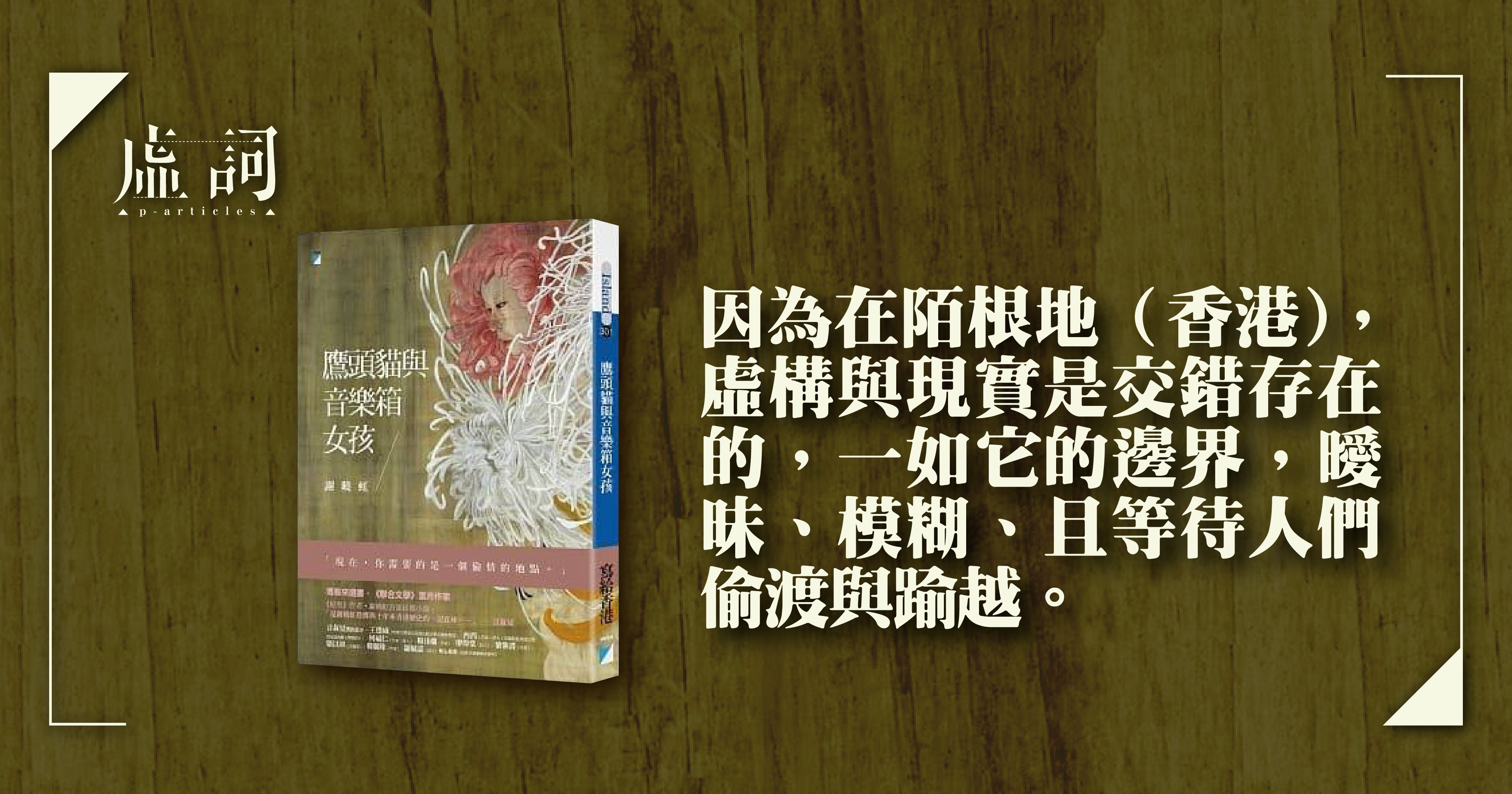把異色愛情投進極權社會——評謝曉虹最新長篇小說《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生活將一個作家拋擲進學院裡,讓她面對繁瑣工作,升等壓力,還有一群桀驁不馴,十八至二十幾歲的荷爾蒙力比多像汗臭一樣濃郁爆發的大學生。其後,身為一個作家還是得寫書的,於是就咬緊牙關跟一切雜事對抗。結果我們終於等來了謝曉虹的新作,《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時隔十多年再出小說,謝曉虹已經不是原本的謝曉虹了,經歷了幾年教授創意寫作課程的蹂躪(我有幸身為她第一屆學生,也就是,她在浸大的原初精神污染之一),我們可以顯而易見地看見課程對她的斲傷。
《鷹頭貓》是一部長篇小說,場景座落於一個異色的香港,在小說裡香港名為陌根地,中國是剎難,英國是維利亞。關於地名的分析,言叔夏在推薦序裡已作出分析,這些稍為錯開而有跡可尋的地理名詞,如若一片薄膜覆蓋在實際的香港上,一種與魔幻寫實相似的錯位技巧,使讀者在真實與虛構的曖昧界線來回遊移。全書故事一如封面推薦語:「一個年過半百的大學教授,卻陷入與人偶炙熱的婚外情。」教授五十多歲還是個處,因其妻保守且不黯世事,他衰老的慾望壓抑良久,終究向著人偶愛麗詩爆發。禁忌與踰越,小說依舊在這組熟悉的母題上打轉,至於如何把這老套把戲昇華呢,《鷹頭貓》的策略就是這樣:將其異色戀情放置於香港抗爭史上作為對照。不過,在本文分析政局之前,我們得先回到敘事技術。
一場表演:敘事腔調的發散與收束
一般來說,討論創意寫作課程的焦點都落在課程設計以及學生能否學會些甚麼,而忽略了這些經年累月的教學時間以及行政作業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是怎樣的精神負擔。《鷹頭貓》的大半部分就告訴了我們,這種影響不容小覷。小說以第三人稱倒敘法開頭,其後平滑地過渡到一段順序記敘,其後忽然跳脫出來使用第一人稱說書人口吻(「我們事實上已知道教授Q的命運了」),故事開始變成一種敘事腔調的連場操偶秀。想得出的都有:第一第三人稱交錯出現、距離忽近忽遠、偶爾故作天真也偶爾陷入深沉反思等等,如果打個比喻,那大概就是一疊創意寫作系學生的合集。
回到一個我們非常關心的命題:我們這些學生在小說裡有沒有一席之地?當然有啦,作出了那麼大的精神傷害,以為可以逃過一劫嗎:「教授Q想起自己平日在其中一扇窗後埋頭埋腦地工作的樣子,便忽然感到氣憤。『我把多少青春,浪費在那個地方!』」、「教授Q一向喜歡一面聽古典音樂,一面批改學生的習作,這樣,他才不至於於一再喃喃自語地嘲笑他們:『文盲!文盲!』」生活將一個作家拋擲進學院裡,把謝曉虹從《好黑》的冷硬內含熱情的南美魔幻寫實技術扭向了使用大量感歎號作為抒情的路線,學院呈現的這種形象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不是嗎?
不過,正如講話時最重要的是一句「但是」,寫小說最核心的要訣也是一個翻轉,一個但是,一個不過,一個掙脫前面一切枷鎖的情節。正當《鷹頭貓》走向一場搖搖欲墜的情色表演即將萬劫不復之時,謝曉虹開始添加一種前文未見的敘事手法:第二人稱。如果說讀《鷹頭貓》尚未看見以第二人稱開篇的部分,儘管在全書非常後面了,也不能說真正進入到故事的核心部分。在這裡,小說終於開始翻轉,把前面的散亂全面收納梳理,將半百教授的異色之戀推向更深一層的反思。
作為一個犯罪者的快樂,全在夢裡
第二人稱開始於小說第29章,如同人偶的提線,把前面二百頁的故事重新操縱。故事大略是這樣的:教授Q於學院打滾多年也無法升等,儘管擁有在外人看來非常美滿的家庭生活,但多年以來從未成功與妻子瑪利亞行房。她如若修女,「談吐優雅、成績優異,眼裡總是有一個秩序嚴明的,萬物已經被分類好的世界。」新婚時教授Q嘗試行房,但在撫摸時她卻一直在笑。沒有甚麼比笑更傷害性的事了,因而過後,在教授Q幾番嘗試不果,他們終究維持著處子之身。後來教授Q就迷上了做夢,也迷上了女體玩偶——也是情色的兩條支線:以睡夢作為慾望的迷逸,以及操縱如死人一般馴服的慾望對象。我們有川端的《睡美人》作為很好的參照。
《鷹頭貓》的最大翻轉,或是說這個長篇小說的「但是」,就是發生於最後的揭曉時刻:在此之前的一切敘事,看起來比較線性的情色時刻與日常時刻,其實有好些也是夢與比喻,我們必須對其抽絲剝繭,分類出哪些是真實發生的,又有哪些只是教授Q的夢。有哪些是實際存在的地方,是教授Q如同夢遊般的旅程裡由於極度的性壓抑,賦予了幻想的性質。第二人稱就是召喚讀者進行反思的翻轉技術。但我們不可以斷言說:這一切都是教授Q的夢。因為在陌根地(香港),虛構與現實是交錯存在的,一如它的邊界,曖昧、模糊、且等待人們偷渡與踰越。
但人偶愛麗詩作為教授Q的慾望對象,卻必然是幻想的產物。她是一個音樂箱女孩,在「一個巨型的箱子,愛麗詩正曲起了一隻腳站在其上,兩手則像一把倒掛的扇子那樣打開來。」教授Q把她買下來,替她穿衣並帶到遠方一個荒蕪小島,在島上的教堂裡狎玩她。在那裡,「教授Q如今重新發現了作為一個犯罪者的快樂。每天,他從家裡,從大學裡逃走,拿著他那把蛇一樣的鑰匙,只一心潛進教堂、音樂箱的秘密世界。」在那裡,在他的逃逸的極樂之夢裡,愛麗詩醒過來了,如活人般向他求歡。
夢作為性慾的載體,是精神分析的基礎命題,教授在教堂裡與愛麗詩進行的異色之戀,也就是他長久壓抑下來的性慾所致。《鷹頭貓》是一部講述壓抑與踰越的故事,這個論點我們已經重複了很多次,不過,在拉康那裡,夢抑或潛意識,也是存在著語言結構的,教授Q的夢再如何異色與反常,他夢中的場域卻始終是一個教堂,一個神聖的大殿之中,他從未逃出秩序的網羅。一切只是如同幻夢,愛麗詩活過又恢復一動不動,而導致教授Q夢醒的恐怖時刻,那個在潛意識裡顯露出的不能承受之物——也就是「真實界」——卻是政治。
結語:提前展露的敘事核心
從始至終,教授Q與妻瑪利亞都對政治保持疏離的態度,學校罷課學生去抗爭了,他不知道,因為忙著玩人偶。政府要進行大規模改革了,瑪利亞不想管,把email刪除當沒看到。抗爭期間他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仔細研究了報紙半天確定「甚麼都沒發生」,於是就很是高興。然而,就在一切如常的情色玩耍當中,政治找上門來,調查員向他指出,他一直在進行玩樂的那個隱蔽小島,只不過是革命份子的躲藏地。而他被告知,只要配合極權的行動,「正是毀滅你做過的夢、毀滅罪證的最好時機。」
極權統治可以摧毀任何夢,即使是最異色最奇幻的夢也無法避免,《鷹頭貓》主要講述的就是這一點。在大部份以教授Q與瑪利亞出發的敘事裡,陰魂不散的「創作系學生腔」之謎如今終於解開——因為從頭到尾都是夫妻兩人自我欺騙的幻夢。兩人遠離政治,維持著童子童女之身,去荒島發夢與玩人偶,都只是蒙蔽雙眼的行動。是以,那麼多故作天真的敘事,那麼多感歎號與「啊!」式抒情,都是假的。其實謝曉虹在小說中途已經提前破題,將小說的核心攤露出來——「時間忽然變得很薄,像無聲的蟬,那用舊了,褪去的褐黃色外殼一樣,脆弱又易於折斷」——只是真的要到達小說最後,使用到第二人稱的召喚技術時,才能知悉這一切脆弱的原因是甚麼。
小說、性慾、壓抑與日常等等,如今在抗爭與極權統治期間重新審視,必然要提出的問題還是那個,也只能是那個:還可以怎樣寫?《鷹頭貓》給出的答案是繁複的,它以一種創作系學生般的敘事腔調,打開了二百頁亂象叢生的「禁忌—踰越」異色描寫後,將政治這龐然大物開進來,輾碎一切幻想空間,讓真實界撬開平滑日常,把敘事強行擰回一種冷硬、疏離、肯定且不滿的語調。這在小說的處理上是鋒銳的做法,但是——我就說過,最重要的還是這個「但是」——由於前面的創作系腔實在磨人,導致極權的暴力闖入且轉換腔調時,我幾乎為其搖旗吶喊,《好黑》的謝曉虹回來了,痛哭流涕。所以在最後,我也是得講句風涼說話,對於初入大學的「文盲」(包括我),還是不要被影響得太深,不然聽多少古典音樂都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