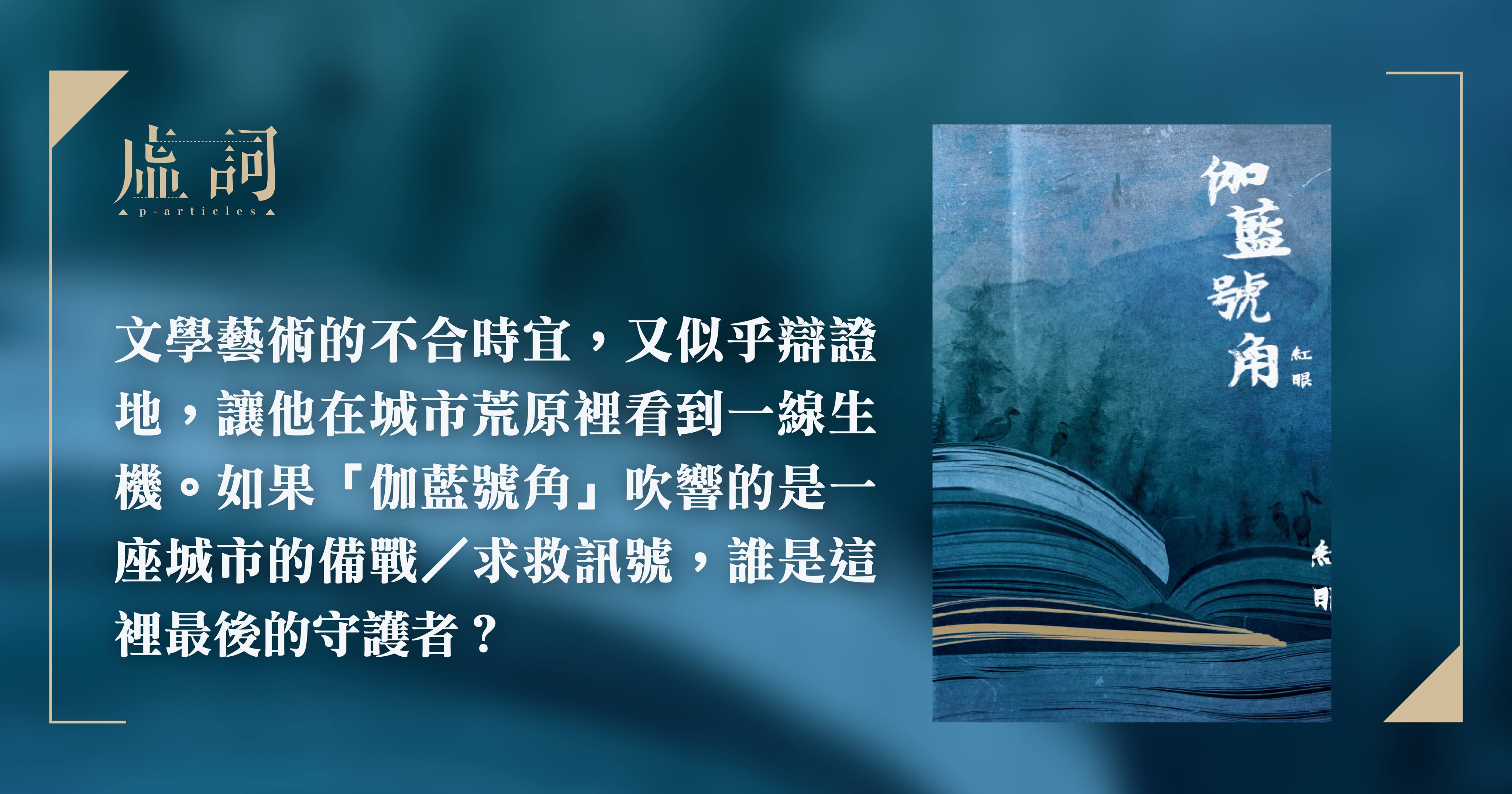【新書】靈光與魅影:後佔領時代的文藝後青年 —— 讀紅眼的《伽藍號角》
後現代情境給予文學藝術的一種解放,是對深度的逃離,讓符號放任在能指層面的冰上滑行,在花式快感之中穿行無阻。從十年前第一本小說集《紙烏鴉》開始,被葉輝稱為「小說新人王」的紅眼,便在這種解放中出場。在一個自我複製、源頭早已失落的擬像世界裡,能指和所指的錯位,反倒孕育了紅眼最初的創作能量。就像小說〈紅眼睛的男人〉裡,那個被目為怪人,在咖啡店反覆出現的紅眼男人,只要謎底還未掀開,便能負載所有想像變奏,只要人物身分未被固定,虛構便可以無限增殖。
在紅眼後來以城市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裡,人物總是反覆借著范曉白、許雅婷、何美芝等等熟悉的名字再生,彷彿際遇總可以交換,毁壞了的都可推倒重來。然而,這些人物交織的故事,卻愈來愈令人感到沉鬱。他們的命運如果不是永劫輪迴,最少也是莊生曉夢。角色與角色交疊成重影,發生過的愛慾和背叛似曾相識,一切竟都是無望的錯認。
紅眼新作《伽藍號角》裡的一個短篇〈造雨人〉,彷彿是這種小說幻術的一個註腳。何美芝總是在下雨天到蘇志健的理髪店,借由髪型的變換,來逃離舊我。而蘇志健不同尋常的剪刀,竟真的能把何美芝,輕易變成了他人眼中的何湘琪,讓她以新的身分到處行騙。小說結尾揭示,蘇志健其實可以是陳天偉,或高海俊,又或何美芝的舊情人,也即讓她想要反覆逃離自我地獄的罪魁禍首。蘇志健視不斷改變自己為年輕的象徵。然而,當他說不想再變換髪型,或者並非因為他已失去青春的創造力,而是因為他能夠洞察,髪型師的魔法,和消費社會的騙術同出一轍。在一個早已被編碼的鏡像世界裡,掌握剪刀的騙子,如何保證自己不被另一雙無形之手愚弄?
《伽藍號角》比紅眼過去的作品更為深沉而婉轉,也流露出對書寫更曲折的思考。從個人的衣著打扮、雜誌編輯風格到各種評論隨筆,我們看到的紅眼,一直是個善於跨越各種媒體,操作流行符號的寫手。他以變化的身影來拒絕被「文藝」定型,以《藝文青》來實踐文學與時尚的結合。然而,流行文化與文學在他心目中卻始終有著無法跨越的分野:文學雜誌上的明星照片只是「招式」,文學卻是關於長久的「教養」;高調推銷文學雜誌的紅眼,在面書上的低語,是趨於隱匿的書寫姿態:
但其實我一直都在寫小說,愈來愈慢,愈來愈少〔……〕我想用一個更慢、更少的形式,讓它繼續微小。
作為一個「跨界」的作者,紅眼對消費社會裡,文學藝術的「(無)價值」,定有深刻的體會;而在一個社會高速崩壞,全民抗爭的時代,文學也似乎愈見「無用」:
小說,更好像變成一件不夠力、不討好的事情,轉彎抹角、風花雪月,既無法迅速回應社會現實,而又難以排遣迷惘時刻的鬱悶。
然而,文學藝術的不合時宜,它無法被資本主義社會所消費的「(無)價值」,又似乎辯證地,讓他在城市荒原裡看到一線生機。
如果「伽藍號角」吹響的是一座城市的備戰/求救訊號,誰是這裡最後的守護者?紅眼這本最新的小說集,從不同面向切入近年的社會運動,其中最動人的描寫,幾乎總是和文藝青年的理想形象重疊起來。在〈最好的選擇〉裡,當佔領運動潰散,人們努力重過「正常」的生活,當日留守在柏油路上,日裡寫歌,夜裡彈結他的男孩子,卻如魅影在城市角落再現 ──「他居然什麼都沒改變過,還是抱著當時的那一支結他,穿著相同的衣服和運動鞋。」
即使文藝終於過渡了青年,這些人懷著近乎天真的執著,卻甚至可以超越消費社會對時間的無情定義。〈擊壤路之春〉以疫症和反送中為背景,苟存的小市民莫不鋌而走險,混水摸魚,一時間兵賊難分。其中長髮男子「長毛」是裝修師父、配音員、婚禮司儀,小說卻強調他的「正職」是搞獨立劇團。看見派文宣的中學生被毆打,只有他仗義出頭。擊壤路上最動人的春情,大概不是彪哥在休旅車上,一再受到干擾,沒有得到 happy ending 的按摩服務,而是打劫四人組搶過便利店後,救走了學生和長毛,在車廂裡播起昆頓塔倫天奴的電影插曲。讀者這才知道,他們原來也是不得志的文藝後青年,打劫得來的錢只夠在暫居的網吧續租一個月,但在車廂劫後餘生的時空裡,他們卻又談起了電影和音樂。
在文藝(後)青年與社運新世代裡,紅眼似乎同樣看到一股不計成敗、不屈從現實邏輯的抵抗力量。在〈移民〉這篇小說裡,父親陳天偉和兒子陳啟榮都曾潛進商場的秘密通道,「移民」到一個些微錯位的平行世界。只是,陳天偉所追求的是一種中產階級的穩定生活,陳啟榮卻帶同他的同學,在逃離警察的追捕後,自願重新回到衝突發生的原初場景。在這個平行世界裡,發生過的社會運動將重複發生。陳啟榮無力改寫故事的結局,卻能憑借自覺的意識,改寫經驗的意義。
紅眼筆下的世界並不天真 ── 即使只是探索微小的逃逸路徑,就足以遭受最巨大的報復。《伽藍號角》鬼影處處,充滿了人、動物和地方,以及他們互相連結的死亡。最讓人震撼的篇章,莫過於〈海明威的貓〉,一個由偷情開始的故事,竟發展成無法收拾的暴力。
原初的失落,仍然是這篇小說的重要母題。沿巧遇舊情人,背妻偷情的「我」,讀者知道男主角迷戀的情慾原型,本是他妻子許雅婷的長腿。失而復得的初戀情人,為何無法讓「我」的婚姻美滿?
「我」從中學開始,便想要揭開許雅婷這個不脫襪的女子,腳掌上的秘密。和許雅婷做愛沒有讓「我」得知真相,兩人分手的導火線,似乎是「我」向同學脫口而出,關於她有六隻腳趾的謊言。然而,謊言其實並不是意外,許雅婷也不是慾望的原初。這些少年的慾望形式,早就被消費文化形構。她的腿被同學解讀成「神秘」的符號,而她不過是 AV 女郎的重影。AV 裡所營造的「神秘」,是通過慾望的延遲,來增加快感,而許雅婷以白襪隱藏起來的雙腳,卻始終不是可慾的對象。即使結了婚,「我」其實也註定了無法看見妻子襪子底下的真相。許雅婷拒絕扮演主流社會所期許的角色,不屑要穿高跟鞋的高薪厚職;她迷醉於逛書店和美術館,奔走於保育與社會運動,她的追求,本就溢出於「我」可理解的範圍。
許雅婷從未被「我」,或曰消費社會的慾望邏輯所真正佔有,愛情故事的下半部遂變成了殘忍的鬥爭。許雅婷自斷雙腳,作為對「我」的反擊;「我」為求在妻子誕生的嬰兒身上,窺見基因的秘密,則不惜找來陌生男子輪姦她。許雅婷最終在各種折磨中死去,但她的意志卻延伸至女兒扭曲的、無法數算腳趾的畸形身體,作為對這個「正常」世界所作的最後抵抗。
許雅婷那雙被潔淨白襪包裹的腳掌,正如柏油路上孤獨地彈結他的少年,本是擬像監獄裡僅餘的一點靈光,遙指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然而,在靈光失效的時代,無可消費的「神秘」沒有被膜拜,而是變成了令人恐懼的,未為資本主義所統治的魅影,一再於城市的暗處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