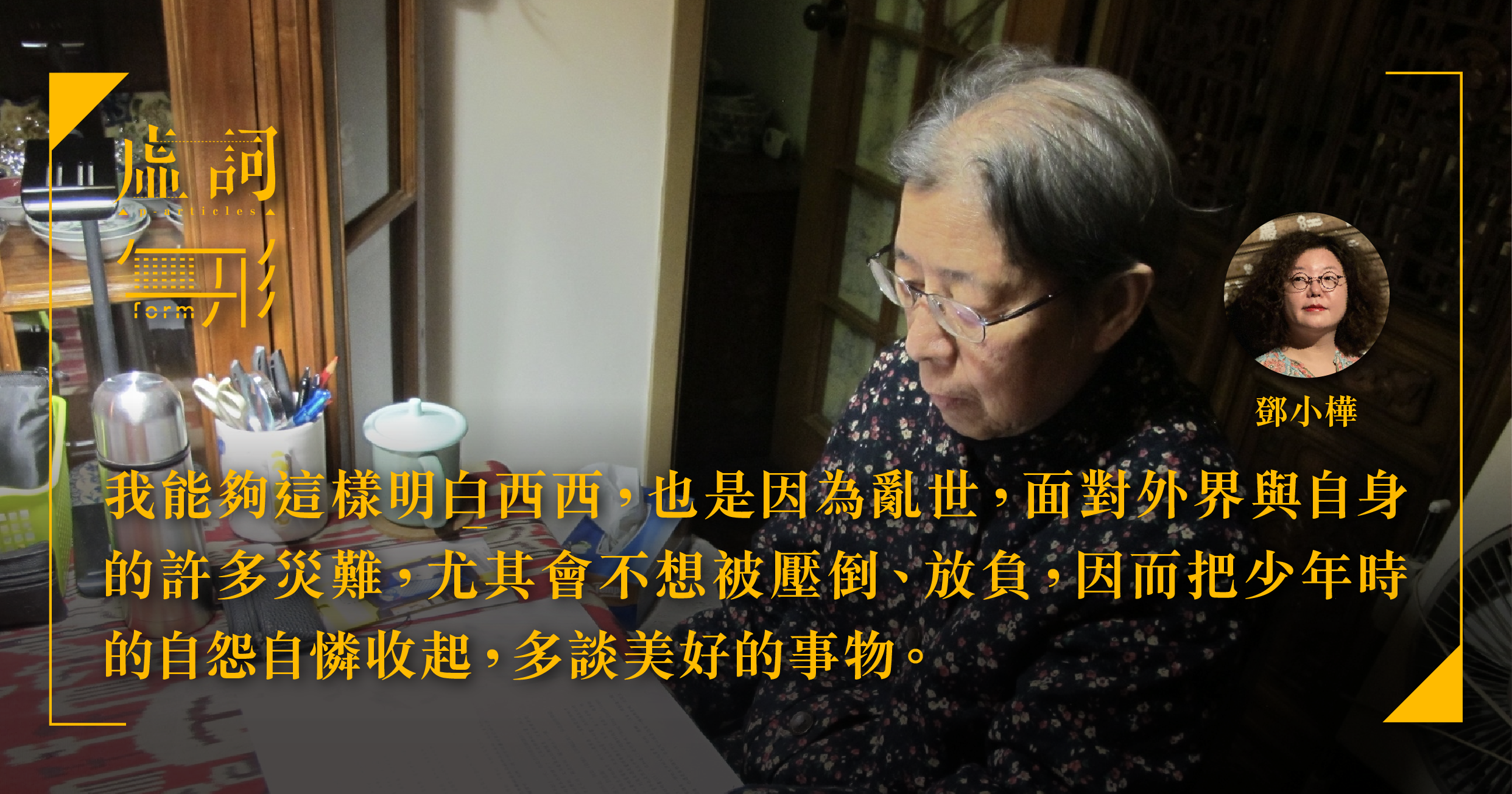【無形.像西西這樣的一個女子】怎麼可以這樣快樂
對於西西的作品閱讀,有些部分是需要時間的展開才能深入理解——不是指花在閱讀時間上的,而是指需要讀者自己生命的進程走到某處,才能真正理解到其中的價值。換一個說法是,事非經過不知難。而西西那麼隨和親切貼近我們,讓我們有時忘了她其實是在引領我們超升。
我沒有送過西西玩具,我已經缺乏玩樂好多年了,不好意思說自己是以看《我的玩具》來代替玩樂——如果這全然只是一篇西西《我的玩具》的書評,我會大講西西有多麼好玩,那些玩具顯得她多麼富於童真、多麼博學而又秉持萬物平等的眼光,正如此書的所有評論者一樣。但這是一篇悼文,某些西西文中本來隱晦的地方會此而特別顯現。《我的玩具》固然是妙趣橫生天真可愛的一本書。但它有些輕描淡寫的地方一直讓我怵然而驚——那便是年老與病患、身體的障礙——這些在書中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幾處淡然提起。首次是〈散步〉,寫自己在公園晨運練雲手覺得天旋地轉,暈倒在石櫈上,不知過了多久醒來,人來人往沒人理她,她自行勉力回家,此後不敢去晨運;再後來右手失去知覺再也抬不起來。讀到這處霍然而驚,這樣的「街外經驗」,對一個老人家而言多麼驚險,頗可喚起許多慘情與憐憫;但西西筆鋒一轉,又樂滋滋去寫她的玩具。
讀西西,看她寫出來的知識與門道已經豐富到消化不來,但還要看到她沒有寫出來的。散文一般被認為與作者真實個人非常接近的文類,但西西在她的散文裡常常是相當隱身的,隱於她所陳述的現實細節與知識背後,負面情緒很少,永遠是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孩童,只是非常偶然地流露出一點半點的驚心動魄。〈阿福〉中寫她有一年夏天去日本旅行閒逛電器店:
「我一時頑皮,伸手去試血壓機。一次,沒有數目字出現,再試,仍是空白。連試幾部,都失敗了。售貨員幫我量,然後臉色一沉,說,See a doctor。以為我不明白,再說一遍,See a doctor。我馬上乖乖回到飯店,對大堂坐在旁邊獨立桌椅的經理說要看醫生。原來這位經理會說普通話,懂中文,姓有馬。他立刻陪我到幾幢酒店外的公立醫院就診,並且做起翻譯。量血壓時又爆燈了。我帶了藥回酒店,翌日連忙購買機票提早回港。幾年後,我再到日本看毛熊展,仍選新宿那酒店。」
引述原文,是想展示這個驚心動魄的血壓暴走情節中,唯一涉及內心的形容是「頑皮」、「乖乖」,最多加上「連忙」,當是一個小孩頑皮闖禍受教訓般的事來寫,彷彿一切還是自己的責任。每當遇險,西西總是這樣帶過去,沒有怨天尤人,半分不自憐,別說沒有誇飾簡直是摒絕內心化,背後是順受天命之意——看來沒有經營,實則是節制到成為自然流露。
西西深諳言簡意骸,又常以孩童口氣說出普世真理,詩文中具宗教高度的啟示性筆法更是常見;但寫及自己現實中「遇險」時,則極度節制,留在現實的層面中,節制了象徵和推衍。像〈陀螺〉中寫自己在桌上玩陀螺,「多年來我已成為左撇子,左手沒有什麼能量,陀螺總是轉幾圈,意思意思,然後倒下,然後靜止。桌上陀螺,只能這樣了。」這明明是右手殘疾的後遺所致;倒下、靜止,當可指涉死亡;陀螺更可以象徵不由自主的生命。但西西把一切隱喻象徵之流截斷,回到最平實最基本的,「桌上陀螺,只能這樣」。
這在文學手法大概沒什麼好分析的,但當一個人面對衰老病殘,又有多少人能如此豁達?老去原是一個剝奪的過程,將你的形貌、身體、行動自由、能力一一拿走,一切是絕對的無可奈何。近年右手也不大舉得起來,久治不癒,遂有明白。當面對這一切受限,你還是否能忍得住,不把自己比喻為一枚不由自主旋轉且傷痕滿身的陀螺?很多人都知道,西西是反浪漫主義的,她不感傷,連自己的遭遇她都不感傷。是我覺得自己做不到西西這樣,才知道這有多麼難。
《史記.留侯論》中論勇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經過2019,我大概可以接近「卒然臨之而不驚」,但「無故加之而不怒」還是經常做不到。但想想,「卒然臨之」、「無故加之」,不也就是命運的挑戰與災難來臨時的狀態嗎?西西的豁達其實是面對命運的大勇,置生死於度外。但因不想親友擔心,活著又有好玩的事,於是又好好活下去。
《我的玩具》中唯一一次比較強烈的負面情緒是〈熊出沒〉中西西發現熊玩偶打理不善而吽出蟲來,「都怪自己愚蠢,明知香港氣候潮濕,又無能力維持一天廿四小時空調侍候,縫什麼熊呀。」西西把萬物當生物,又把自己置於萬物之下。又有一篇寫她坐著的溫莎椅散架,讓她整個人跌到地上:「我居然亳髮無損。於是也原諒了椅子,應該是,彼此彼此,因為之前對它的形容失敬。」這裡的擬人,是將物與自我齊平對待,寛容平等,當是自己得罪了椅子。「擬人」這種修辭手法,原來還可以幫人消化自己遭遇的意外和危險。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因是已。[⋯⋯]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莊子.齊物論》
關於身體衰病之事,《花木欄》後記有流露病弱時的低沉,集中全面開展的有《哀悼乳房》,收在《白髮阿娥的故事》中的〈解體〉更以前衛文體極寫身體內部的爭戰與崩壞;其後,西西倒只寫外在的、趣味的、善良的那些玩藝。我從小「老積」,偏好結構性強或沉重高遠的文字,喜歡看死亡和疾病的書寫,連童真都要進行分析,自然也有覺得西西作品太過輕快的時候。西西過世後我和洛楓小姐做過一個LIVE,她提到一直有人嫌西西作品太輕,到西西過世了之後還在嫌。的確我有見過,我以前也一度有微言。是到自己老了限制多,才知道西西如何舉重若輕——她一直堅持著卡爾維諾的信條,繼續往「輕」的高處提煉,同時舉起了更多更多個人命運的重負。如果你覺得那輕是不合情理,其實要想到她舉起的那重也是極致。
特別要提醒的是,西西的「輕」並非浮淺,相反是承載愈來愈多的知識內容。大概也有人要抱怨西西是太正面、正能量了。我是在與洛楓做LIVE時,突然明白這種正面傾向是一種知識份子及教育工作者的取向。西西博學讀書多是眾所周知,但知識份子不止是多讀了書而已。吳念真常提起他童年時村口代寫信的「條春伯」,覺得條春伯才是知識份子的代表。村子裡的大老粗請條春伯代寫信叫在外的大兒寄錢回家,本來是滿口粗言的訓罵,條春伯則將之改寫溫暖婉轉關懷有禮之語,並向大老粗複述一次,問「是不是這樣?」大老粗喜笑道:「是是是!就是這個意思啦!」知識份子的責任,是要把人間的粗暴情緒與紛亂輾壓,轉換成能夠普遍明白與接受的言語,勾現底層的善良,讓世間往好的方向發展。愈是面對叢林般粗礪兇險的現實,愈要這樣。至於教育者,則是面對比你更弱勢更年輕的人,負起教育者的責任去為他們服務,那自身的EGO也自然縮小,好把自己放低一點。
我記得《字花》第一期,有西西的一篇短文〈熊藝〉(不知算是散文還是小說),前段寫西西初學做熊的手藝細節,大概如日後多篇文章所見;特殊的是文末寫一個與西西一起學做熊的女孩,一邊用木棒塞棉花入毛熊肚子一邊喃喃道「死了吧,死了吧」。文章就在這裡結束,不吝可以發展成一部驚悚小說,又或用來抒發「世風日下現在的小孩好可怕」之類的老式言論;但西西沒有這樣做,這個短篇沒有收在任何集子中;當時間和體力都有限,西西選擇去做《縫熊誌》,那麼多個精緻到超越想像的毛熊,細節承載著大量的歷史考察知識與創意。舉重若輕,是想把力氣花在美好的地方,把美好給予更多的人,讓世界再好一點。
我能夠這樣明白西西,也是因為亂世,面對外界與自身的許多災難,尤其會不想被壓倒、放負,因而把少年時的自怨自憐收起,多談美好的事物。吳靄儀說過,希望是一種責任。如果是太平盛世,西西的遊藝手作、晚年小說可能只是一些美好的消閒,儲藏給人間日後細味;但當世界日日出現壞事、連自己身體都是災難現場,我於焉明白了西西的美好之難、及難得。那不是壓抑,不是隱埋,不是為了呃LIKE而只呈現美好一面,而是真正消化命運的巨大挑戰,以自己快樂的方式超越其上,同時俯身親近萬物﹐所謂舉重若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