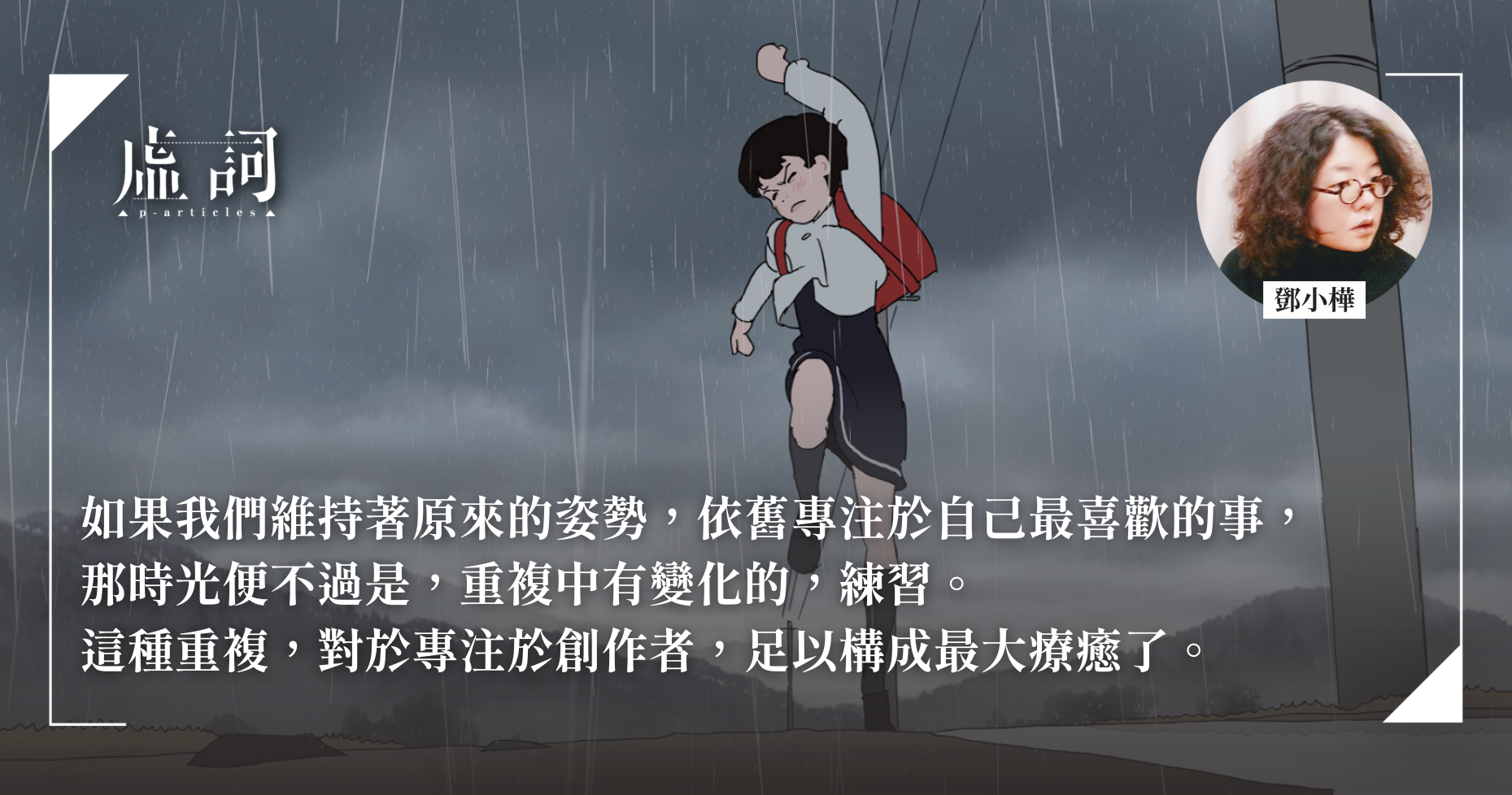還有什麼能療癒你
《LOOK BACK》是好看,但覺得短了點——看完電影之後我馬上與友人衝向電影院樓上的書店,去看《聯合文學》雜誌的驀然回首專題,想知道電影/漫畫原作的故事是否來自作者藤本樹的親身經歷。因為故事描述的兩位漫畫少女好友兼拍檔的友情如此動人,可能很多人都會以為那是藤本自己的真實故事。然而,藤本在訪問中談起的卻是2019年的「京都動畫縱火案」,那造成了36 名動畫工作者身亡及32人受傷,對京都動畫造成重創,甚至造成業界非常嚴重的中堅人才斷層。直至事件發生一年後,京都動畫重新招聘員工,並恢復製作。事件兩週年之日,《LOOK BACK》漫畫發行。《LOOK BACK》,原來是對於同業者的一次安慰。這也解釋了為何作者要強烈地指涉Oasis的歌曲〈Don't Look Back In Anger〉,那Anger,不是私人的Anger,而是巨大公共創傷的Anger。
這個發現反而讓我覺得藤本樹是個比我想像中更厲害的作者,並對電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讀。電影中的無差別殺人與縱火案,同樣是讓漫畫工作者失去夥伴的傷痛;藤本通過將公共事件中的傷痛,寄託於一個非常個人的故事:「如果我沒有讓她離開房間,那她是否就不會死?」「失去了夥伴,我還可以怎樣繼續走下去?」「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保護她……」此皆傷痕的核心。而電影敘事借助平行時空結構,並非旨在改寫憾事,而是讓藤井看到自己作品對於京本的意義,從而明白,自己繼續畫漫畫就是京本最大的願望,也是她們之間最重要的連繫。這一層故事內部,回到初心的療癒,應該很多人都已體會。
但你知道,《LOOK BACK》對我而言最大的療癒是什麼嗎?那在電影很早期便出現,當藤野坐在窗前伏案狂畫,京本便在她身後的榻榻米上安靜奮筆,然後是,一次次的季節變換:二人身上的衣服變化,但姿勢依然不變。然後是描繪窗前景色的圖畫,同樣的景物,不同的季節顏色,一張一張疊加上去——因為是繪畫,它讓標示時光過去的功能,與繪畫作品作為電影中的「物」兩者重疊,這些像日子紀錄一樣的畫彷彿同時是藤野與京本的作品,她二人在時光中就是作著這樣重複的練習,那就是最美好之物。
是這樣嗎:如果我們維持著原來的姿勢,依舊專注於自己最喜歡的事,那時光便不過是,重複中有變化的,練習。
這種重複,對於專注於創作者,足以構成最大療癒了。
《古詩十九首》裡說:「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兩句便概括了無數蒼老、衰頹與虛無。然而,作為現代人,又何嘗不知變幻原是永恒,城巿本就變化多端,街道整修不斷,店子開了又倒,搬家轉工移民——何況當下是一切分崩離析大翻轉的時代。
正因如此,用自己的方式,營造一個世界,掌握一種重複中變化的練習,去克服時間及一切鴻溝,反而變成一種極有說服力的行動方式。這是第二層次,故事與故事外部連結而述說的安慰。藤本樹說,「唯有創作,能讓我們與死亡和解。」
還有類似之物安慰我:藤本樹與約翰伯格作類似之事。伯格在過世前一年出版的《閒談》(Confabulation)中寫到左翼理論家羅莎.盧森堡,他喚她一如青梅竹馬好友:「妳經常從我正在閱讀的頁面走出來,有時還會從我試著書寫的頁面走出來;甩頭微笑地走出來,加入我。沒有任何一個頁面和任何一間他們反覆關押妳的牢房,能夠束縛妳。」
羅莎.盧森堡受囚禁、1919年被虐打致死,而伯格以極其親愛的語調,把她的書信與論述,與他當下的生活、友人、往波蘭旅行所見作平行剪貼,那種自由筆觸之親密無間,超越生死。他引用羅莎鋒利的論述也引用她明亮的指引:
//「當個人,」妳說:「是最重要的。 意思是,要活得堅定、澄澈且開心,沒錯,開心,同時,欣喜於每一天的明亮與每朵雲的美麗。」//
他還向羅莎說明他所見的波蘭人,「發明許多夾縫求生的計謀與策略。」左翼理論家當然相信策略,並有一種左翼的昂揚,至死不滅。各種引用與生活叙述無疑是重回回憶,但同時也讓伯格和羅莎,都繼續變化。如此自由的筆觸之下,作為主體的伯格和他所描寫的羅莎一樣隨心所欲,儘管那時他已經接近死亡,但自由的書寫讓他和羅莎都有了清澈的尊嚴。
即使我們觸目皆已破碎,自身的能力範圍一再削減幾至於無,但萬物的過去未來,都可以在我們珍愛的目光中,呢喃的叙述中,重生。非常非常愛的時候,我們都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