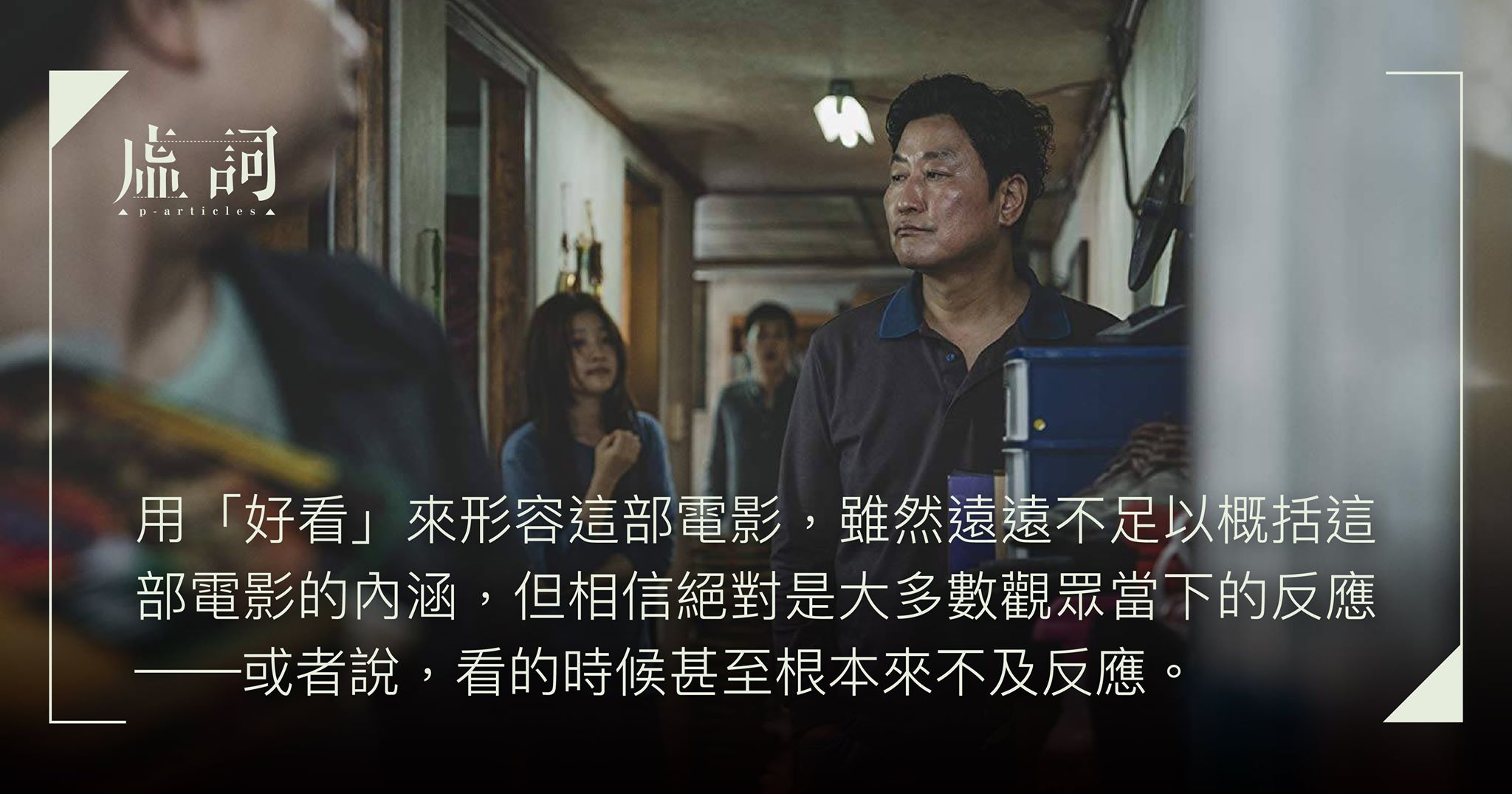同時奪得康城影展金棕櫚獎以及奧斯卡最佳影片的《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將商業電影的可能性推到巔峰,凌志誠在這篇影評以劇本、剪接、鏡頭運用等角度,分析這位奧斯卡最佳導演對影片的掌控如何一絲不苟,成就電影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閱讀更多)
【時代抗疫】防疫與我們的共同體
然而傅柯、阿甘本或埃斯波西托等哲人之所以討論生命政治,並不是要告訴我們生命不過受主權操控的事實,而是要讓我們去想像一種新的可能,傅柯認為古典哲學不乏教導個人重新管轄身體的篇幅,阿甘本從方濟各會苦修士生活思考一種全新的、不受社會或政權操控的生命形式,埃斯波西托則提出一種肯定性的免疫機制。 (閱讀更多)
Todd Haynes 電影中的恐懼感——《追擊黑水真相》
影評 | by 區皓棕 | 2020-02-05
疫情還未受控,前往戲院未必是個好選擇,但若心癢想入場看電影的話,影評人區皓棕推介《追擊黑水真相》,「合家啱睇」之餘,更是「黃藍皆宜」。主角花了整整十七年,才看到丁點成果,同樣地,在我城生存,我們一定要捱過去,才看到曙光。 (閱讀更多)
字裡行間,窺探粵劇「鬼才」唐滌生的內心世界
書評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02-03
數粵劇界的傳奇人物,唐滌生定必佔據當中一席,在他筆下的粵劇作品數以百計,為後世留下不少經典名劇之餘,亦教粵劇迷欲窺探這位「鬼才」的內心世界。《虛詞》編輯部特意挑選五本與唐滌生相關的好書,藉著對唐氏劇作的專門研究、歷年來與粵劇相關的唐氏語錄、深入剖析經典劇目的文學造詣、鑑賞對其別具意義的物件及珍貴照片,將這位在中國文學,戲曲及粵劇界屬異數的百年難得奇才,更立體地在字海裡呈現。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