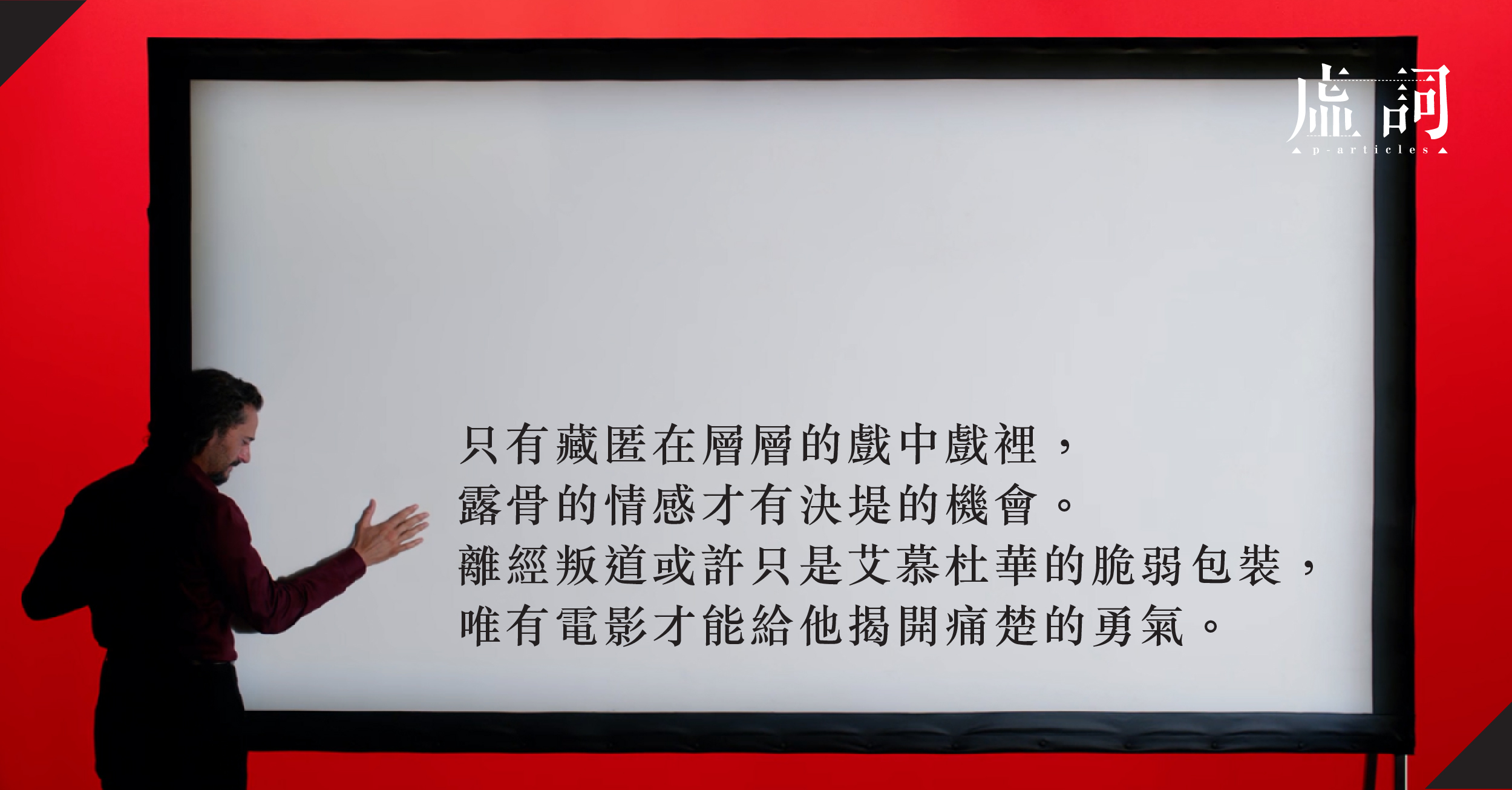《萬千痛愛在一身》:電影無法拯救世界,卻能安撫人生
「我對電影的概念總是聯結著夏夜的微風,只有夏天我們才看電影……我童年的影院,聞到的永遠是尿騷味、茉莉花香,以及夏日微風的氣息。」艾慕杜華對電影的原初記憶,充滿了普魯斯特般的執著與浪漫:「即使物毀人亡,氣息和味道卻在,它們更柔軟,卻更有生氣……讓人想念,等候,盼望。」如果在《天堂電影院》裡的電影是童年與家鄉,那麼在《萬千痛愛在一身》中,電影更是救贖,將一切不能言說的藏於其中,再化為光影,在大銀幕釋放。
電影甫開始,便看到頭髮花白的導演薩爾瓦多(安東尼奧·班達拉斯飾)半蹲冰冷無聲的池底,回憶乍現,水中無形的凳變成母親堅實的背,年輕的薩爾瓦多騎在辛勞地洗衣服的母親背上,母親未曾責怪,反跟兒子說:「看!是肥皂魚!」陽光下,一群母親唱起歌來,這段回憶純樸如小薩爾瓦多的笑:電影始於情,那些不能言說的痛亦始於情。

可惜美麗的幻象如肥皂一觸即破,回歸現實,只見一個百病纏身的薩爾瓦多,現在的他無法再拍電影,是一個失語的獨居老人。電影之於薩爾瓦多,是一本讓他進入世界的百科全書,也是他言說痛苦的藥箱,可是「不拍電影,人生沒有意義」。失去了電影這劑止痛藥,一個導演還能做甚麼?
對電影的癮,以毒品緩解
答案竟是吸毒。回看三十二年前的舊作《滋味》,薩爾瓦多發現當年鬧翻的演員Alberto(阿希爾‧艾特先迪亞飾)其實演得不錯,他前去尋找Alberto,卻因而接觸海洛英。《滋味》這套電影,其實承載了與其舊情人Federico的回憶。電影是人生的記錄,讓情感永遠封存。因為一次重看,薩爾瓦多回想起當年,他閱讀和記下與Federico有關的句子,甚至主動尋找Alberto。與其說是跟Alberto和解,倒不如說是跟這段過去和解,於是主動向Alberto索取海洛英,臥身嘗毒,只為代入當年戀人的心境。這招以毒攻毒,激進而合情理,六十多歲的薩爾瓦多直視內心情慾,忽爾回春,一生也未曾如此敞開心扉。舊情的痛,全寫進了戲中戲《上癮》:
「愛或許能移山倒海,卻不足以拯救一個你愛的人。」
「拯救我的是電影。」
唯有電影才能帶來真正的拯救,強如海洛英和愛都不是解藥。吸毒只是創作的助燃劑,還是要拍出來、說出來,於是薩爾瓦多寫了《上癮》,先以文字把傷痛封存,再通過Alberto的演繹公諸於世,但他卻要隱藏自己是編劇的身分,還要求演員演繹自己時要壓抑情感。張狂如艾慕杜華,卻常以迂迴曲折的方式剖白情感,在《女為悦己者狂》和《情婦的情夫》裡,女主角也是藉著配音告白。只有藏匿在層層的戲中戲裡,露骨的情感才有決堤的機會。離經叛道或許只是艾慕杜華的脆弱包裝,唯有電影才能給他揭開痛楚的勇氣。

痛苦與榮耀,偶然和救贖
電影創造的是機會。只要拍出來,就有被觀看的可能。Federico看了《上癮》,深夜訪尋薩爾瓦多,致電他時,已在他家門下守候多時。薩爾瓦多初時不知,在窗邊看到Federico後才改稱:「我看還是睡不著了,不如你二十分鐘後來找我?」兩個不敢踏前的男人,多年不見默契依舊,既小心翼翼又彬彬有禮,但心底情感卻已大聲叫囂。Federico真誠地向薩爾瓦多道歉,薩爾瓦多反說:「你並沒有阻礙任何東西」,「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人或事像你一樣充實了我的人生。」電影終於點題,何謂Pain and Glory?電影的靈感源自痛苦,可是電影又讓痛苦得到釋放,痛愛難分,彷若艾慕杜華的電影,笑中有淚,悲中帶喜。薩爾瓦多的作品不只拯救自己,也拯救了看這套舞台劇的舊情人,最後二人激情擁吻,卻無下文,從前未說的話現已說出,這樣的和解已是他們最好的結局。
毒癮只是心癮,解開了第一重心結,薩爾瓦多決心戒毒,亦終肯面對心底最大的痛。他跟醫生坦承:「兩年前我的背部動了手術,四年前我的母親去世,這兩樣東西至今還未痊癒。」
最愛的母親,最初的慾望
艾慕杜華或是全天下最了解女人、最歌頌女人的男人。在《女為悅己者狂》裡,失戀的女人明明歇斯底里、麻煩難纏,在他的鏡頭下卻充滿活力,愛恨分明,女人做事女人當,女人挑起的紛爭,由女人解決。在《論盡我阿媽》裡,所有角色竟全是女人,甚至連「父親」也不是男人,一群女人哭哭啼啼,卻支撐了整部電影。這是艾慕杜華眼中的女人:感性但堅強,矛盾是她們的魅力。在《萬千痛愛在一身》裡,薩爾瓦多的母親一如艾慕杜華筆下的所有女性,偉大而勇敢,面對死亡毫不畏懼,還千叮萬囑薩爾瓦多脫去她的鞋子,因為她想「輕盈地走去那個地方」。
而這個回憶的盒子,不再是由薩爾瓦多獨自打開。電影前半部,薩爾瓦多都是孤獨一人回憶童年的時光,此刻他終肯在他人(女助手)面前,以說話追憶母親臨終前的時光。
最令他無法釋懷的是作為兒子的不稱職:「對不起,單單是做我自己,就令你不滿意。」這段自白讓人疑惑,難道從來看破世俗禁忌的艾慕杜華,在母親面前竟然介意自己是同性戀者?命運一再輾轉反側,充滿戲劇性。薩爾瓦多意外看到兒時水泥匠的一幅畫,剎那間童年回憶湧現,更揭開了他最初的情慾。畫作依然是艾慕杜華最愛的紅色,卻不是鮮艷刺眼的紅,而是濕潤的水彩紅。這是慾望萌芽的顏色:溫暖、怡人、含苞待放。此刻他便明白,其實母親早知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慾望並不羞恥,到頭來有甚麼事不能和解呢?人生的種種遺憾與無法面對的事,不都已經說出來了嗎?

戲假情真,有人就有電影
電影尾聲,薩爾瓦多迫不及待在手術床上跟醫生分享:「我開始寫劇本了。」醫生問他是喜劇還是悲劇,他回答尚未知道便昏睡過去。迷迷糊糊中兒時回憶浮現,但鏡頭拉開才揭露,這也是一場戲中戲。艾慕杜華不斷挪移真實與虛構的界線,就如那舞台劇《上癮》,Alberto獨站舞板,演得架輕就熟,如親述個人的經歷,但作為觀眾的我們都知道,這是薩爾瓦多的故事。當Alberto的影子投射到舞台的白幕上,猶如當頭棒喝,提醒我們當下觀賞經驗的虛幻,眼前影院屏幕上的Alberto也不過是一連串人造的投影,戲中有戲,話中有話,是真有其事還是虛構想像,都難以一一證明,但我們仍然投入,並為之動容,相信薩爾瓦多不過是艾慕杜華的代言者,故事或許虛構,但艾慕杜華的真誠說服了我們,戲假而情真。
常說艾慕杜華初期離經叛道,後期逐變深邃感性,其實不然。早在《情迷高跟鞋》,艾慕杜華便已溫柔感性。我們或許被胡鬧的母女鬥戲劇情吸引,可是結局處看似對母親恨之入骨的女兒卻說,小時候要聽到母親的高跟鞋聲才能安然入睡。這段最後的和解,正是艾慕杜華送給觀眾的禮物。薩爾瓦多常祈求戲中的女主角能得到幸福,但從未如願,艾慕杜華的電影,卻從未令觀眾失望。走至古稀之年,艾慕杜華再次送給觀眾盼望,結局未知,因為人生仍要繼續,只要能拍下去,就有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