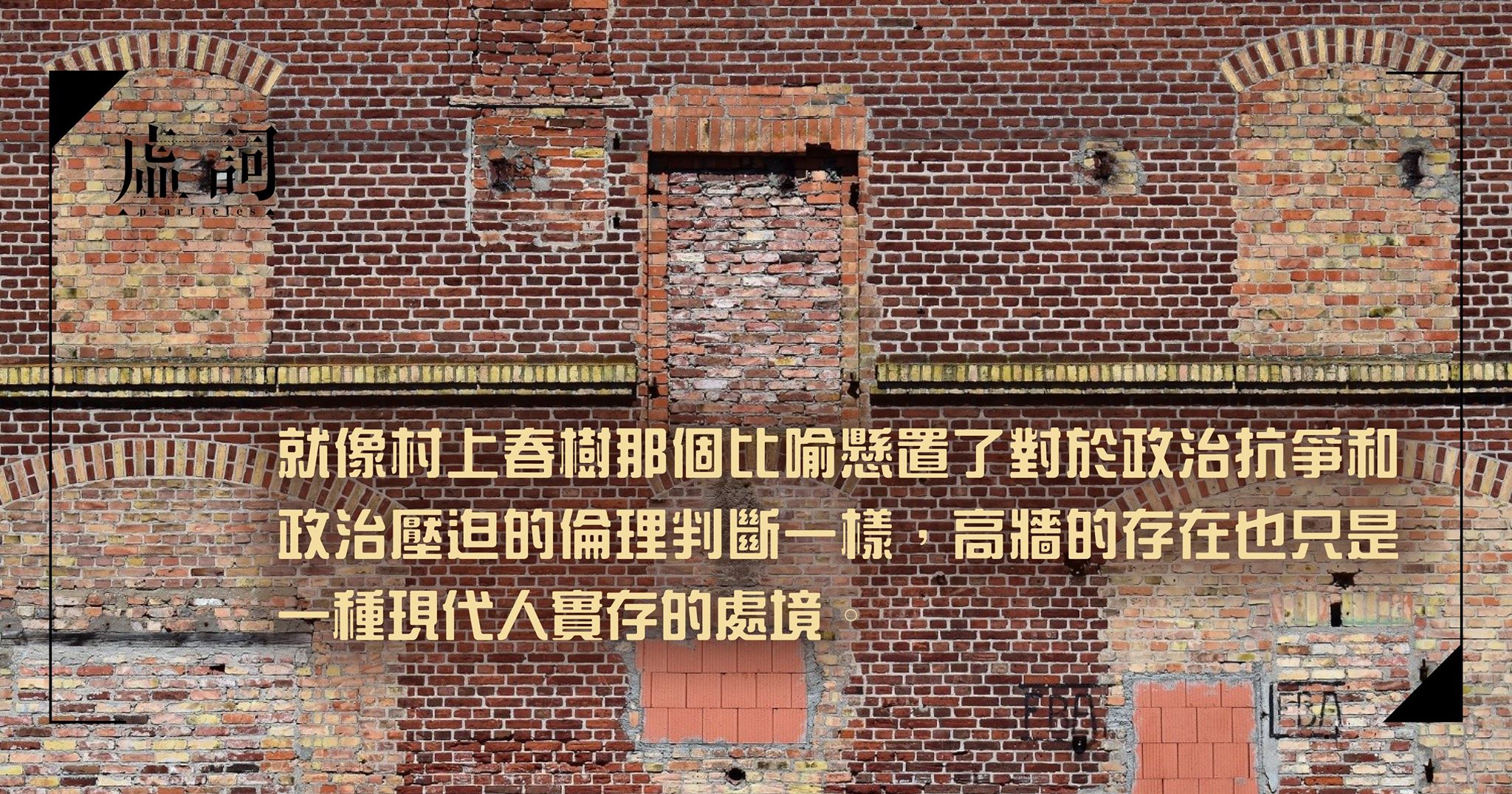高牆
2009年,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奬,出於大家意料之外,村上春樹去了耶路撒冷領奬;也出於意料之外,他發表了一篇關於雞蛋與高牆的演說,並聲稱「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接下來的,都變成歷史,以及老生常談、陳腔濫調了。
但亦因此,「高牆」從日常生活中無睹之佈景,進入了政治抗爭者的語言,然後,由具備政治抗爭的特殊意涵,變成一般人都明白的隱喻。但隱喻歸隱喻,高牆還是實實在在的矗立著。就像村上春樹那個比喻懸置了對於政治抗爭和政治壓迫的倫理判斷一樣,高牆的存在也只是一種現代人實存的處境。
牆本來是為了每個家庭保護生命財產、防禦盜賊而建立的,牆的存在體現出核心家庭作為戶籍獨立存在的狀態。但每個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說明了,他們必須築起一堵堅壁高牆,否則敵人就會入侵其領土、屠戮其人民,掠奪其資源,什至取代他們的政權,滅絕他們的民族。秦始皇修建萬里長城以抵禦匈奴人入侵,這不是歷史上的特例,因為稍晚的時候,羅馬的哈德良皇帝,也在不列顛北部修築長城,以抵禦皮克特人的入侵。這些都是歷史上著名的高牆。
但國家的意志從來都是向外擴張的:如果秦始皇或哈德良的軍隊有能力征服匈奴人和皮克特人並統治他們的話,他們又何必耗盡人力物力修築長城呢?或者他們的皇帝以其實力和威德馴化並管治侵略者,例如萬里長城在滿清統治者眼中已沒有實質用途,只是一件歷史遺跡,而在今日英國接近蘇格蘭的北部荒地上,哈德良長城什至只是一堵橫亘在山上、由石頭堆成的殘壁,間中有旅人前來參觀。
然而在全球化的年代,高牆不單沒有消失,還繼續以嶄新面貌,不斷被建築起來,其實際作用亦由抵禦外敵和盜賊,轉變為防犯內部的「敵人」,全球化年代不單沒有終結「高牆」,反而透過人、資訊和科技的全球高速流動,變相鼓勵世界各國築起更多高牆。美國外交事務專家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在《牆的時代》的導言裡說,八十年代美國的列根總統,曾站在分隔東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向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喊話:「拆掉這道牆吧!」馬歇爾指出當時有知識份子曾倡言「歷史的終結」(指法蘭西斯.福山),但歷史並沒有因此終結。其中一個表徵就是全球化將各國在地緣和意識型態上的衝突白熱化,因為冷戰時代的鐵幕既是兩大陣營的區隔,也是各國政權自保的壁壘。如今,在全球貿易、資訊和科技流通的大趨勢下,各國政府必須直面來自敵對陣營國家附帶在國際活動框架內的木馬式侵擾。所以,世界各國政府又重新以各種理由,在邊境、國土內和網絡上修築各自的長城。
書中第一章談及的是中國。古代長城曾經是用來抵禦外敵的高牆,但國土的遼闊增加了修築長城的難度,也相對令平民百姓感覺皇帝和京城距離他們更遙遠,尤其是來自江南豐腴省份的百姓,更感覺不到那些北方民族的威脅。上述這些感覺非由古代中國人所寫,而是由明朝(最後一個修築長城的朝代)滅亡幾百年後,生活在千里以外中歐布拉格的猶太德語作家卡夫卡寫出來的,他對這個帝國臣民心態的描寫竟然無比準確!不過提姆.馬歇爾要說的不是這些,而是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下對宗教、少數民族和社會的箝制。卡夫卡那個短篇小說中的主角,自小必須接受築牆的訓練,時至今日,中國軍方以及進行網絡管理的部門,也把保護網絡長城視為關乎國家興亡的訓練。在地緣層面來看,古代中國時刻提防中國西部、西北部和東北部的少數民族,如今中國政府依舊提防著西部、西北部和東北部的少數民族,不過是從邊疆的長城變成邊遠省份的維穩政策,什至是今日惡名昭著的再教育營。
與今日對維吾爾人杜漸防微的中國相比,美國也有其不光彩的過去。黑人問題固然構成美國內部(如南/北、貧/富之間)的高牆,提姆.馬歇爾指出美國白人佔人口超過百分之七十,而黑人只佔百分之十幾,但黑人被謀殺的比率卻是白人的數倍。但近年來更被人注意到的,無疑是特朗普上台後聲言要在美墨邊界建造高牆的言論。而事實上,這不是特朗普開創的,早在奧巴馬當總統時,美國已在墨西哥邊境築類似的高牆,而特朗普雖然夸夸其辭,實質上卻沒有付諸行動。美國雖然口口聲聲要防止墨西哥罪犯和偷渡者湧入,但追溯歷史,早在十九世紀初,加州、德州等美國西南州份仍屬墨西哥領土的時候,是墨西哥政府鼓勵美國移民開拓當時仍然貧瘠荒蕪的上述各州,是後來從美國湧入當地的「新移民」(佔那些州份大部份人口)要求脫幅而去,才令這些地方成為美國的領土。
中美例子說明了這些「高牆」的軍事特質:它們原來為了捍衛歷史上的「侵略」成果而建造的:清朝征服了今日新疆準噶爾和回疆,美國征服了墨西哥舊領土。相形之下,以色列的「高牆」亦一樣,而比中美兩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色列今日的國土本來不是猶太人的土地,是以色列軍隊不斷掠奪巴勒斯坦原居民的居留地,將後者殺害、逐出家園的成果,猶太人本身已生活在四周不屬於他們的土地。另外,以色列的猶太人來自五湖四海,其主要兩大族群阿什肯納茲(Ashkenazi,即東歐猶太人)和賽法迪(Sephardic,即北非猶太人)之間,即使信仰相同,在文化上也有極多相異之處。
政治學者溫蒂.布朗(Wendy Brown)曾寫過一篇探討圍牆與主權關係的論文,後來出版成《圍牆內的國家,衰落中的主權》(Walled States, Waning Sovereignty)一書。布朗在書中勾勒出全球化標誌著國家主權的衰落,無力控制外來移民及其帶來的問題,因此越來越多國家在邊境修築圍牆,如印巴分治後印度在東巴基斯坦(孟加拉)邊境或鄰近孟加拉的阿薩姆邦修築圍牆,南非為防止疫症而在津巴布韋邊境做同樣的事情,等等。布朗的研究還仔細標示圍牆的設計。但布朗真正想說明的,是現今民族國家正經歷一場存在焦慮,需要修築圍牆來捍衛自身,也透過滿足這種民眾的慾望,重新凝聚民眾的向心力,就像特朗普競選總統時說build the wall,但沒有認真計劃過在德州與墨西哥的漫長邊界線上興建圍牆,他只知道這句話對民眾支持的威力。
不論是因為軍事征服與被征服者的反抗,抑或是因為對跨境移民和難民的防範,多國政府不單在邊境,也在國境內加築圍牆,內部圍牆的設立,既有防止族群衝突的作用,也有提防非主體族群的作用。以色列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地區並不斷加以殖民,雖聲稱西岸多處土地為其領土,然而層層疊疊的圍牆,又彷彿將領土與領土之間重重隔絕,巴勒斯坦人出入家宅時都要穿過重重的圍牆。內部的圍牆本來是為了防範外敵,然而現在變成防範已經「被統治」的屬民。而圍牆從最初只是橫亘於邊境線,至現在伸延到國內每個族群之間,正如甘地夫人年代為了防範孟加拉移民而設立的圍牆,現在已廣延至用來區隔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高牆。
高牆本是我們或一國政府為了自保而設立的,但高牆反過來也成為國與國或族群與族群之間桎梏對方的武器。溫蒂.布朗說當代的高牆已不再像古代的城堡防禦敵國入侵,而是防止後現代世界中的非國家行動者(non-state agents)如個人、族群、宗教群體等,但對鄰近地區群體的提防,最終卻淪為強國蠶食或孤立弱國的現實。巴勒斯坦明顯是這樣的例子,而孟加拉三面與印度高牆接壤,出海口經常發生海嘯,更像一個隨時會被環境災害毀滅的國家,而在鄰近的佛教國家緬甸被壓迫的羅興亞回教徒,也大量湧入孟加拉國境,使問題更加嚴重。羅興亞人也湧入印度邊境,而在附近緬甸國境的納迦族(Naga)經常反抗緬甸政府,叛亂者經常逃入印度,令問題更複雜。
我們出於對雞盜賊的恐懼而修建高牆,時至今日,高牆是用來防範雞蛋的,基於恐懼雞蛋的反抗或雞蛋之間的衝突會殺死建造並管理高牆的部門,面對雞蛋的挑釁,高牆毫不手軟,什至前者肝腦塗地,但強大的高牆,其存在理由就是出於對雞蛋的恐懼。其實村上春樹的比喻很粗疏,蛋殼本身也是一堵保護蛋黃和蛋白的牆,高牆與存在者的本體關係密切,正如人沒有了皮膚,細胞失去了細胞壁,都會死亡,而人體也有無數幅保護各細胞、器官的牆壁,佔人體相當部分的重量。
牆壁會保護我們,也能封閉我們、窒息我們,它幫助我們定義我們是誰,亦強行局限了我們的身份。政治源自群體及其自身認同,但所謂「群體」或「認同」亦意味著必須首先接受一道外在的高牆。沒有高牆,我們什麼也不是,但高牆既能使我們成為什麼,也能使我們什麼也不是。與卡夫卡一樣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希臘詩人卡瓦菲斯,早年曾寫過一首名為〈牆〉的詩,很切合身處高牆內外的人類處境:
沒有考慮,沒有憐憫.沒有羞恥,
他們已經在我的周圍築起一道道牆,既高且厚。
此刻我坐在這裡感到絕望。
我什麼也不能想:這個命運啃著我的心——
因為在外面我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當他們在築這些牆,我怎麼會沒有注意到!
但我不曾聽見那些築牆的人,一點聲音也沒有。
(黃燦然 譯)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