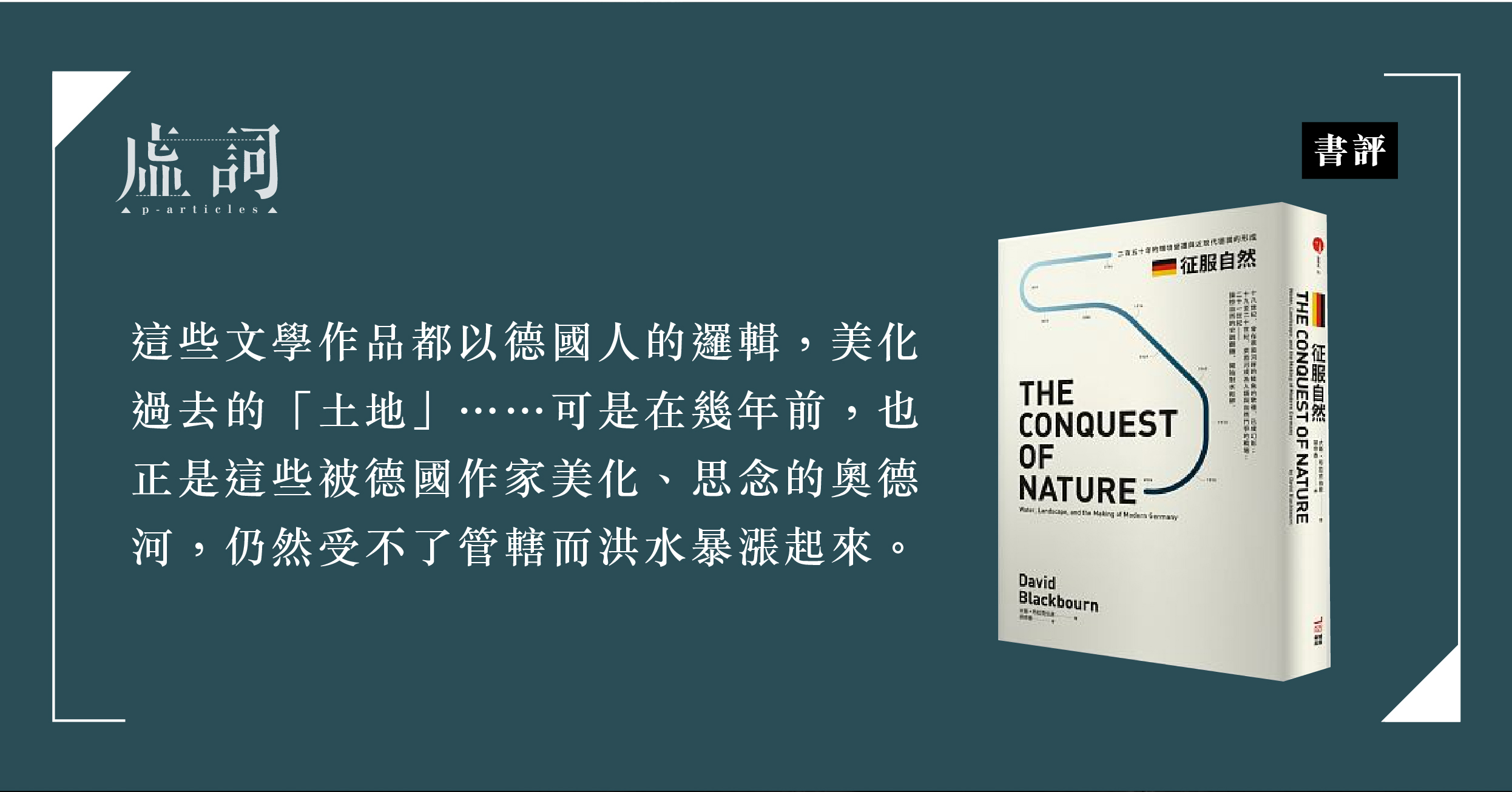自然與德國人的土地情意結
說起德國的文學,大家可能會想起歌德的《浮士德》,這部詩劇至今已成為世界文學名著,大家可能會想到浮士德向魔鬼出賣靈魂,但當中更多的是歌德對自己一生的反思,甚至當時德國的境況,例如浮士德幫助皇帝印鈔解決財困,作為交換,皇帝送給他采礦的特許權,活脫就是當時銀行家、資本家崛起和資本主義誕生的寫照,而後來浮士德幫助皇帝打贏內戰,因此皇帝劃出海灘一地作為其封邑,以及浮士德在封地上填海等情節,又令作為香港人的我們,想起政府填海與地產發展項目等熟悉的話題。金錢是萬惡之物,但我們都需要它,得到它的辦法就是從自然中盡情予取予求。
談地貌,也是談人文
然而每個人對物質總有著無限的慾求,世上人類如恒河沙數,在大自然面前卻如此渺小,人類的悲苦在於此。從歷史上看,德國人總是一早就察覺到自身的侷促,從中世紀征服波羅的海地區的條頓騎士團,到現代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理論,無一不是針對生存環境的征服,而這一切征服都被冠以「進步」的美名。大衛.布拉克伯恩的《征服自然》中,就將德國在這二百五十多年間,政府人民以開闢自然為名與河川、地表進行的鬥爭,還有當中所付出的代價,極為生動地描繪出來。這並非單純從科技史、自然開發史及自然變化(如水文、地貌、氣候)去剖析問題的專題著作,而是更像一部德國政府與大自然搏鬥,或試圖改變自然的集體傳記。作者透過這些人的作為,討論二百五十多年來德國自然的觀念變化。
要討論這二百五十多年來德國人對自然的觀念變化,就離不開梳理啟蒙時代到浪漫主義思潮,本書開宗明義就是一部思想史,這部思想史的開端源於德國人生活其中的自然環境﹕在德國尤其是普魯士境內,沙地、沼澤多,肥沃的可耕地少,河道經常泛濫,而二百多年前的啟蒙時代歌頌科學與進步的論調,正好為他們束縛、馴化、壓制、征服自然提供了理論根據。蘇格蘭啟蒙哲學家鄧巴爾(James Dunbar)的話:「讓我們學會對自然宣戰,而不是對我們的同胞宣戰。」更鼓舞他們向蠻荒的自然開戰。另一種極端態度源自浪漫派,當中包括華滋華斯等對大自然的讚美,歌德在《少年維特的煩惱》中也謳歌純淨美好的大自然,如此美好信念也表現在影響納粹深遠的,二十世紀初的漂鳥運動(Wandervogel)之中。
作者在引言及第一章裡談論種種對自然的態度。作者說:「書寫近現代德國地貌如何塑造,就是在書寫近現代德國本身是如何塑造的。」這話聽上去也許有點誇張,然而想到德國社會、科技及工商業經濟在這兩百幾十年才開始起步,在十九世紀的短短幾十年內追過英國、法國,甚至扭曲到發動自我毀滅性的世界大戰的地步,也許就會看得出這個主題在德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地位。從德國人身上,我們知道無論我們怎樣看待大自然,大自然對於我們都是一把兩刃劍。在德國文化中,既有以科技驅使自然為人類服務的信念,也有保育自然的觀念,後者或許與德國人特別濃厚的基督教原罪觀念有更密切的關係。在近現代德國的政治意識型態中,我們發現,不論是普魯士式專制、納粹主義、社會主義,抑或是當代德國式的資本主義,也離不開如何取捨這兩種態度。
德國版明日大嶼?被管制的自然
故事從普魯士君主腓特烈大帝整治奧德河岸的計劃開始,繼位者腓特烈二世則繼續改造奧德河岸的奧德布魯赫,並勒令東普魯士省長抽乾蒂爾西特市附近的沼澤地。這些「偉大工程」所奪去的人命可媲美彼得大帝填平聖彼得堡原址沼澤時罹患瘧症而死的民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這些沼澤地是冰河時期從斯堪的納維亞南下的冰川所遺留下來的,它們除了阻礙農業發展,帶來疾病之外,還為逃兵提供窩藏之所。簡而言之,這些工程有助政府更無遠弗屆地控制及管轄每一寸土地。
類似的事例還可以在後面幾章裡找到:來自巴登公國的水利工程學家圖拉(Friedrich Tulla),在法國與巴登公國斟定萊茵河邊界,拿破崙擴大巴登公國疆域的時候,研究如何整治萊茵河道,這項龐大工程並非有利於萊茵河岸村落,有些本來不受水利困擾的村落,在萊茵河改道後卻被河道滅村,這項為了「數十萬人的福祉」的水利工程,曾遭受克尼林根村民的抗議,從經濟收益上看,讓巴登公國經濟受惠的「萊茵河的黃金」,也因為河水湍急而日見稀少;而歌德在阿爾薩斯(萊茵河對岸法國省份)時見過的四十五種魚類中,大多數物種數量大減,這對當地漁業造成致命打擊。人類為了控制自然所作的事情,有時候未必一定帶來更大的利益。
從萊茵河的事例中,也反映出《征服自然》所涉及的實質問題遠比作者梳理的複雜。基於篇幅所限,作者只能討論以人力改變水文、地貌等自然環境的計劃及其利弊,工業化及礦產業發展對自然的影響並不屬於本書討論範圍內,然而工業化正是令萊茵河魚類減少的主因。另一方面,在發現秘魯黃金以前,從中世紀起,萊茵河採金業一直成為當地王侯的財富來源,其對萊茵河地區的環境破壞也可以想像。畢竟布拉克伯恩只是聚焦於普魯士或德國所著手的明日大嶼式工程,對於工業革命前後經濟產業對環境的破壞也沒有太多著墨,而且本書的重點在於德國人的自然意識。
環保議題的政治內涵
關於這種日耳曼思維,讀者可以德國和波蘭的自然景觀作對比,在共產主義化以前,波蘭可算是中歐自然植被最廣袤的地區,而德國恰好是中歐工業化最徹底的國家。然而正如本書第五章所說的,在納粹黨崛起的年代,德國開始興起關於管治自然的種族主義論調,認為斯拉夫人(即波蘭及大部份中、東歐國家民族)的土地都是荒原,而德國人的土地則被管理得綠意盎然。十九世紀德國政府在未受控制的自然裡大興土木,而納粹德國政府則幻想著將歐洲大片土地變成純種德意志農民的耕地。雖然一種是「前瞻」,一種是「倒退」,但那種自詡能把自然管理好的傲慢想法,恰好與啟蒙時代那種要為人類生活征服自然的野心,同出一轍。
到了二戰結束時,德國被徹底打敗,分裂為東、西德之後,許多德國作家又開始緬懷過去的疆土,當中君特.格拉斯的小說《遼闊的原野》甚至以650多頁篇幅涵蓋近兩百年的德國歷史,透過筆下一個研究十九世紀德國小說家馮塔納(Theodor
Fontane)的東德檔案管理員烏特克(Theo Wuttke)去看從馮塔納那個時代到冷戰時代的德國地貌變遷。作者還提到東德作家沃爾夫(Christa Wolf)在小說《童年模範》中,將歷史與記憶和地貌緊密融合,也不禁令我們想到一位作者沒提及的東德詩人波勃羅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的詩作。他的詩喜歡描寫以前曾有德國人聚居的最東端地區,包括東普魯士、拉脫維亞等。按作者的邏輯,這些文學作品都以德國人的邏輯,美化過去的「土地」,以及在透過記憶哀悼德國東部這些「失落」的國土。可是在幾年前,也正是這些被德國作家美化、思念的奧德河,仍然受不了管轄而洪水暴漲起來。
這種思維一直延續到今日,作者帶領我們從中看到德國於「土地」(Land)的觀念如何構成今日德國的綠黨及綠色政治,讓我們瞭解到,為何環境保育在德國總是充滿了政治和歷史的意涵,即使德國人在慘痛的歷史回憶過後高喊「保育自然」的口號,我們也多少能感受到人類(這裡是德國人)對於能掌控自然的自信心,全然不理人類不過是大自然其中一個卑微的造物,然而作者並沒有作出任何評論,他只是展示出這段精神史,讓我們去自行判斷。或許,每個國家,對「土地」的複雜情感和聯想,都能扣連起被冠以「明日」的發展藍圖背後的情意結。
大衛‧布拉克伯恩﹕《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衛城出版﹕2018年10月)
(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