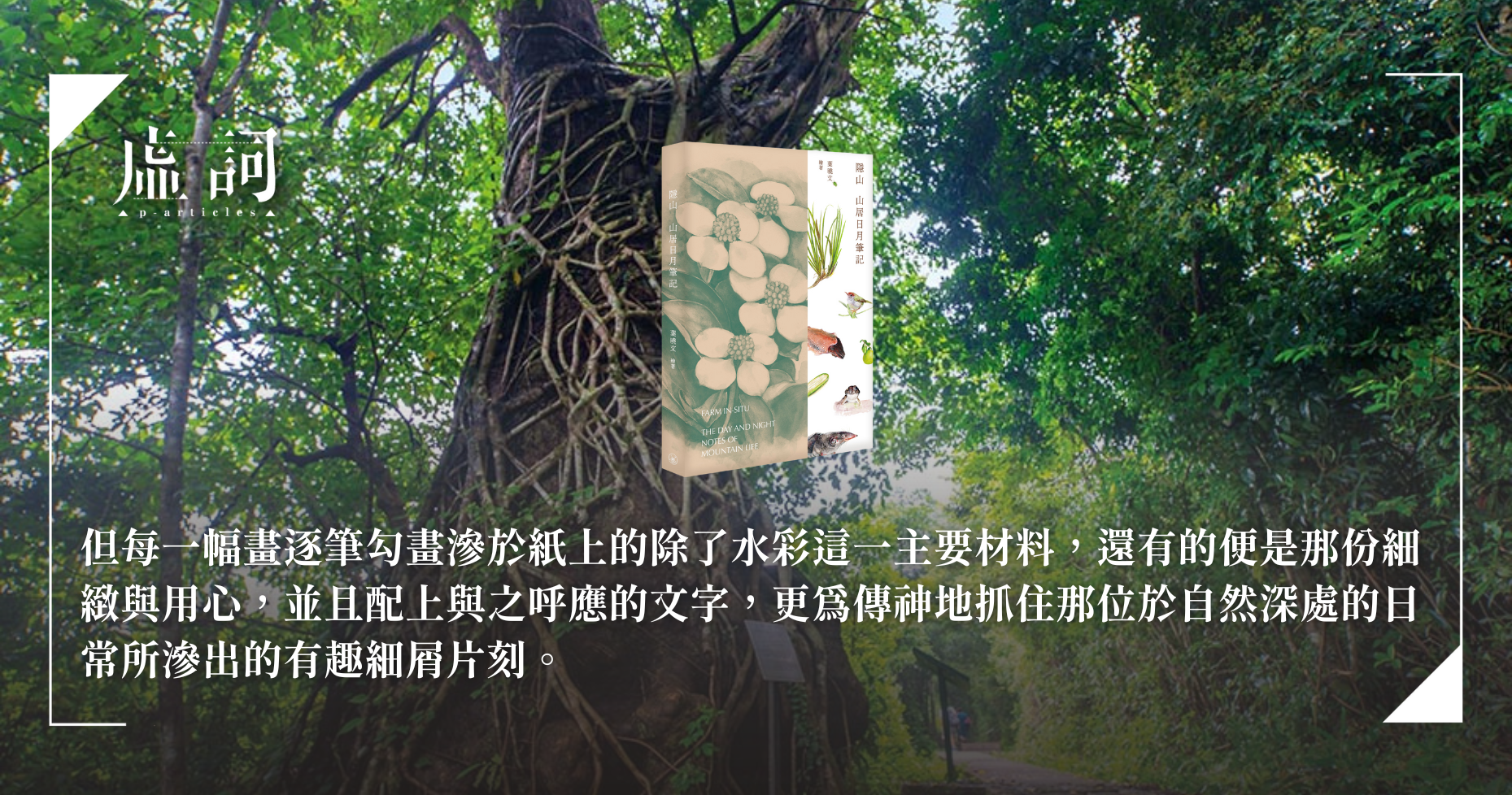隱世生活不隱世
書評 | by 亞C | 2024-12-02
香港作為一座公認的高密度城市,緊密矗立著的高樓,如潮般擠迫的人群,是此處最為常見的景象。不過,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其實尚餘很多自然和鄉村散佈在高樓之外。而這些遠離城市和人群,看似偏僻的地域,實際上也曾吸引着不少人前往,其中不乏從事藝術創作與策劃的人。在《方圓》的第八期中便曾收錄了查映嵐所寫的《香港鄉藝共通體源流》,文中列舉了多個鄉藝團體以及它們的發展歷程與源流,展示了那些遠離大眾認知,似乎常被忽略的鄉村地域,其實也與城市發展,社會氣氛乃至藝術創作擁有緊密的聯繫。那些未經「石屎森林」進駐的土壤,不但孕育著大量的自然動植物,也為藝術創作提供豐富的養分。
而在這期《方圓》出版的那年(2021年),自然書畫家葉曉文正式搬進了位於香港東北角落的荔枝窩,但她並不從屬任何特定的團體,這幾年內,她獨自在這個藏身於自然的原始客家圍村裡生活,並一直保持創作,將居於此處所經歷,所體會的種種,寫成了自己的新書《隱山:山居日月筆記》(下簡稱《隱》)。
不過對於這本書而言,單說「寫」並不準確,不同於其他慣常的散文集,《隱》的作者名下除了「著」,還加上了「繪」。因在《隱》中,除了多篇的散文(包括一篇小說),還穿插了多幅葉曉文所繪的畫作。
常說「書畫」,文字和圖畫這兩種不同的藝術創作形式,後者似乎往往更易吸引眼球,尤其在資訊發達的當下,文字彷彿常處於弱勢,遠不及圖片或影像般「直入人心」。但若將時間放長,這兩者的「強弱」彷彿卻是相反。被譽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王維,他那些數百年前寫下的詩似乎比起繪下的畫更「活現」於現今大眾的心裡,能背誦出《山居秋暝》也許大有人在,但相對較少人會知道《雪溪圖》是什麼模樣。即使是近代的張愛玲,十數年前寫下的文章現今仍不斷吸引著新舊讀者閱讀,並一直保持出版,但早期那些有着圖文並置風格的小說,無論是大陸或是港台的版本,大多都只留下文字,原與之相並的畫作在新出版的書籍中都消失不見,甚至可能有些張愛玲的書迷都不知這些畫作的存在。
但不論怎言,「書」與「畫」都是兩種十分重要的藝術創作形式,並且兩者編排在一起時,常會蘊藏著某種特別的聯結,產生各自單獨「存在」時所沒有的藝術效果。
《隱》之中的畫作基本全都是自然動植物,但絕非那種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製圖,就像書中幾乎每篇文章都會提及到某些動植物的科學常識,如所屬類別,生活或生長習性等,但大多都點到即止,不會深入至科學研究的範疇,反倒更像是各種生活日常裡的觀察和經驗累積所得。
但在荔枝窩居住的數年裡,曉文所觀察和體會到遠不止這些科學常識,深居大自然的生活也絕非僅限如此。《隱》書中分為紀年,四季,日月星辰,以及時光四個章節,主要都是以時間區分,但文章的內容與結構卻並非那麼嚴密。平淡筆觸寫下的文字娓娓道來的除了某種動植物所屬的科目之外,還有各種在身邊目睹碰觸到的,無論是夜晚偶遇到的青蛙,冬天朝早落田時碰見的形態各異,自遠方長途跋涉遷徙而來的候鳥,或是已洞悉牠們的行蹤,以及各自「親屬關係」的「牛牛朋友」們,都散佈於這隱世生活和書中的字裡行間。除此之外當然亦少不了曉文親手創辦的「隱山農場」內那些躬身耕作,悉心照顧下成長的各種作物,雖然這些作物大多並非如動物般在繁榮都市內無法覓尋,只會在人跡罕至的自然世界裡留下足跡,但在超市或餐桌上見到的那些如此熟悉的作物究竟是如何從無到有,在一片荒蕪之中成長起來,中間所歷的那一大片的空白反倒是曉文在荔枝窩的生活以及《隱》裡所寫的一大部分。並且亦少不了細緻地記錄下如何將收成的作物好好利用,製成如茶粿,糭子,或是帶有客家民俗傳統的「清明茶」與「清明仔」。
而這一切都是淡淡的。在那人煙稀少的隱蔽自然鄉村裡,常少不了神祕玄幻的情節來「引人入勝」,甚至還不乏「鬼故事」。但是經常路過空無一人甚至是墳頭的曉文,面對村裡某位以此恐嚇他人的長者時,唯一感覺是「好笑」而非「恐懼」,「活人的靈魂一樣是靈魂,我判斷靈魂的參照點不在於『生』與『死』,而是在於心地『善』或是『不善』。」(初一|披著星光夜行)
如此淡然且閒適。就像書中的畫作,並非有著極之高深的技法,也不是應放置於博物館,值上數千字評論的「驚世之作」。但每一幅畫逐筆勾畫滲於紙上的除了水彩這一主要材料,還有的便是那份細緻與用心,並且配上與之呼應的文字,更為傳神地抓住那位於自然深處的日常所滲出的有趣細屑片刻。比如在曉文寫到更習慣在朝早落田,除了逃避酷熱,還因清晨也是觀察鳥類的好時光。並且在冬天時節,位於南方地區的荔枝窩還會吸引不少「冬候鳥」和「過境遷徙鳥」駐足停留於此處。幾幅北红尾鴝,銅藍鶲,白鶺鴒的畫不但更直觀地展示並令人想像到何為「全身帶著金屬藍色」、「活躍又不大怕人的橘色毛球」、「以優雅的碎步行走並上下搖動尾羽」的模樣與姿態,還勾勒着雀鳥在清晨時分原來也會和人一樣,「大概剛睡醒不久,總帶著半分痴呆。」(聖誕節|麂鹿與冬候鳥)
這些細碎而有趣的日常小事,就這樣彷彿從自然,從書中來到身前。
但是,終究是不同的。
在荔枝窩的黎明除了可碰見各種鳥類,在草坪上還可觀賞到很多蜘蛛網,「蜘蛛把網結在矮小的禾本科植物上,平時並不起眼,然而在夜裡捕網眾生的淚與夢,並在清晨凝結水珠,織成白白的,細緻的小網兜。」除此之外,曉文還寫到如毛蟲,樟天蠶蛾,螞蟻等蟲類(一炷香|山中的蚊蟲)。初讀時只覺如其他描寫作物,鳥類或其他動植物般,但轉念想起幾天前發現自己房間內莫名出現部份不知名小蟲在牆壁爬過後,連忙噴上了大半支殺蟲水,心中方覺那些感覺稀鬆平常,貼近著生活的種種,其實只是個美麗的錯覺。
正如書題所寫的「隱世」,畢竟根據導航,比如從金鐘這一位於香港中心的地方出發,前往荔枝角需乘坐地鐵至上水,然後轉小巴到達沙頭角碼頭,再在碼頭搭船方可到達,共計歷時近三個小時,堪比乘坐飛機從香港至臺北。而這遙遠而周折的路途便為此處逐點褪去城市的痕跡,並瀰上層層濃霧,籠罩保護著這迥異於外界的世界,旁人亦甚少能碰觸或看清其中。
不過陶淵明筆下的那些生活在不知秦漢的桃花源居民們會千叮囑萬吩咐誤入其中的漁樵萬勿洩露此次行蹤,但居於此隱世村落的葉曉文卻恰恰相反。
「老實話,我以前是自閉童,不說話的,像塵埃,最好你看不見我,但我竟然終有一天以講課為事業,口講不停,這是我人生中其中一項最謎樣的事情」(甲辰|龍年)。而更「謎樣」的是,這改變是發生在曉文搬離城市之後的。
《隱》之中不少章節都曾提及到曉文帶領著學生或其他來自城市的人們前往這個隱世角落,構建着此地與外界聯通的橋樑。比如其中一位男同學隨大眾一起領取到在隱山農場種植的西蘭花,但志在的卻是西蘭花上面的粉蝶幼蟲。西蘭花絕對屬於平時最常食的蔬菜之一,家中老人教落,每次炒之前要細心清洗乾淨之餘,還要先稍微烚一下水,這不但可以令西蘭花之後炒完吃起來更腍甜,還因它極之容易藏污納垢,像其他蔬菜般單單用水清洗尚不足夠。但是在市場出現的西蘭花大多都絕不會出現這「倒米」的害蟲。只是未曾想過深惡卻「素未謀面」的幼蟲雖會影響生意,更是不可放進口中,但卻是不可多得的觀察的好對象。
而這與外界的聯繫,也並非是單向的。《隱》之中還提到了嶺南大學的教授安東尼曾將校園水池裡撈得十數條蝌蚪贈予曉文,由她帶回荔枝窩細心培育數十天後蛻變成為了青蛙(午夜|夜裡蛙蛙叫)。青蛙是由蝌蚪蛻變而成,這個常識年紀很小的時候便於科學書上獲知,但未曾親歷,更未聽過有人嘗試,畢竟身處自然環境方可將最後躍動的青蛙「悉數放回出生地,讓牠們開啟自己的生命故事。」並且說來汗顏的是,嶺南大學的那個水池過去自己曾經常經過,只知有着不少彷彿踐行着某種理想生活狀態,每天不動絲毫如蠟像般的烏龜,卻從未留意過原來水底竟浮游生長著不少蝌蚪。
回到文首所提查映嵐所寫的那篇文章結尾,「一種包含傳統工藝、民俗信仰與儀式、農耕技術與本土自然風貌的嶄新原民性,正待更多的悉心灌溉,假以時日,或可滋養港人的本土想像。」而葉曉文便正是其中一個親身實踐並悉心灌溉着的人,而且還努力將這些易被忽視,常隱在暗處的屬於香港的自然與文化,運用自己所創作的書和畫,令其不再「隱世」,浮現於更多人的身邊。而這本《隱世:山居日月筆記》絕對便是其中一重要的養分,「滋養港人的本土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