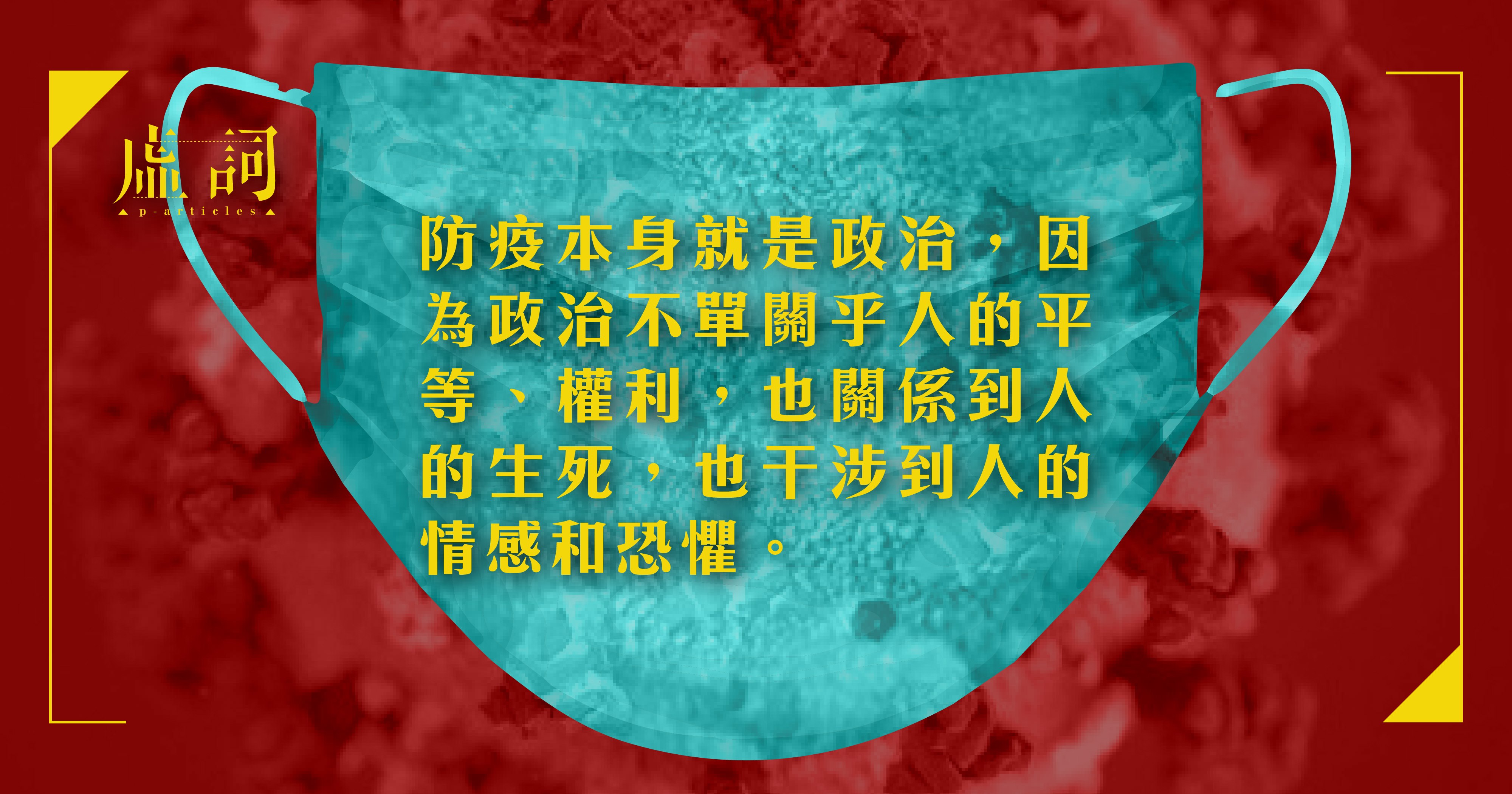【時代抗疫】防疫與我們的共同體
反送中運動延續大半年,香港政府對五大訴求仍然無動於衷之際,新型冠型病毒從武漢向全國各地,甚至全世界擴散,又蒙太奇地將香港帶入一個新的困局﹕疫病患者四處走動,不封關等於放任疫症擴散,可是在經濟疲弱的情況下,封關意味著厭棄中國大陸社會。當習近平頒令各省市嚴陣以待後,相對內地各省市立即封城,封路的措施,香港政府日益顯露出這種偏向不作為的窘態,尤其是前後考慮將粉嶺未落成的暉明邨,及鄰近美孚新邨的饒宗頤文化館用作隔離區後,更引起鄰近屋邨 / 屋苑居民嚴重不滿,令警民對峙的場面,重新出現,連此前反對抗爭活動的藍絲市民也怨聲載道。香港政府的顢頇無能,可謂表露無遺。
此時此際,大家都都對比十七年前,香港政府應對沙士一疫的措施,指出當今政府的無能﹕當時政府全面隔離爆發疫情的淘大花園,將淘大居民遷徙到遠離市區的渡假村救治,亦不失為一合理的辦法﹔然而今日香港政府卻選址在位於粉嶺社區周邊狹小山谷下的暉明邨,不禁令人懷疑今日香港政府的智商和居心。說起沙士一疫,我們也會想起當時特首夫人可笑的叮囑「千祈千祈千祈,洗手洗手洗手」,以對比今日特首的麻木不仁。除了勤洗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莫過於當時衛生當局呼籲市民採用稀釋度1:99的漂白水清潔家居,而文學界的朋友更會想起鍾國強的詩〈1:99〉﹕
當我是1,你是99
當我把稀釋的漂白水倒進浴室的U型去水位
當我第23次用酒精紙巾揩抹雙手
當我嘗試再用點力,擦掉杯沿咖啡或茶的陳跡
今早,床腳下的灰,有一張收據
而幼腳蜘蛛大模大樣爬進相架背後露出便便大腹
給昨夜弄疲了的蜻蜓在光管下仰臥
我在網上第129次重看關於自己的信息
化名嘲諷,攻擊,然後矢口否認
自己是另一個自己很快便忘記的名字
當我拉開戴久了的口罩嗅到一股噁心的氣味
當我打開房子的頂蓋,警告上面一個也不認識的鄰居
當我開始學懂在骨碌碌的眼球中辨識新的符號
今早,電梯門打開,人群匆匆向兩邊的空氣稀釋
而一聲咳嗽可以免費換取身邊偌大的空間
維園一株樹木獨對躲開了的玻璃森林
我走過的路給自來水猛烈攻擊,電梯扶手
迎接盡頭塑料手套一團一團濡濡濕濕
圖書館緊急疏散前,我被一列一列靈魂拒絕
當我攤開地圖發現走過的地方從未走過
當我遮蓋眉眼露出下半臉的白色口罩
今早,當我揭開報章找尋醫院的新鮮數字
一隻僵固的蜉蝣正把蜘蛛驅逐出游絲
而我不敢開窗只得翻檢儲物櫃和抽屜
發現小津的秋刀魚塵封在希治閣的後窗
我問我們的結婚錄像要不要轉成光碟
你說你高聲地說誰看呢誰還看呢我說
甚麼甚麼隔著門廊走道隔著那麼多東西
當我用稀釋的漂白水洗過我們走過的地方
當我第221次用酒精抹盡所有扶手
當我取出萬能膠,嘗試黏回暴雨後霉脫的牆紙
今早,過期月結單內,有蟑螂乾屍
當你是1,而我是99
2003年10月10日
——收入《生長的房子》,2014年初版。
1:99的鴻溝
這首詩之所以為人討論,並不是因為1:99切合當時的話題,而大是因為詩人思考並突顯出1:99這種比例背後的本質,將1:99變成一個大而化之的母題,一種我和他者之間被驅離抑或被接納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限於戴著口罩或咳嗽的「我」與身邊人們的距離,我和你之間的婚姻關係的鴻溝,或者當下的「我」與舊物勾起記憶中的「我」(如一幀小津電影《秋刀魚之味》的光碟,反映詩人以往對電影的興趣)之間的關係,甚至電影映像拷貝(《秋刀魚之味》光碟)與真實生活拷貝(結婚錄像光碟)之間的對比。
寫詩的時候,詩人大概不會知道,1:99日後不單意味著漂白水稀釋比例,亦意味著富人和窮人以及窮人在人數上和財富分佈方面的相反比例,成為「佔領華爾街」的其中一個口號。這看似巧合,但1:99的對比並非A與B之間純然的對立,而是充滿質量差異和壓力的對比。無論我們把1:99放在淘大抑或華爾街,我們都可以感覺到這99並沒有把那1進行稀釋,而是兩者都總是處於不平等,而且各自孤立的關係,由詩首的我作為1的主體「當我是1,而你是99」到詩末的我作為他者「當你是1,而我是99」,鍾國強把猶太學者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我與你》(ch und du)中指陳的那種「我與你」關係變得不平等卻也立體化,而且透過「我=1,你=99」變成「你=1,我=99」的過程,表現出有時間維度中的關係扭轉。
疫病如影隨形,逃避可恥而無用
回顧今天,人們似乎沒有從沙士疫症的史例中得到教訓。當疫情驚動中央政府後,習近平下的命令是公然全面封城並進行軍管,變相在全省宣佈緊急狀態,而武漢高官則遙遠控制軍、政、醫人員的調度;然而在封城前夕,這座人口1100萬的華中重鎮中,已有500萬人逃到鄰近地區,他們中間又有不少人在其他省份,甚至在國外確診染病。薄伽丘的豔情小說《十日談》講述一班貴族為了逃避黑死病而避居山上,因為沒有教會權威的思想拑制,而放浪形骸。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薩德侯爵又認為《十日談》主人翁所標誌的啟蒙和思想自主,正是道德淪喪的起因,他將這種想法表現在小說《所多瑪的一百二十天》裡面,小說中的主角夢想逃避遍地血腥的大革命時代,在荒鄉中建立一座烏托邦,任意行自己認為對的事情,結果淪為性虐待和獸行的地獄。今日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帶著不知名病毒離開武漢的人,心裡多少厭惡封城或隔離所意味著的「不自由」,然而他們的自由亦以病毒擴散全世界作為代價,雖未至於主動施暴肆虐,其不責任的行為亦足見其道德之淪喪。
說到他們,不禁亦想起愛倫坡的恐怖故事《紅死神的面具》(Mask of Red Death),故事的主人翁普羅斯佩羅親王,在紅死神肆虐其轄地人民之際,挑選精壯貴族男女一千人,想效法《十日談》的主人翁那樣,躲在山上由一修道院改建的堡壘中,天天縱情聲色,以為這樣就可以不怕紅死神的來臨。從結局我們知道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疫病會如影隨形一樣追蹤,直到把你弄死為止,最好的辦法還是直接面對它。
防疫本身就是政治
至於「封城」,則令人聯想起古代中國對疫癘的處理方法,網上流傳各種武漢市面的照片,令人更加深了這種印象。十多年前,大陸曾上映一部影射沙士疫情的歷史電影《大明劫》,電影虛構明末將領孫傳庭屠殺隔離區疫民的做法,似為諷喻實施全面隔離的所謂狠招。電影結束時,孫傳庭在潼關一役兵敗身亡,反對孫傳庭下狠招的醫學家吳又可則去了江蘇運河,繼續行醫救人。而香港政府的做法恰恰與「封城」相反,它遲遲未決斷「封關」。作為香港市民,耳聞目睹香港政府種種不決策的決策,與及有待中央決策以證明其合法性的考量,我們很容易把香港政府的不作為和內地各省市的封城 / 隔離措施連結來看,得出香港政府不是出於人道考慮而是出於放生武漢外逃者的考慮而作出決策,從而質疑中央政府是否既又要封城封省但又暗地縱容武漢外逃者,並不禁猜度這種矛盾方針背後的動機為何。
從近幾週爆發疫情的亂象來看,我們處處看見主權和主權—地方關係的困局。雖然某衛生局高官曾經說過:「防疫不能有政治考慮。」但防疫本身就是政治,因為政治不單關乎人的平等、權利,也關係到人的生死,也干涉到人的情感和恐懼。為何我們會團結起來反對香港政府的防疫方針,那就是因為我們恐懼武漢病毒攜帶者不負責任地四處走動的行為(正如鄰省政府和平民亦同樣恐懼)。恐懼並非解決問題的良方,卻是共同的本能。這種本能把人連結成一個共同體,也能人的群體拆散或解體。
誰是「免疫」的「社群」?從拉丁文中追溯兩者的對立關係
意大利哲學家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在其成名作《群體》(Communitas)中,曾重新考掘西方語境中「社群」(community)一詞的本義。他考據原拉丁文communitas一詞的構成,抽絲剝繭地挖掘詞根munus的本來意義。根據埃斯波西托的說法,每個共同體都基於法律加諸每一成員共同義務的前提,而非預設每一成員他們的權利,或非所謂「共同的」(communis)「財產」(proprium)。他說,雖然munus這個拉文詞語可解作「禮物」,但並非指一件普通的禮物,而是附帶有相關的義務的,以此引證「社群」原意並非共同權利,而是掮背著共同的義務或責任。
「社群」的基礎是有規範其領域的「法律」,法律無遠弗屆意味著理論上無人能豁免其管轄。然而我們所熟知的「免疫」一詞(immunity)恰好意味著相反的事情,它的拉丁文字詞彙immunitas亦同樣源自munus這個詞語,不過本來有「豁免」的意思,它意味著某位成員可以免除某些義務或職責。是故當埃斯波西托寫下《豁免》(Immunitas)一書,他想探討的概念恰好是似乎在communitas對立的immunitas。
英語的「免疫」(immunity)一詞,源自拉丁文詞彙immunitas,然而immunitas本來只有「豁免」,而無「防疫」的意思,直到十八世紀,巴斯德、科克(Koch)等人為麻疹進行實驗時,immunity才獲得了今日生物學上的涵義。埃斯波西托提到薇依將「權利」連結到「義務」的時候,她所說的「義務」就是munus,而每個屬於一個社群的成員,之所以當然地享有權利並必須負有附帶的義務,並非生來如此或出於自發的選擇,而是社群法律將其munus加諸在每個人身上。但它並非蓋涵所有社群或共同體的普遍成員身上,而只是指某些特定成員能免除法律所規定的munus。
法律上的「豁免」大概是「政 / 法共同體」的內部黑洞,法律容許有些人不受法律約束,可以行使暴力就是最佳的例子。埃斯波西托有討論到班雅明在《暴力批判》中所定義的「立法暴力」(law-making violence)和「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加上薇依提出帶有強制性的「強力」(force),還有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在《暴力與神聖》中探討的「暴力」,這些都是很熱鬧的題目,另一位同樣喜歡探討法律 / 主權 / 暴力關係及生命政治的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亦經常討論。
以「防疫」為名,免疫於法律的中共巨獸
埃斯波西托在《社群》第一章談論「恐懼」時提到英國十六世紀哲人、《利維坦》作者霍布斯的理論,說明「恐懼」不同於「恐怖」,因為它是孕育政治共同體誕生的因素,正如此時此地,因「恐懼」死亡而要求「防疫」、「封關」的意願令香港人團結在一起,但我們也可以從中國大陸政府各種「防疫」措施中看到,中共這頭無限膨漲的主權怪獸,正運用「防疫」為理由,不斷強化維護合法性的暴力,他們不過將人傳人的武漢肺炎等同於疆獨、台獨或港獨等思想,需要動用整個法律系統進行「法律上的免疫化」(legal immunisation)。
身處中共防疫的亂流中,我們平日耳聞目睹的,大抵是這頭龐大的主權巨獸,怎樣運用由自身法律系統賦予、卻又豁免於法律監察的國家暴力,瘋狂地與恐怖的疫症作殊死搏鬥。在搏鬥中,這頭巨獸不斷加強社會監控的權力,並堂而皇之地宣佈緊急狀態,讓法律聲稱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權利,形同虛設。目前中國政府在湖北疫區及全國強制執行的軍管措施,包括拘禁、隔離懷疑患病者,及監控群體聚集的情況,亦符合社會信用系統的社會監控目的。作為哲學或政治哲學的課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現代法國哲人傅柯已透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討論了這個課題。他晚年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的其中一屆課程「必須捍衛社會」(1976年)的最後一講中,已提出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是一種能令人活著或死去的權力。及後在1977-78年度主題為「安全、領土、人口」的課程中,傅柯思考了現代主權在安全、領土,進而在人口方面實施管制的三大階段,並稱這是新自由主義政治典範。而及後的「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79年度),正好接繼了上兩屆課程討論的內容。
就現代主權的「防疫」原意來說,當然是為保障治下人民生命及整體安全而設立,但這種保障的邏輯又建基於主權假設一個外來的、危害共同體共同安全的外部敵人,不管那是疫症還是外部勢力,現代醫學甚至加深了人們視政體或共同體為一細胞的印象,外來的病毒會入侵,撕破細胞壁,然後細胞會死亡。在這種邏輯下,我們的生命形式(life form)事實上亦被這種集體或主權恐懼所產生的措施操控了。另一方面,這也暗合霍布斯對於恐懼和犧牲的論述,即我們因為恐懼因為互相殺害而死亡,所以把我們的自由甚至生命犧牲給主權,或者讓它管轄我們的生命。
免疫的唯一方法:從「生命政治」中想像新的可能
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接續討論傅柯生前在「生命政治」課題中關於「主權權力」本質的研究,阿甘本認為那是一種「操殺生的大權」(vitae necisque potestas),生命政治應該稱為「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見阿甘本大作《牲人》(Homo Sacer)),而埃斯波西托則訴諸對「豁免 / 免疫」(immunitas)的詞義,擴展到法律暴力(如警暴)、防止外部勢力、人工防疫這些範圍。本來法即或以天然個體或單細胞來說,其免疫系統亦有出現自體免疫(auto-immunity)問題的潛在風險,這是內在於免疫系統的疾病。德里達就認為每個形同細胞或個體一樣的政體(body politic),都同樣帶有這種「自體免疫問題」。
然而傅柯、阿甘本或埃斯波西托等哲人之所以討論生命政治,並不是要告訴我們生命不過受主權操控的事實,而是要讓我們去想像一種新的可能,傅柯認為古典哲學不乏教導個人重新管轄身體的篇幅,阿甘本從方濟各會苦修士生活思考一種全新的、不受社會或政權操控的生命形式,埃斯波西托則提出一種肯定性的免疫機制。論述方向和內容儘管不同,他們所看重的,都是個體如何反抗整個沉疴重重的社會或政治—法律機制。對埃斯波西托來說,整個共同體必須自行發展出一種全新的免疫系統,而不是服從於現在那種壓迫性的免疫系統。不管有沒有人傳人的疫症出現,〈1﹕99〉所描述的那種隔絕和疏離,都是整個社會的疫症。可幸的是,雖然我們恐懼,但仍未至於產生中國除湖北外其他省份那種自我毀滅性的恐慌甚至恐怖亂狀,然而出於恐懼,我們更要想方設法奪回社會決策的權力,不要讓這個政府的不作為毀滅這座城市。
〈小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