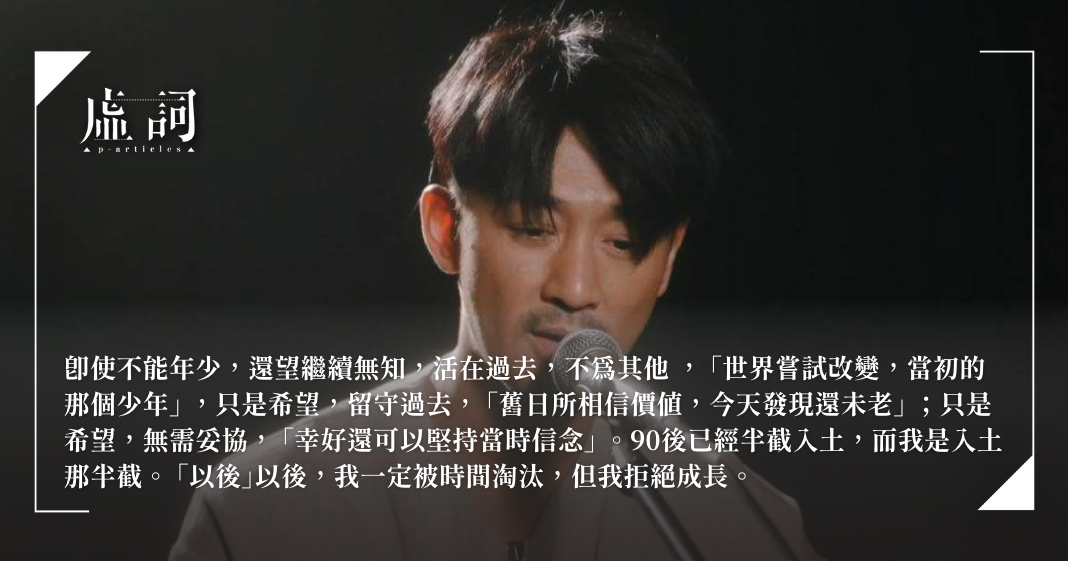【虛詞・同病相連】詩四首:〈菠蘿包 ——記骨關節炎病人〉、〈記一位大腸癌病人〉、〈我在天上的父〉、〈痛症〉
詩歌 | by 逍遙,陳新宇,梁一丁 | 2024-04-05
你的膝蓋不知為何 種在床上 痛楚落地便碎成玻璃的後代 躺回床上你一一領養 眉皺成手術刀 (閱讀更多)
【虛詞・同病相連】養病神醫
小說 | by 綠色衫 | 2024-03-27
這是一份自我診斷報告。病人姓李,洋名Eason,讀番書,養唐狗。今早上班後出現頭暈、頭痛、嘔心、焦慮、發冷、彷徨、失落、精神痛苦等症狀。初步判斷為錢財衰竭導致唔開心症候群,疑為醫學界新型病毒所感染。現在追蹤過去兩星期重點行程尋找感染源。 (閱讀更多)
【字遊行.倫敦/巴黎】賞墳
字遊行 | by 廖子豐 | 2024-03-27
廖子豐當過導賞員,亦是導賞團常客,特別是墳場和死亡相關的導賞。近年他參加了英國倫敦海格特墓地導賞團(Highgate Cemetery Walking Tour)和法國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Walking Tour),分別令他對生死和導賞都有所反思。同樣是當地最有名的墳場,但導賞員的選材和講解帶給他兩個截然不同的感受。參加導賞團的時候,觀賞景點以外,其實導賞也是一門藝術,導的,可以是社區,可以是概念,可以是種生活態度。 (閱讀更多)
【小克專欄】關於填詞的100件事(十九)
小克去年發表的詞作中,第一首是電影《毒舌大狀》的宣傳曲《毒舌神曲》,而他說「法律」是他不熟識的主題,幸好歌曲是由影像作品所衍生,可以從已有的故事框架構想,詞人的責任只是把握劇本中心思想。小克憶述從Gareth. T收到旋律,知道歌曲要先聲奪人以chorus開章,便精準道出主角形象,並加入了黃子華的棟篤笑形象,同時具有已成病癮的斷句及食字遊戲,可見廣東口語入詞的玩味性。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