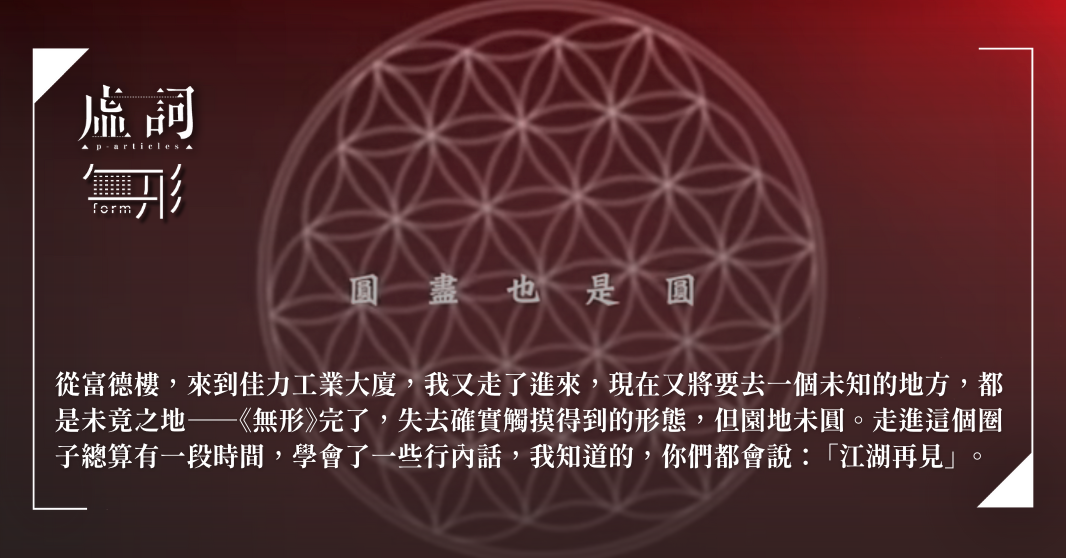關於「圓」,編輯曾繼賢想起〈生命之花〉的一句「圓盡也是圓」,然後嘗試尋找圓形的起點,沿著那些緣起順延下去,點與點之間的聯繫讓他看見了更多自己和香港文學的可能性。他說《無形》是一片園地,校稿散落於工作檯的四周,又像撒了一盤種子,而《無形》完了,失去確實觸摸得到的形態,園地卻未圓。 (閱讀更多)
詩四首:〈我是一個香港詩人〉、〈鷹〉、〈花期〉、〈自首〉
詩歌 | by 枯毫,石堯丹,馮松興,黑土 | 2024-04-22
我今日 立懸崖邊 崩雲 而仍寫詩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不屈平仄格律險韻 字字如金 (閱讀更多)
【無形・◯】Bez końca
無法再說下去,可以有很多原因。阿萊夫(Aleph)是希伯來語第一個字母,神秘哲學家認為,它的意思是「要學會說真話」。博爾赫斯借用到小說裡,將阿萊夫變成「從各種角度看到的、全世界各個地方所在的一點」,這個直徑約兩三公分的小圓球裡,每件事物都伴隨另一事物,無盡延伸。我們如何才能以貧乏的詞彙,去把握、傳達阿萊夫,言說不可言說之物?博爾赫斯又寫過,一本頁碼混亂、看過一頁後便會消失,以新一頁取而代之的沙之書。事情總如沙流失,如同遺忘才是記憶的主宰。那麼所謂寫作,是否在不斷的折損與消逝中,嘗試逼近,把當下的一點確定下來,留下可供記認的輪廓? (閱讀更多)
【無形・◯】無形易碎
見證著《無形》創刊的李卓謙說起《無形》的尺吋和紙質,第一期有著連logo都幾不可見的銀白色封面,以及薄到透光的雜誌紙,與易碎品無異,由此念及因《無形》而遇上的人們。在愈是虛擬的年代,他愈相信實體,又或不久會有新的文學雜誌出現——野草總是燒不盡,野草總是充滿生命力,而又脆弱。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