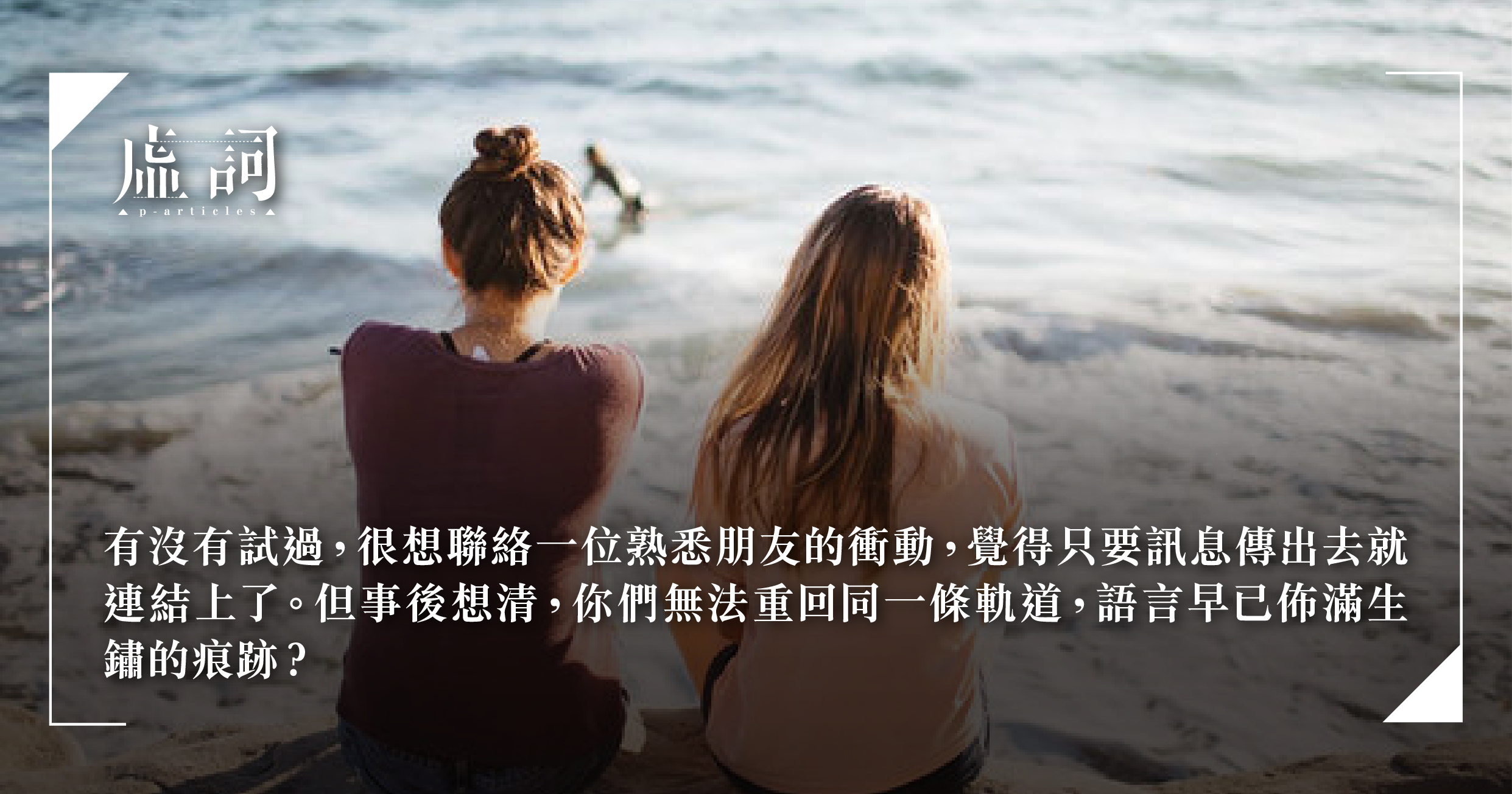T
1
窗外無星無月,藍黑藍黑罩著每一棟樓的頭頂,圍城夜晚一直都很靜,偶爾有汽車,駛過——又恢復寂靜。大部分公寓的燈也滅了,凌晨兩三點,睜眼的人有幾個?每次望見月光黃的街燈把整條天葵路刷得異常發亮,我就會想起圍城夜中多少個與我同樣無眠人士。爵士樂抒情地拉扯起潛伏已久的情緒共舞,爬梳記憶的同時,又成為另一種熟悉的背景旋律。
所有事物一去不復返,連記憶有天也會變成石化。
二〇一八年,塵埃在陽光底下滿天飛揚而我只是隱匿在光的背後不願現身。軟弱一刻曾想過找T,我們什麼都不說只坐坐就好?後來念頭打消,失聯過久,一切該從何說起?我的電郵、手機號碼、手機、電腦在時間軌道中符碼一一變更替換,生活不至於荒腔走板但實際上,與T已經相距遙遠。
時間走過二〇一九到二〇二二,然後就來到二〇二三。
2
V字電郵荒廢已久,沒想到有天為了尋找某張相片,輸入久違的密碼後,彷彿跌入異樣時空——在電子郵箱翻開一個世紀前的前塵往事:斑駁、雜亂、粗糙、令人懷念也有種種不堪。記憶的蝴蝶飛呀飛,青春童話由失落字符在半空中盤旋再盤旋,一半在偷窺自己前半段人生,另一半感覺每封郵件都顯得如此真實而厚重。經歷那些年的變化,由是我知道成長是艱難的。無論如何,如果青春期我曾一度感受「被寵愛」的感覺,那一定是來自T。
在十多歲投稿報章時,意外認識地認識到T,她是一位地道香港人,年少時勤奮好學,當時因家境問題沒上大學,後來在夜校補足,自學英文,程度好到可以隨時翻譯句子。一生獨身未婚,工作以外的時間奉獻給閱讀、學習、義工和教會。如果T是一位適合生活在陽光底下的女性(她身上具備所有滿足正向人生的好例子)那我必然是潛伏在暗夜裡的孩子:忙著跌撞與爬行。(所以我們的軌道注定分岔?)她對生活充滿感恩之心,善待與體諒他人,更重要的是:善用時間,從來不染一項陋習。當時我們交情很深,常常結伴出遊。說是朋友,更多時候她也在照顧我吧。
那年只有十二歲,生澀稚嫩的光影投射在身上,那就是T第一次見到我的模樣。
一個週六午後,地點在港鐵兆康站靠近嶺南大學的F出口,事先我們透過電郵相約(一如所有的網友)。後來路過,我都記認這裡曾直直立過一個瘦削身影,她手持一份報紙,沒有精心打扮但自然中短卷髮看起來十分柔美的身影。遠遠站在那裡,好像等了很久,走近時,她對我溫柔地微笑。
知性、有禮、皮膚白皙、善良溫柔,是T留給我第一印象。外型與台灣作家林文月相似,那樣的卷髮,那樣的優雅。你能夠想像這種老派式的見面嗎?
3
相識初期T在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碩士,所以我們一同走過嶺南這所校園。好幾次在嶺南樓飲茶、吃飯,聊天,填飽肚子後,也許她會回到圖書館寫論文,而我回到圍城的家中繼續努力溫習。如果時間較鬆動,我們也許會並肩走在離開嶺大的路途上,沿路步行到五分鐘到富泰商場的茶餐廳用餐。T十分喜歡有人情味的餐廳或小店,相對抗拒連鎖或集團式經營(在資本主義這大熔爐中,尋找縫隙。)大快活、麥當勞從來不是我們的落腳點。後來再長大些,我們移動足跡遠至馬料水中文大學,餐廳眾多她唯獨喜歡留在蘭苑吃飯,她說,那裡靜。
中文大學未圓湖畔一席青綠,抬頭陽光漫溢四周,是萬物復甦的春季,鼻翼聞見新鮮嫩綠的空氣。二〇一二年三月底我們來到未圓湖邊,白色巨型符號猶如從天而降隨後在綠草地上穩穩地躺平,上面刻了元問好的詞與北島的詩,為未圓湖增添了一份詩意。T攜來相機,讓我站在裝飾藝術前拍照,笑瞇瞇的臉部擠出一團肉,撇不開一絲青澀靦腆。但是T說,值得用鏡頭記錄眼前的日子。
T帶我走過許多地方,那時年紀小,對外間事物充滿好奇,凡是與文學文化藝術電影有關的靜態活動,一有時間她便撈我去,讓我張開感官認識校園以外的事物,發掘自己的愛好與興趣。印象中T十分節儉,只是對我這樣一個小妹妹,她從來不會捨不得。當時我拿著每週僅有的零用錢增值八達通,週末跑去九龍或港島會合她,電影票或展覽入場費、餐費一切由T墊付。當交通一來一回,八達通裡的錢像被老虎吃掉一半,回到家裡不時遇到母親碎念。T知道後,輕輕問:「我替你增值八達通好嗎?免得你跟母親常為錢爭執。身外物,不值得傷感情。」我沒同意,但一直記得她說:錢是身外物。
虔誠、真誠、獨立、孝順、謙遜、溫柔、克制、盡責……T的身上都有。我甚至認為,太多太重了。
4
報紙編輯不容易當,甚至比出版社編輯難度更高。儘管T負責的版塊是週報,但組稿、採訪、催稿、篩稿、校對幾乎由她一人完成,底下記者時有時無,同行者一時熬不住辦公室又剩她一人支撐。晚間下班時,月亮不知道爬去哪裡。時間已經慢慢爬到了九點、十點,甚至更晚。中環回到馬鞍山,夜色跌入更深更沉的黑暗中。有時夜深回到家了她還捎來一封信:「做事不能沒有熱忱,保持初心是很難的。首先你要喜愛你的工作,才會享受,付出再多也值得。」T不是修女,但始終一身潔淨、無瑕,甚至那一圈圈頭頂上的光環神聖至令我肅然起敬——很像向他人描述她的美麗與詭異,虔誠與溫柔,骨子裡始終有著一份堅硬如石的信仰。隱形牆在兩人中間漸漸築起,思想的偏差、行為的偏離,由此區分出信徒與非信徒之間——儘管沒受洗的我吃飯時與她一起祈禱,或走進教堂唸天主經或聖母經,聲音很細,也很尖細,雙手緊扣,一不小心就會扎疼了手。
回想從前,我們去過很多座天主教堂,很喜歡欣賞那些或尖或圓的拱頂、彩繪玻璃窗與充滿故事的壁畫,耶穌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聖經故事從小聽到大(還是依然忘記)。其中一年我們到訪廣州沙面露德天主教聖母堂,那次意想不到的旅行是唯一一次共同離境,搭什麼火車還是巴士嗎?我忘了。只是記認,那座小島非桃花源地,卻依然予人一種遺世獨立般的存在。街上每一棟殖民建築、每一座雕塑都獨特綺麗,古樹老根盤纏於地面伴著島上居民共同生活,那是真正的百年老街風景。出發前T說:「我預訂了勝利賓館,帶你去住好嗎?那是一座老字號,可以感受一下著名的歷史建築。」我不曉得賓館一晚多少錢,從建築外觀、裝潢到設施,看起來都不便宜。後來才知,勝利賓館建於十九世紀末,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曾經喚作維多利亞酒店。我們這次住在西樓,前身更是1920年建成的匯豐銀行,是沙面著名的古老建築。至今閉眼我還能記起房間的氣味、木質深色傢俱佈景,兩張單人床,我們各自躺在床上聊天的時光。
在此行之前,我們中間曾斷了一年的聯繫。彼此不相往來。
那是懵懂歲月的中段,因學校group project要採訪校外人士,當時與組員選定了出版行業對象,我心中自然屬意採訪T。但事與願違,在信件溝通上出誤會,也為T增添了些工作麻煩,採訪沒成,人也消失了。這不像T的作風,當時年少情深,恍如一匹緊密無間的布被銳利的剪刀割開了,很久還聽見撕裂的聲音。一年後她再次出現了,內心傷口好像迅速癒合(還真是因為年輕)。她邀我同遊,沙面之行,她才逐漸把一些潛伏在心底的抗拒因素告訴我,其中一些是無法宣之於口的秘密。那個長夜,我記得自己流了一些淚。
5
Dear V,
Wish you a blessed happy birthday. The day leads you to a new horizon of your new life.
Wish you a new life full of friendship, support, trust with true love and true hope. To become a person being cared and concerned but not fully occupied and 'booked'. To become a young lady learning to care and love but not to overlook the one(s) whom has/have given up oneself(ves) to be with you.
That is my words leaving to the 'good words' to those words of congratulation to your age 18's birthday!
May the Lord keep on bless and guide you day by day. Happy Birthday and Merry Christmas.
Peace,
T
這封信躺在郵箱十年了,生日的祝福,十年後,我重讀幾遍。
從通信的痕跡顯示,早在十一月初T已經開始規劃我的生日打算一起同行去哪些地方慶祝。我忘記自己當時在忙些什麼,課業或朋友,總之最後好像沒成行。
想起也慚愧,她在自己生命以外擠出一個小小的空間容納細小的我,只是後來我年歲漸長,沒有珍惜。
6
人人都覺得香港小,我們竟從來沒在街頭遇見。上大學後我們偶爾聯繫,上一次見面背景在台北,T來看我。事先她把機票訂好,旅館也是選擇靠近我學校的「師大會館」,她自己一手安排妥當。從香港來台北看我的人都住過那裡,包括當時的情人M,師長P,他們分別都住在同一處地方,是我很熟悉的場所。那些年,台北總是下著綿綿細雨,如我四季奮力卻拔不走的鬱結,悶成一坨濃縮在空氣。我和T坐在一間羅斯福路上的法式餐廳,她任我點豐盛所有喜歡吃的東西並且告訴我,別擔心價格。她來,主要是為替我慶祝即將邁入二十二歲的生日。那麼重視,那樣疼惜,每一年她都不會錯過,甚至在我們失聯的日子。那天是12月22日,T來台過聖誕節,卻故意不約平安夜。我記住了那天台北的毛毛細雨,記住了自己向T輕描淡寫台北生活的愜意,「我在這裡很好呀,同學都不錯,放假偶爾搭火車去台東花蓮旅行,也很喜歡逛這裡的舊書店。我覺得台北很好。」不符合T世界的語言,我把它們都吞進肚子裡。過去生活大小事都能告訴T,直到發現再也無法訴說的那天,才感覺到我們之間,明顯隔著一道江河。
也正因如此,我在台北錯亂、錯置、顛倒的生活,使得我們愈來愈疏離。
7
T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卻從來不對我傳播信仰。以前我們一起走進教堂,T唸經,我坐在木質長椅靜靜祈禱,結束後,T會溫柔地凝視著我微笑,然後一同離去,帶我到特別的餐廳吃飯。那些年不過十幾歲,T真的好溫柔好溫柔,與家人生疏但我不拒絕與陌生人親近。我們相識於二〇〇九,投稿文章被T採納,一段時間後遂來信邀請我在學生報章撰寫專欄。一寫就是幾年。(寫作種子也就埋下了?)當年筆名「惜」,記憶鎖在塵封的箱子裡。
大學之後,斷斷續續又通了幾次信,再後來,就沒有了。
有沒有試過,很想聯絡一位熟悉朋友的衝動,覺得只要訊息傳出去就連結上了。但事後想清,你們無法重回同一條軌道,語言早已佈滿生鏽的痕跡?
T不在身邊了,我必須承認,編輯種子種在心,是當年受T影響的。入讀中文大學的念想,也是因為T。我們好幾次約在中大碰面,走在山頂天人合一的地方,視線越過吐露港便到達對岸的馬鞍山,T告訴我家就在那頭。「假若你考進中大,我們距離就很近了,可以常常在這裡見面。」我記得那時T也在中大修讀夜間課程,與生命教育有關,才剛修畢文化研究碩士,又立即將頭埋在學業堆中,那真是典型的T。勤奮,好學,全力以赴,不浪費分秒朝夕。
後來我也順利入讀中文大學的研究生課程。
再後來我畢業了。
在我們相識十三年後,終於,我跳進大染缸成為她同行。只是這時她已悄然隱退,回到馬鞍山那間推窗滿眼翠綠山景的屋子裡,度過隱居生活。「你相信緣盡麼?」L問。當時沒有肯定答案,但我想我是相信的。有些時刻,曾經是一顆遙遠的星球,遠遠掛在半片天空,伸手但不可及。
說起來都好像昨日的事。
我只知道,緣分是很難說的。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