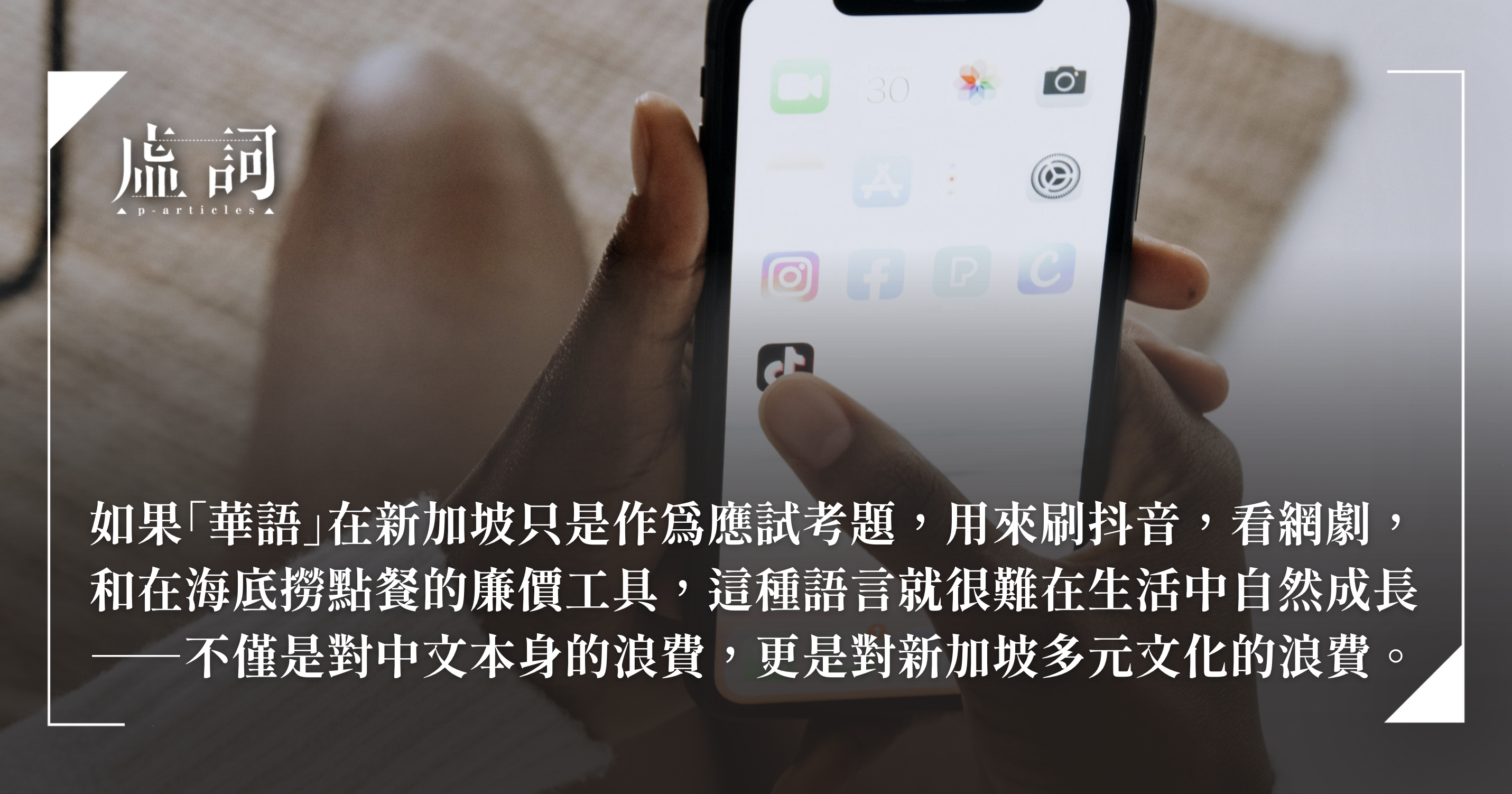驚蟄
鵝頸橋下屬三叉路口。三叉路口煞氣大,古人化煞為用,這兒自然成為打小人的聖地。適逢驚蟄,橋下塞滿了人,人山人海,硝煙瀰漫。亂世下,果然小人當道。儘使擺攤的神婆比平日多了幾位,但依然供不應求。噼噼啪啪,拍打聲此起彼落。神婆手起鞋落,打過不停,人潮倒是有增無減。 (閱讀更多)
【無形・進擊的動漫】反覆試錯——Monster Hunter : Rise
《Monster Hunter》今年邁入二十周年,蘇朗欣卻說在前年才初次接觸。劇情通關以後,她決定挑戰自己:用弓速刷一隻角龍,但即使組合出當前版本最強裝備,又灌藥、灑粉塵、放閃光彈,依然是屢戰屢敗。當她的完成時間由最初的15分鐘縮短至5分鐘時,她決定放棄,體認到速刷玩家的悲與喜:循環決戰上千次,才拍到那僅僅一段完美的通關影片,那快感恰好可以抵消無數次的失落和飲恨,而現實人生總不能一直如此反覆試錯。 (閱讀更多)
【無形・進擊的動漫】我看到的⼭就如你看到的水——《葬送的芙莉蓮》
被稱為近年的「暖⼼神作」,曾拿下漫畫大獎2021第1位的《葬送的芙莉蓮》並不是少女漫,但確確實實是我看過最浪漫的作品了,沒有之一。 (閱讀更多)
【無形・進擊的動漫】叮噹、「76」與烏托邦
叮噹是以「柒碌」為主題的。基本上,讀者可以輕易發現,叮噹的主題其實離不開叮噹不斷以22世紀的未來道具介入20世紀主題。早在漫畫的第一回〈從遙遠的未來世界而來〉(未來の國からはるばると),叮噹在出場後對一臉懷疑的大雄作出一直陪伴和照顧的保證後,他就將應該放頭上的竹蜻蜓誤裝在大雄的屁股,由於頭尻不分,大雄首次飛行經驗以短褲子脫落,直插地面受傷告終。被救後的大雄說了大長篇以外最有智慧的一句對白:「那傢伙,真的靠得住嗎?」在兒童眼中,當然我們可以提出《叮噹》嘅漫長出版歷史,係以來自未來的藍色機械貓為中心,富有人性地協助20世紀日本比平凡小學生更低能一點嘅野比大雄改變未來的故事。但對成人讀者(或是長大後的兒童讀者)來說,很多人都會像杉田俊介在《ドラえもん論 ラジカルな「弱さ」の思想》的觀察一樣,留意到叮噹的主題其實在描繪「失敗」與「軟弱」在結構深嚴的日本社會的深層意義。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