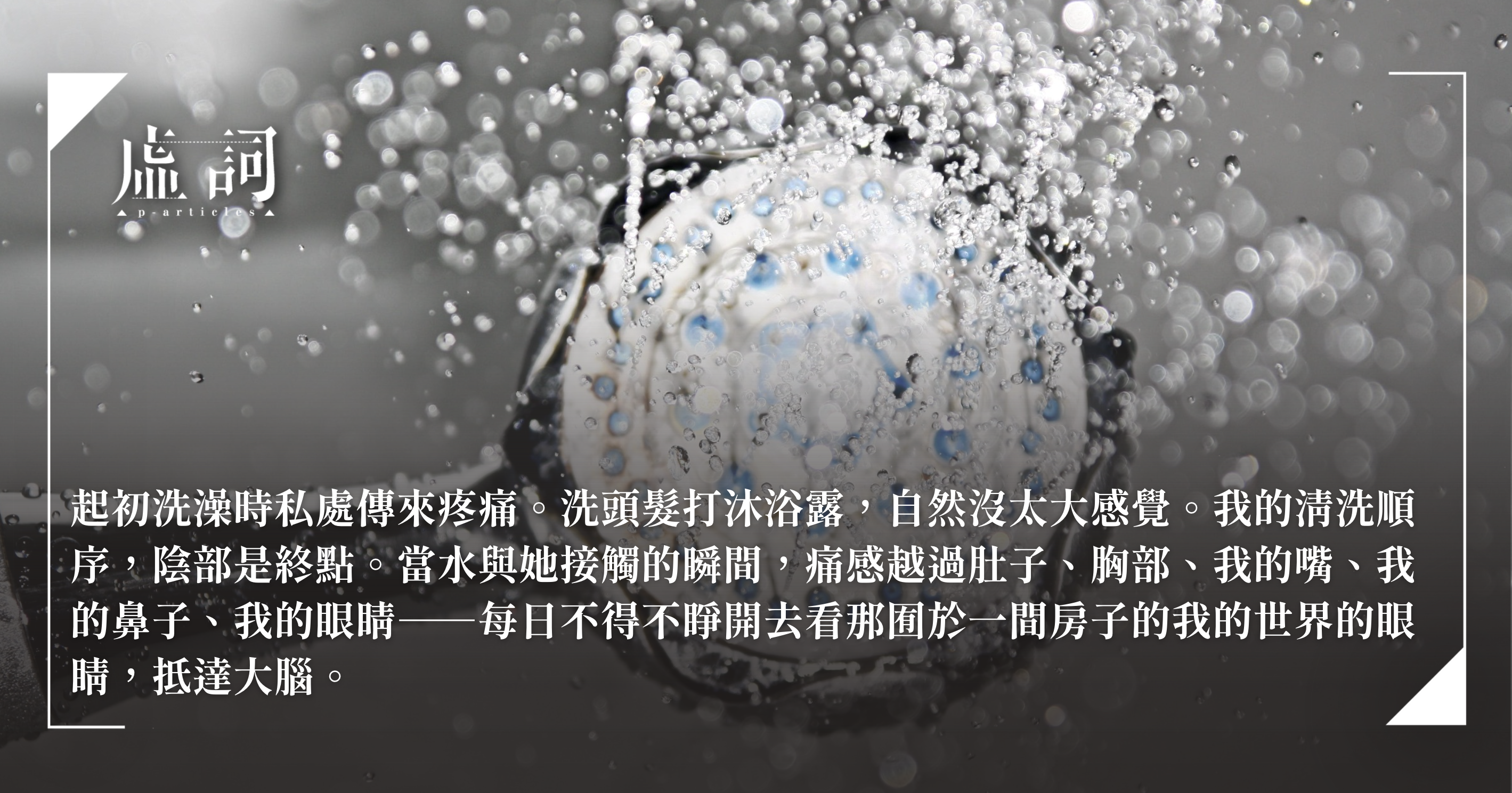【虛詞・過敏鳥】止癢
散文 | by 王萊姆 | 2024-01-26
紫棕色的痂,出現在床單。
那是2022年4月,從3月偶爾的小區自行封閉到4月的完全靜默,居家的我不再特意整理床鋪,不過是從裡間到客廳來回返赴,卻還是瞄到了那紫棕色的、來自身體的脫落。
起初洗澡時私處傳來疼痛。洗頭髮打沐浴露,自然沒太大感覺。我的清洗順序,陰部是終點。當水與她接觸的瞬間,痛感越過肚子、胸部、我的嘴、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每日不得不睜開去看那囿於一間房子的我的世界的眼睛,抵達大腦。
我沒停下,只要短暫的幾十秒去適應,那輕微撕裂感像是熱水澡的附屬品,不那麼難受了。長舒口氣,告訴自己本來就是這樣嘛,沒甚麼不對。
又這樣過了幾日,我開始懼怕沖澡。只要夜幕未降臨,我就不擔心疼痛襲來。它不只在水中出現,躺在床上聽到樓上傳來咚咚咚腳步聲的時候,癢從身體下方冒出,咕嘟咕嘟,和著咚咚咚,一大二大有節奏地律動。
我不停撓,再撓。打開手機,新聞告訴我哪裡又有破門而入的消息,社交軟件上有人分享自己搶到的菜,但這喜伴隨悲而來的時候,畢竟是少數。更多時刻,悲傷獨自前來,鏗鏘有力,於我當頭棒喝,而我無力承受,只能繼續撓私處的手。
這症狀絲毫未減痛,很快我可以感到那被撓的皮膚開始有突起,我會忍不住去撕,聚攏在一塊兒,然後被丟進垃圾桶。偶有沒清理乾淨的,就成了床單上殘留的紫棕色碎片。我用森綠色床單,我感到這澄澈被污染。我塗大量的身體乳,是嬰幼兒用品,我想用純潔去治癒這污穢。或許有起到止痛的作用吧,然而每次滿懷期待彎下身去查看,斑駁沒有絲毫好轉。我趕忙起身。
我開始思索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一個人的封閉,沒有性生活,每日洗澡,換洗乾淨內褲,以客觀角度來看,如此無暇,為何會裹挾疼痛與瘙癢,打轉。那一定是過敏,可是過敏的對象呢。
我不知道。
白天症狀平緩,在做飯和做事之間,它乖乖躲在體內,好似從沒來過般,我因投入也根本不記得這檔事。直到夜幕來臨。
就這樣持續一個多月,在上海宣布將於6月解封的前幾日,開始有「放風時間」,好像一戶一天2小時,同一時間只允許一人在外遊蕩。獨居的好處此時再加一,我不必和誰商討我們該如何分配,是時間對半分,還是今天讓其中一人玩個夠,隔天再換人。
我不會騎自行車,我只有我的雙腿,通過私處連結成完整一具走路工具的雙腿。走過天橋,在零散通行的陌生人中,走向某個地方。
背後腳步聲由遠及近,有位阿姨同我講話。她問醫院是往前這麼走吧,我說是的。她講自己如何辦到通行證,如何從閔行靠走路和公車來到這兒,印象裏是乳腺相關的問題。我的記憶可能不再準確,忘卻是自那時起習得的本能。
我們在路口分別。向左,向右。我那時根本不敢靠近醫院。
解封後的十幾日,我終於下定決心預約掛號。醫生大概只掃幾眼,便說沒事。這怎麼能算沒事呢。我洗澡時的疼痛,每晚抓的癢,是真的啊。醫生還是做了白帶檢查,我在走廊等化驗結果,看人來人往,我們的目光對視,也只剩目光可以對視。
醫生拿著化驗單,説一切正常。我們望向對方,無奈,給不了彼此想要的解釋。我只能返屋企,等待某一天恢復如常。
11月,在2022年終於要過去時,我在社交媒體看到「某某洗衣液出問題了!」,氣憤與釋然同時到達。我拿起陽台上的那一瓶,果然在問題批次中。是用了很多年的品牌,曾經以為貴價可以帶來品質。就像從家鄉來到上海讀書生活,認定文明先進的發達城市能夠給我尊嚴,然而沒有。
那個品牌在今年重新來過。我曾寫下投訴意見書,可從未收到過回音。於是,只能,不斷更換洗衣液品牌。
2023年要過去了。我的床單不再有皮屑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