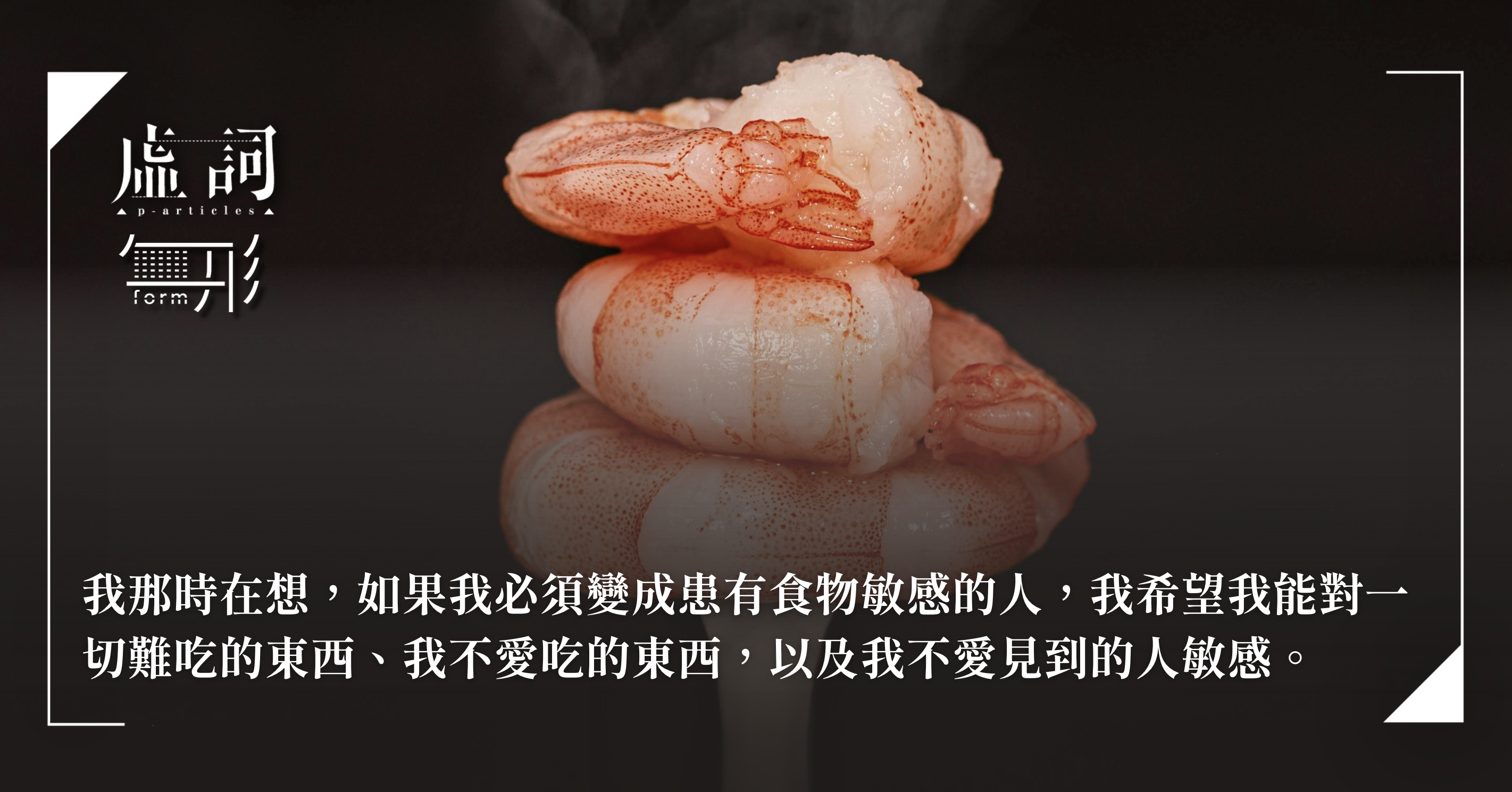【無形・過敏鳥】給阿蝦和阿蟹
親愛的阿蝦、阿蟹:
每逢跑過一學期,我就會去街市買半斤蝦或兩隻蟹。回家路上,滿足快樂。有件事我沒有在家政課和父母身上學到,就是劏:劏雞、魚、蝦、蟹,從前也不懂;現在還是不懂劏雞和魚,但可以劏蝦和蟹。我想,這是有關欲望的問題。阿蝦、阿蟹,劏開你們的時候,你們不會流出鮮紅的血,所以我不怕。
我自覺是個幸運兒,暫時沒發現任何食物過敏反應;但我偶爾討厭「食物敏感」,它帶來了對蝦、蟹產生過敏反應的人,以及對蝦、蟹產生過敏反應者的反應過敏的人。他們有時會不自覺地奪去我在餐桌上,理應獲得的樂趣。
自從某家親戚的小女兒出生後,我就避免與他們同桌吃飯。只要他們的小女兒在,桌上就沒有蝦蟹,說是小女兒對甲殼類敏感。我最喜歡吃蝦和蟹。長輩隨口跟我說,不如從此大家都少吃蝦蟹,以免多吃就變成對蝦蟹敏感。我當時太年輕,想不通。至於不能吃蝦蟹,是體質的問題,而不是阿蝦、阿蟹的問題這件事,我長大後才懂。
小女兒來吃飯的時候,就算是打邊爐,也要分成兩個鍋;不是鴛鴦鍋,而是多搭一個爐,多煮一個鍋。她的父母很喜歡送大家大樽大樽的營養品,某回送了我父母魚油丸和甲殼素。我那時在想,如果我必須變成患有食物敏感的人,我希望我能對一切難吃的東西、我不愛吃的東西,以及我不愛見到的人敏感。
這名小女兒因誤食甲殼食物而產生過敏的反應,我見過一次:嘴唇、舌頭突然腫脹起來,下巴附近的皮膚生出紅疹,任誰看到都覺她可憐。聽說這是輕微的情況;至於她從前有沒有反應嚴重至緊急送院呢,我不知道。致敏和中毒一樣,永遠是餐桌所揮之不去的攞命調味。不論是過敏的人,還是與過敏者一起的人,也只好順從,臣服。
踏入社會,在職場上遇過分別對蝦、柑橘、酒精和味精敏感的人。這些同事都只簡單地告訴大家不能吃某些東西,桌上有一道他們能吃的就可以;又或是建議去吃西餐,各自修行。他們也不會迫我吃我沒有過敏,但不喜歡吃的羊肉、蛇肉、豬肉、薑和辣椒。
外子有個舊同事對花生敏感,這同事吃午飯的時候,常常與店家弄得很不愉快。他每次在越式餐廳點「撈檬走花生」,店家都會不以為然,依然在他的食物中撒下一大把花生碎。我有次聽罷,便非常不近人情地問外子:「他不點撈檬,點湯檬,問題不就解決了嗎?」料想店家心裡想著的,也是同一個問題。
阿蝦、阿蟹,世上一部分人吃了你們,或者花生,就會沒命。可以吃你們的人,有能力、很樂意把過敏者的份一起吃掉,聽起來好像挺相安無事。韓劇《原來是美男》就有這一幕:男主人公黃泰京對蝦敏感,於是欣然讓女主人公高美女吃下自己盤中的蝦,順便逗高美女開心,多浪漫。只是,凡想到世上一部分人,每天會因為擔心誤食而滿腦憂慮時,這種想法聽起來又有點不道德。
高橋留美子的「人魚系列」,可算是她最殘酷的作品;因為故事關鍵「人魚肉」害人不淺,差不多每回都是悲劇收場,所謂「死得人多」。「人魚肉」是甚麼呢?就是充滿劇毒的人魚的肉。少部分人吃了人魚肉,會長生不死;但大部分人吃後,身體無法適應劇毒,會當場喪命或者變成失去人性的怪物「半人魚」。
這樣看來,吃人魚肉後會喪命或變成怪物的人,就是對人魚肉過敏的人。不能吃蝦蟹的人,不會變成怪物;但他們不是大多數的人,而是少數的。如果能吃的人較少,不能吃的人較多,這樣,不能吃的人就不再是異類了。
話說回來,那個對甲殼類敏感的小女兒打邊爐的時候,可以吃甚麼呢?我依稀記得是牛肉、蔬菜;還有一種我特別有印象,就是小女兒的母親要求我母親預備的白年糕。當年不易買到韓國年糕,連現在最普通的松鶴、宗家府年糕也是難求;寧波年糕又要花時間泡水,派不上用場。
母親最後買到一包來歷不名,極之難吃的白年糕條,還待大家都在飯桌前坐下後,鄭重地宣佈:白年糕是為別人的小女兒預備的,大家也不要吃。由於當晚大家都小心翼翼,只敢預備看起來比較溫和的淡水魚,沒有讓蝦蟹回家;因此,我覺得患了敏感的,其實是小女兒以外的人。我們都對很難吃的白年糕敏感,想吃的人就是找死。
阿蝦、阿蟹,用你們來炒宗家府年糕或寧波年糕,都極好吃。蝦的話,去殼挑腸,拿殼去煮出蝦油;蟹的話,蒸熟拆肉,蟹黃小心留著。我自覺是個幸運兒,暫時沒發現任何食物過敏反應——這算不算是你們倒霉的地方?這也是你們應當疼愛那個只吃白年糕的小女兒的理由。
我有沒有偷吃那難吃的白年糕呢?當然有,否則我怎會曉得,它極之難吃。吃了人魚肉一般的白年糕,大難不死。惡毒不可以說出口;蝦蟹買兩個人的份就好,不要帶不想見到的人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