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書來也書去】一百一十箱書魂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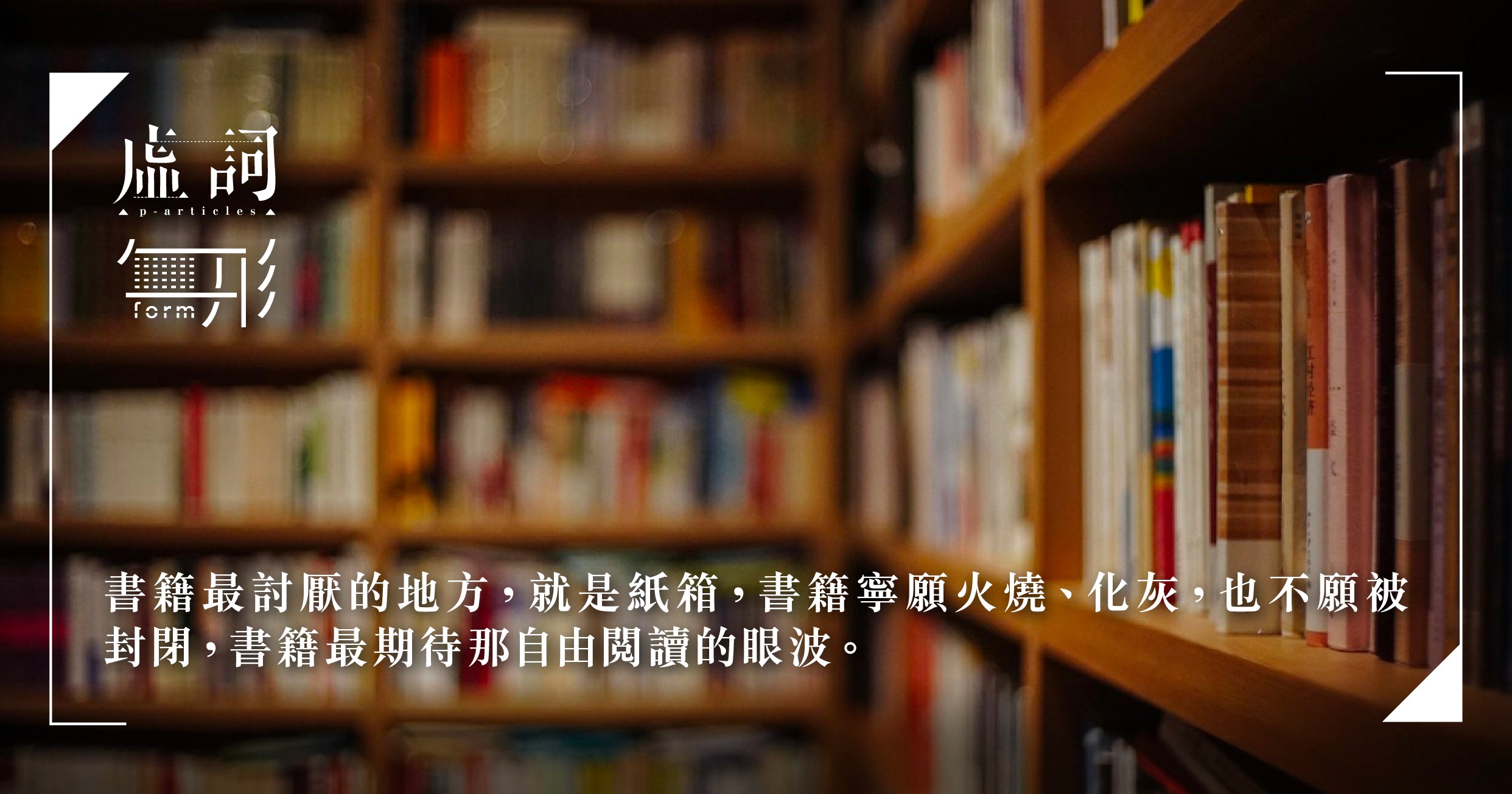
293426992_3219869088268506_8503100170303332015_n.jpg
「閱讀及其儀式成了反抗行動」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著、黃芳田譯《深夜裡的圖書館》
一
在二〇二二年五月臺北文學季「迷宮取代迷宮──寫一本時代的小說」活動中,主持人放映一段由臺北文學季特邀團隊在北京拍攝的陳冠中紀錄片,影片一開始,陳冠中就回憶他在香港的文藝啟蒙經驗,那是一九七一年,他入讀香港大學的第一年,有一天走到九龍尖沙咀一家樓上書店,赫見店內全都是台灣書刊,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白先勇的小說,以及由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作品,陳冠中接而提出,自己中文文學的根是台灣小說。
陳冠中五十年後仍念念不忘的書店,正是早年從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的香港僑生王敬羲,六十年代回港所創辦的文藝書屋,可說是香港第一代引進台灣書刊的獨立書店,尤其重要的,是遭當時戒嚴時期臺灣政府查禁的李敖、殷海光、柏楊、陳映真等等作家的書或曾刊載其作品的文化刊物諸如《文星》、《文學季刊》,都可以在那位於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找到。王敬羲與文藝書屋為讀者引進了不一樣的台灣文化想像:抵抗禁制,延續文化,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帶來瓊瑤、青山、姚蘇蓉以外的具抗衡性的台灣文化,破卻一般人對台灣的刻板印象。
七十年代中期,陳冠中與友人創辦一山書屋、《號外》,進一步延續香港文化中容納異見、發揚前衛思潮的特色。不只王敬羲和陳冠中,在七十年代以至八、九十年代,我們有傳達、青文、南山、五車、田園、新亞、樂文等等自由售賣中港台文史哲社科書刊的獨立書店,也有《文化新潮》、《突破》、《八方》、《越界》等等多元開放的文化思潮雜誌,它們以近乎無限的、自由飛翔的書頁,默默超越一般人以至官方對這島的有限想像:香港不只是金融經濟發達之都,更具多元開放的文化靈魂。
但這靈魂現在怎麼了?據二〇二二年六月六日《明報》報導,香港有中學因應教育局頒令的《國安法:學校具體措施》所指,「校園內的書本(包括圖書館藏書)、刊物和單張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於是把多種圖書從圖書館下架,有一家中學圖書館下架了一百七十三本書,當中包括陳冠中的小說《是荒誕又如何》和《裸命》。
圖書館下架了一百七十三本書,意味學生再不能從圖書館借閱那些書,它們曾經存於學生的借閱經驗裡,如今那些書的存在被取消了,好像從不曾存在世上,然而,圖書館是什麼地方?如鄭振鐸筆下的中國古代藏書樓,如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筆下的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如波赫士筆下的永無止盡六角形巴別塔圖書館,應是盛載想像、抵抗遺忘之所在,是一切純美、思辯、幽獨之靈寄存之所在。人類文明史上,總是暴君焚書,而惜書人苦苦護書;亂世時,惜書人捨身竭力把被禁之書藏於壁中、地窖,盛世時,惜書人斥資興建藏書樓,告誡子孫務必珍惜書本。然而當今香港的圖書館要把圖書「下架」,猶似托兒所把兒童驅趕、避難所將難民放逐,可以想像,一個一個專業的圖書館員基於命令、出於焦懼,也許歷遍連番爭論、掙扎,徹夜把本應珍惜的、已按其「杜威十進分類法」或「中文圖書分類法」一一安放好的圖書「下架」,當中的蝕骨之痛。
的確是「是荒誕又如何」,我們在七、八十年代成長的、曾受益於多元開放及自由前衛的香港文化傳統的一代,實在無法想像香港會有圖書館自殘自棄的這一天。在這樣的日子,在這裡,我想由自己的圖書館回憶開始,記下我對圖書館與書的感念,以至我家裡圖書的聚散、播遷。
二
旋轉式的鐵製書目架,吱吱聲轉動,同學們爭著抄錄書名和索書號在紙條上,遞給圖書館員老師,一位老哥,一位叔叔,一人叮囑同學要守秩序,另一人轉身從神秘的角落找出了書。那時候小學的圖書館大多是「閉架」的,我們只憑書目架上的書名,想像書的內容,判斷是否值得一借。同學喜歡《十萬個為什麼》系列叢書,我也讀過,但更喜歡小學生叢書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小學生叢書」,陸續借閱了《世界寓言選》、《大人國》、《中國民間誌異》等書。二十年後,一九九六年間,我在灣仔軒尼詩道的三益書店見到三十多冊原版的「小學生叢書」捆在一起,即使索價不菲,仍毫不猶豫的買下了,那是我童年自發尋求啟蒙閱讀的源頭之一,是無價的。
「閉架」的圖書館畢竟有局限,在我小一之年,哥哥帶著我從彌敦道的一端跨越馬路到彌敦道另一端,沿公眾四方街(今名「眾坊街」),穿越榕樹頭公園,到達油麻地停車場大廈,從大廈入口陰暗盡處轉入右側的門,就是油麻地公共圖書館,經過大門入口的借還處轉左,是我們視為樂園一般的兒童圖書部,不單因為開放式書架可自由取閱而且冷氣充足,更重要是偌大空間幾乎從來不見有大人,沒有任何人「看管」小朋友,而小朋友處此開放自由之境,好像自然而然地自律,明白圖書館應有的安靜與秩序。開放式書架分類井然,我在「自然科學」、「史地遊記」、「美術遊藝」等區段流連良久,挑出合意之書,可在四十五度傾斜的閱讀桌上翻看,也可用借書證借返家中。
我開始知道,書不是單一的,書是一種積木般的組合,書也不是無聲的,它呼應知識和情感,呼應自由與開放之靈,像荼蘼與雲雀,它在我心裡默唸時,形成了獨立的書面說話聲,永遠附在我身,文字隨著血液,遊走逐漸成長的驅體。
三
我在《地文誌》的〈旗幟的倒影〉一文提及:「屬於我自己的第一套藏書,是父親從台灣買回來的八大冊《世界偉人傳記》,內文每字右側都有我不明白的『國語注音符號』」,記得這套書曾與幾本漫畫一起放置在睡床前的小書架上,因著後來一再搬遷,早已遺失不見,真正留下的藏書,是中一開始流連旺角奶路臣街一帶書店買回來的書,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選叢書」,有五四至三四十年代的作家選本《何其芳選集》、《端木蕻良選集》,有從上海來港的作家《徐訏選集》,也有香港土生土長作家《舒巷城選集》,陸續我再買到高原出版社的李素《讀詩狂想錄》、徐速《第一片落葉》,再發現出版了一兩年的素葉出版社「文學叢書」:也斯《剪紙》、何福仁《再生樹》、西西《春望》,以上這些,不論是香港文學研究社、高原出版社或素葉出版社的書,每本頁數都不厚,我記得大部份是在奶路臣街的貽善堂書店,或西洋菜街的田園書屋,或麥花臣球場對面的五車書屋,以定價十二至十六元再八折買回家的,我覺得自己開始收集了一些名字、一些觀念、一些抒情,大部份來自另一個年代,卻都與我想像的世界、遊蕩的街道相連。
四
積聚有時,散落有時,從中學、大學、研究所的學習階段,至沙田、屯門、大埔的不同工作空間,住處搬遷了多次,隨身的書籍,不免因空間和思想的變化而有所取捨,最終或始終相隨我身的,在沙堆中閃閃生光,在情感的脈絡中絲絲牽掛,時代起風,人面遠去,言語化成了書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我從大埔搬返父母三十年前購置的窩打老道寓所,多年來我在這寓所幾番遷出遷入,最後只有我一人了,書籍和我實在搬得太累,什麼時候可以真正安定,不需再搬呢?號角響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底的某天,我決定要再搬,搬得更遠,遠得連地址都沒有。二〇二一年六月,我從一箱一箱、一疊一疊凌亂不堪的舊文件堆中,日以繼夜地尋回了三十年前在台灣留學時的重要文件,開始辦理移居台灣的手續,經過幾番文件往來傳送,八月底完成手續,我隨即向學校呈遞辭職信,待「通知離職期」一滿之稍後時間,即二〇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式離任,結束十二年有半的大學教職。
緊接的第一問題是,如何處理數十年積存的藏書?我無法亦無意數算冊數,它們比我的狂喜與幻滅都要巨大,書籍在日間呼應蟬鳴,夜間放映幻燈,我向書籍說話,凝視撇捺有情的書頁,到這半生的中途五十之年,我身邊僅餘的就是書本,這兩冊上海亞東版《獨秀文存》購自西洋菜街尾的實用書店,這十數冊五十年代出版的《文壇》來自結業前的波文書店,這一本《雷聲與蟬鳴》有我老師也斯先生的簽名,這一冊《失去的金鈴子》有聶老師予我「華苓,愛荷華,二〇一二年秋」的題字,這一冊用「民間美術」製作的土織藍染布書套包好的《三魚集》,有我在台灣留學時的淚痕,這一冊一九五八年版扉頁蓋有「教育部敬贈」印章的《臺灣文化論集》是我父留下的藏書。時代幻變,人面縹緲,一切都失去了,我生命最後僅餘的就是書:
書魂無紙無字而有記憶呼叫
書籍無人閱讀只好自嘲一番
現實的書無表情但書魂會笑
笑那禁絕書本的下架人間
五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我向電腦屏幕中的大部份沒有臉孔的學生,低聲說再見,是真正的再見,真正的最後一課,上完了,我開始執拾家中的藏書、雜物和學校研究室的書本、資料、文件,準備放入紙箱。我把堆到高處的書放回地面,過程中不只一次,一整列書失去重心跌墜我身上,書籍知道我要對它們作出的事,書籍最討厭的地方,就是紙箱,書籍寧願火燒、化灰,也不願被封閉,書籍最期待那自由閱讀的眼波。
一整天,我滿面是灰,有時陷入回憶,但餘下日子無多,我收拾心緒,強行關閉一幕一幕記憶的畫面,終於整理成一百一十箱書。時候差不多到了,我在物流公司貨運單的「地址」一項,仍只能填上「台北市」三個字,因為沒辦法,我無從作出確切安排,只訂了十四天防疫旅館,之後須抵台後再尋覓租賃居所。時候到了,一百一十箱書要先行,二〇二二年二月九日,搬運工人花一個上午搬走我積聚數十年的藏書,移到一個倉庫,待我告知確切的台灣地址始付海運。
曾經,我每隔數小時或一兩天作一番自言自語,現在,自言自語在無書的空屋中發出幢幢回音,真正成為對話。沒事的,我知道真正先行的是我,一百一十箱書待命顛渡,像無聲的戰友相隨。二月十一日,與空屋對話了兩天,真正出發了,一百一十箱書等著與我重逢。時代停滯,時代又再流動,書亦如我,走上一條流動的路,之後會否再移動,說實在,真的不知道,完全無法確定、茫無頭緒的,但有書魂相隨,我就是我自己的圖書館,現實的書、存放世間的書終必盡散,唯一百一十箱書魂不散,洗滌笑痕塵土,依約酒醒浩歌,生命或將再度流動,我竭力保存的書魂也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