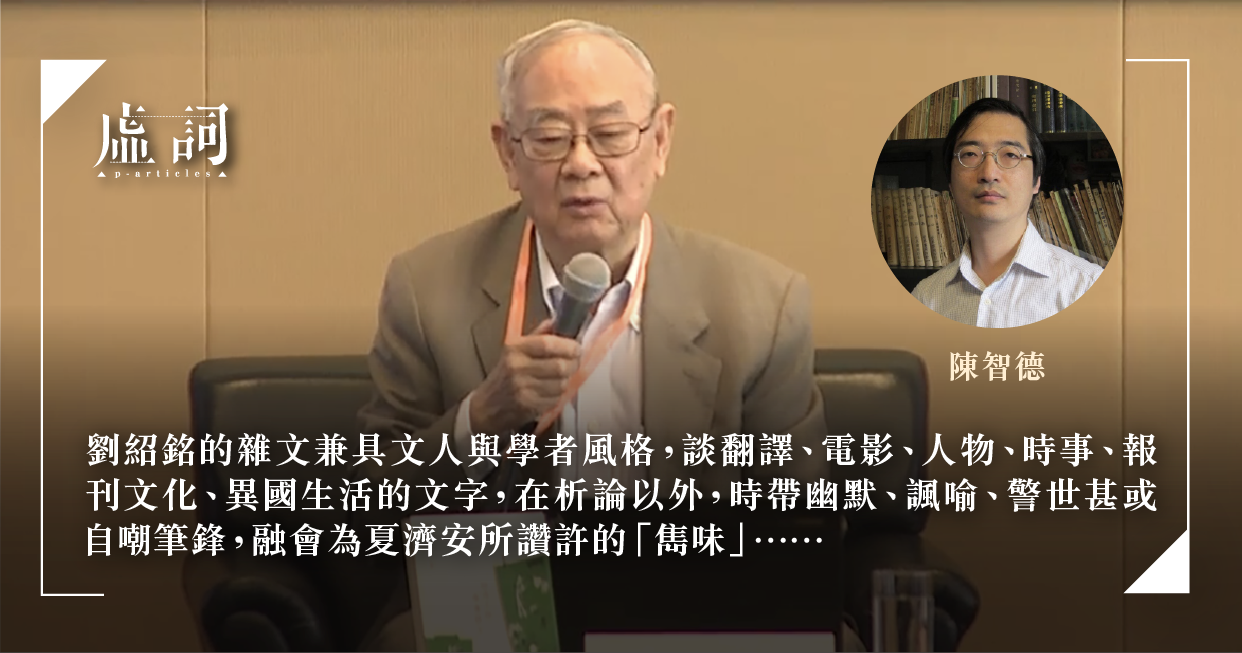【悼劉紹銘】從《靈台書簡》到《二殘遊記》──劉紹銘的文藝歷程
雜文是劉紹銘文藝生命的最核心,一九五〇年代末就讀台大外文系時,他的雜文已獲夏濟安賞識,在其主編的《文學雜誌》,先後發表〈不堪集〉(1957年11月第3卷第3期)、〈坑中人語〉(1958年1月第3卷第5期)、〈影壇走筆〉(1958年4月第4卷第2期)、〈影壇縱橫談〉(1959年8月第6卷第6期)和〈引頸集〉(1960年5月第8卷第3期)等等好幾篇有關小說和電影的雜文,以本名劉紹銘或「紹銘」發表。《文學雜誌》是當其時台灣相當重要的文學刊物,論述與創作並重,作者有著名的梁實秋、覃子豪、思果,年輕一輩的有余光中、林文月、王文興,而劉紹銘在《文學雜誌》發表的幾篇都是雜文,可見夏濟安對其文筆的看重。
前此,劉紹銘的文藝歷程,實始於一九五〇年代初的香港,在他少年失學、到社會謀生不久,就投稿到《中聲晚報》、《新生晚報》和《香港時報》,作品有雜文也有小說,據劉紹銘在記述留美生涯的自傳體文集《吃馬鈴薯的日子》所述,他到台後,自費出版了一冊在香港時所發表的雜文和小說,並送了一本給夏濟安求獲指正,後來夏濟安找他談話,說他的小說寫得不好,「但雜文卻寫得頗有『雋味』,因此邀我替『文學雜誌』寫些隨筆之類的東西」,可見雜文寫作的成績,是劉紹銘獲夏濟安賞識並得以在《文學雜誌》發表的關鍵。
劉紹銘的雜文兼具文人與學者風格,談翻譯、電影、人物、時事、報刊文化、異國生活的文字,在析論以外,時帶幽默、諷喻、警世甚或自嘲筆鋒,融會為夏濟安所讚許的「雋味」,其雜文或可說揉合了錢鍾書、魯迅和梁實秋的風格。
六七十年代,劉紹銘在台、港兩地的報刊,包括台灣的《文星》、《中國時報》、香港的《大學生活》、《明報月刊》、《純文學》(港版)、《南北極》等刊物發表雜文,其後結集的《靈台書簡》、《二殘雜記》、《傳香火》可說是這雜文寫作階段的總結,其中《靈台書簡》是以書信體寫成的雜文結集,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寫的一輯名為「馬料水書簡」,在新加坡大學任教時寫的一輯名為「牛車水書簡」和「靈台書簡」,另有名為「雜文」和「前言無後語」的兩輯,一篇一篇談及作家與書評的文章中,在談文說藝的基調以外,掩藏在書信體文字筆鋒的背後,更表達了作者對學院生活和學院文化的洞察體會。
劉紹銘把當中對學院的諸般洞察體會進一步發揮,演化成一九七四年起在《中國時報》以「二殘」為筆名發表的現代章回體諷喻小說《二殘遊記》,承續雜文時期的幽默筆鋒,而更深刻地發揮諷喻和警世宗旨。劉紹銘對此作品投入很多心力,也許當中亦融鑄了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所論的感時憂國精神,自一九七六年初次結集出版的四季版《二殘遊記》,到一九七七年的洪範版《二殘遊記第二集》,後者乃接續前集的回數,從第八回起收錄至第十四回,其中,據劉紹銘在該書後記之說明,第九回內容完全出自楊牧的手筆,是楊牧以「殘三」為筆名,同樣在《中國時報》連載的,收錄第九回在該結集中是得到楊牧的授意。
差不多十年後,劉紹銘再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二殘遊記》並以「新篇」述名之,一九七七年一月結集為時報文化版的《二殘遊記新篇》,同年九月再出版《二殘遊記完結篇》,二書完整收錄新一輯「二殘遊記」全文共二十回。從一九七〇年代的《二殘遊記》,到八〇年代的《二殘遊記新篇》,劉紹銘從美國學人的人物故事角度針砭時事,亦刻劃時代,在新篇的前記,指出取「二殘」之名,一方面是借鏡於清代劉鶚的《老殘遊記》,另方面是有感一九八〇年代文革後的時代,「神州大地,看來說不盡殘山剩水的淒涼況味」,因以「二殘」之名,著「二殘遊記」。這四本合共三十四回的《二殘遊記》系列小說,可說是劉紹銘以晚清諷喻小說的體式,結合他本人的雜文風格,以幽默筆鋒,寄託諷喻和警世宗旨,抒寫感時憂國情懷,無疑成就了劉紹銘小說創作生涯的高峰。

劉教授的雜文集《靈臺書簡》(台北三民書局1972年初版)
以上探尋一段劉紹銘文藝創作生命的歷程,希望從史料和作品角度,敘說出劉紹銘在文學史上不應被忽略的位置。此外,我想再憶述一段本人在嶺南大學就讀研究生課程期間,劉教授予我的啟發和幫助。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我在《信報》「文化版」讀到劉教授所撰文章〈能不憶香江〉,寫及五〇年代他與詩人楊際光的交往。我對該文印象特別深刻,是因為楊際光是我所心儀的詩人,不但如此,楊際光可說是一位久被文壇遺忘的詩人,而我當時跟隨梁秉鈞教授研究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新詩,第一年經常到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搜集資料、查看舊報刊,除了楊際光的詩集《雨天集》,我首次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時報》和《海瀾》等報刊,讀到多篇前此未見的作品,所以,當我讀到劉教授憶述與楊際光交往的文章,心情難掩激動,暑假結束後的九月第一個上課日,即我碩士生涯的第二年之始,當時知道時任文學院院長的劉教授之辦公室,與中文系位處同一座大樓,當天我就從三樓的中文系,沿樓梯走到二樓,找到文學院辦公室去叩門,向秘書表示想見劉教授,請問他是否有空。
現在回想當時自己是太過唐突冒昧,實在大學行政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我不應如此倉促打擾,所幸劉教授不介懷,他先著秘書問我來訪何事,我說自己是中文系研究生,有學術問題想向他請教,劉教授知道就同意讓我進門。我坐下後立即取出刊載劉教授文章〈能不憶香江〉的《信報》「文化版」剪報,說明自己正在研究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新詩,其中包括楊際光的作品,我請劉教授可否再多談一些他所知的楊際光故事,劉教授就為我補充一些文章未談到的部份,最後,他取出一張辦公室常用的備忘標紙,抄上楊際光的美國地址給我。
一九九九年暑假,我完成碩士論文,二〇〇〇年三月,嶺大中文系舉辦「現代漢詩研討會」,我以〈楊際光初論〉這修訂自碩士論文一章的題目參加,其後發表在《作家》第七期。二〇〇一年九月,我獲取錄入讀嶺大中文系首屆開辦的博士班,九月的某一天,劉教授透過秘書約見我,囑我到他辦公室,如是我就得以第二次踏足他的辦公室,記憶中不是文學院裡面,而是另一處劉教授本人的辦公室,他表示讀過我的楊際光論文,並予我一番鼓勵,此次見我,主要是把手上的楊際光研究資料移轉給我,包括多份署有「紹銘弟存念」、下款是楊際光親筆簽名的《南洋商報》文章影本,以至多份同樣具上下款、楊際光親筆簽名的手稿影本,全部放在一個A4文件夾內,劉教授說他用不著這批資料了,故此全都送給我,囑我繼續研究下去。
我再讀劉教授的〈能不憶香江〉和〈皮匹詩人〉二文,寫他對楊際光的感念之懷,在文字以外,因著對楊際光詩作的研讀,以及劉教授寄予對楊際光研究的囑咐,我明白了〈能不憶香江〉和〈皮匹詩人〉二文的一切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