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像西西這樣的一個女子】與西西從容出入於浮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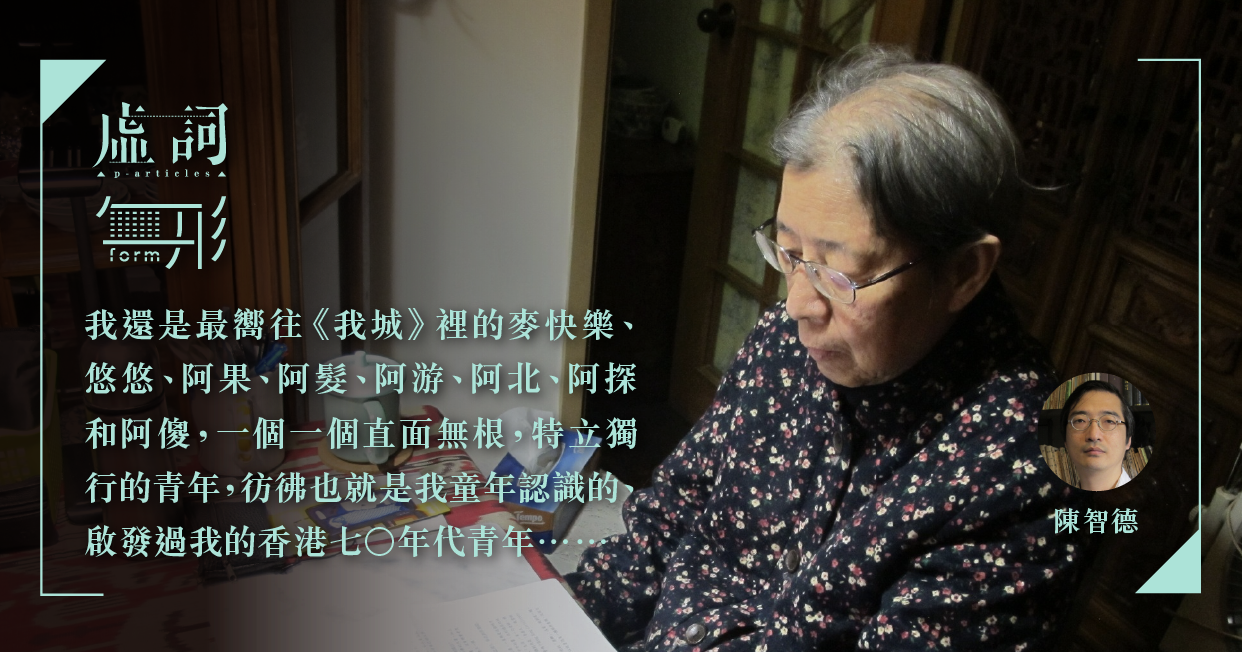
329017182_145911374705413_7641837411360882868_n (1).png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在報攤買到一份《大拇指半月刊》,之後每期都買來讀,讀到十一月號許迪鏘談《大拇指》八週年的短文,我才知道這刊物已辦了八年,由一九七五年的《大拇指週報》演變為我手上的《大拇指半月刊》,我應該早一點買來讀才對啊!當時我剛由小六升上中一,在報攤,在那往返油麻地和旺角的夜路上,很容易就遇到報攤,我買漫畫,也買《突破》、《年青人週報》和《大拇指半月刊》,在跌宕的街燈與枱燈之間,我逐漸記住了西西、也斯、何福仁、許迪鏘、關夢南、葉輝、馬若、鄧阿藍、陳錦昌、飲江、洛楓等等作家的名字。
不久,在旺角的二樓書店,田園、學津、貽善堂,我陸續買到素葉版「文學叢書」中的《我城》、《石磬》、《春望》和《哨鹿》,彷彿一一呼應我在《大拇指半月刊》感受到的文字風格,它們鮮活、求新,生活化,像《石磬》中的〈快餐店〉、〈花墟〉、〈美麗大廈〉,也暗藏一些對世俗的抗衡,像〈可不可以說〉這詩,即使我初讀時只是個中一學生,卻完全理解當中未有說出的反抗性,我最喜歡讀到詩的末段有這樣的句字:「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一隻七省巡按/一匹將軍/一尾皇帝?」在那轉換量詞的輕快節奏中,不明言卻引導著對於主流威權形象的顛覆,讀來使人痛快,因為在我心目中,學校那位訓導主任,實在早已是「一頭訓導主任」了。我也喜歡〈我聽懂了〉這首詩的結束處:「如果千般的愛只有一種/語言/我已經聽懂了,並且/跟從你說過一遍」,這樣深刻卻又制約著情感的語言,真的與我當時在中國語文課本上讀到五四初期新詩近乎濫情的詩句很不同。〈我聽懂了〉這詩的副題是「給我的外文老師S姑娘」,我也很希望有機會向《石磬》這書中、另類老師一般的西西說,我在當時已經讀懂了,並且,願意跟從你說過一遍。
在《大拇指半月刊》,有一次我讀到西西的〈關於「木蘭詩」〉一文,印象深刻因為當時在學校的中國語文課堂上,老師講到〈木蘭辭〉這課文,我正好可以由西西的文章對比學校老師的講解,所得當然很不一樣,特別是西西對〈木蘭辭〉的「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這句,從女性角度提出很不一樣的解讀,我愈發感到,《大拇指半月刊》、素葉版「文學叢書」以及眾多我從書店認識的香港作家名字,將為我帶來從根本上迵異於教科書以至整個教育建制設定了套路的、完全不一樣的文藝生命路徑。
西西這一輩戰後在香港成長一代作家,包括崑南、蔡炎培、也斯、飲江、鍾玲玲、何福仁、關夢南、葉輝、許迪鏘等等許多位,承接南來作家於五六十年代的《人人文學》、《中國學生周報》、《文藝新潮》等刊物播遷至香港的文藝,進而吸收西方現代思潮、呼應本地情懷,創建出《新思潮》、《好望角》、《秋螢》、《四季》、《詩風》、《大拇指》、《素葉文學》等等由香港戰後一代主導的文藝刊物,以其現代而創發性的文化視野,形成一個生成於民間的公共文化空間。西西這一輩作家的特色,是特別講究鮮活而獨立的角度,不滿足於定見,更抗衡建制、潮流和世俗,他們所創造出來的「香港文學」,絕不只是香港一地發表或有關香港一地之文藝,更是一種與香港共同成長的精神、視野和文化態度,他們寫出的亦不只是一篇一篇在香港發表或有關香港的文藝創作,而是一種有別於教育建制和世俗潮流的文化、一種獨立的知識進程。這群香港作家的傳播和影響力,大概無法與教育建制和世俗潮流匹敵,但只要讀者真正有心接觸、理解,必隨著他們進入一道不一樣的香港文化門廊、一種新的文化領域。
七〇年代的西西,自六〇年代的〈異症〉、〈東城故事〉所代表的存在主義式虛無風格中掙脫,創出《我城》、〈玩具〉、〈星期日的早晨〉等等展現鮮活語言新風格的小說,尤其《我城》以出殯和遷居而開展的故事,終結束於電話線的安裝接通,經過對歷史記憶的哀悼和肯定、連串社會現象的呈現和批評,展現出一個一個具鮮活形象的青年,整本《我城》的達觀、向上氣氛,是由七〇年代青年對文化藝術和社會改革的信念建築而成,使第一章有關出殯的「那麼就再見了呵/我說——就再見了呵」,與第十八章亦是全本小說結束處所說的「那麼就再見了呵。再見白日再見,再見草地再見」,兩種「再見」展現很不一樣的意涵,它們之間也不是二元對立,而是有如硬幣之一體兩面,寄望於人際的溝通、文化的覺醒和多元開放,締造出認清了「無」之後始能直面的一座「我城」。
八〇年代,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碗〉、〈感冒〉等小說,寫出香港職業女性面對社會刻板性別觀念上的掙扎,她們自定型的世俗中掙脫出,拒絕接受這世界提供的愛情觀、婚姻觀,哪怕它是一種眾人都認可的潮流:「世界上仍有無數的女子,千方百計地掩飾她們愧失了的貞節和虛長了的年歲,這都是我所鄙視的人物」,西西透過〈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寫出她對世俗和潮流的拒絕,某程度上,是與她自《我城》到〈浮城誌異〉的文化身份省思密切相關的。《我城》裡的阿果,從一次又一次被質疑國籍與身份的過程中,認清了自己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這種七〇年代的文化省思,連繫到八〇年代中期,因中英對方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和《中英聯合聲明》引致的身份迷惘、移民潮等現象,西西以〈浮城誌異〉作回應,小說中的敘事者引用德國作家雷馬克著於一九三九年的小說《流亡曲》扉頁上的一句:「沒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氣的」,寄語總是夢見自己浮在半空的「浮城人」要直面無根、超越無根,再以「明鏡」、「窗子」、「烏草」和「慧童」等章節,寄喻浮城人要直面本身的「異」,並由這「異」的重新審視以至肯定,始能現出對香港未來的新視野、新想像,就好像「時間」一章中,壁爐下駛出火車的超現實境象。由這閱讀的脈絡中,我體會到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碗〉、〈感冒〉等小說對女性自主角度的省思,是與她對香港身份的省思相通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對刻板性別觀念的拒絕,也就是〈浮城誌異〉對無根與「異」的直面。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碗〉、〈感冒〉等小說的女性自主省思以外,西西亦對父性的隱退和消亡具深切描繪,這是西西可能被忽略卻是另一使我驚異的所在,她早於一九六八年的散文〈港島.我愛〉,已從對先父的懷念引申到地方的變遷和認同:「因為有過你的園已經不再有一點痕跡」、「有一間你愛在窗櫥外蹓躂的伊利,它們也逐漸隱去,而一切就升起來,城市建在城市上,臉蓋著臉」,城市急速發展,最終蓋過了西西對父親回憶的連繫,但西西仍肯定對港島的認同,因為該認同始終與懷念父親的感受並存:「我開始穿一雙紅色的鞋,穿過馬路,和一個你坐在電影院裡。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城,你說。是的,是的,我愛港島,讓我好在明天把你一點一點地忘記。」在〈港島.我愛〉這散文裡,人與地是不能分割的,是共同的情懷,父性的隱退、消亡,同時締結出新的地方認同。
在眾多西西小說的故事角色中,我很欣賞〈玫瑰阿娥的白髮時代〉、〈夢見水蛇的白髮阿娥〉和〈照相館〉中的白髮阿娥,那穿越事物真幻的淡然,但仍在世界詭變中揮不去瞻前顧後的複雜情懷,也許某程度上,反映西西在時代轉折裡的思考。著於二〇〇〇年的〈照相館〉,是從一九八〇年代的〈春望〉伊始的「白髮阿娥系列」小說的最後一篇,白髮阿娥在那老舊屋邨邊陲行將結業的照相館裡獨對舊照,在香港那年代的「舊區重建」背景中,小說瀰漫一片舊人事終止和離散的氣氛,在小說的結束處,當阿娥從沖印底片的黑房走出,照相館的大門出現一位女孩洽拍學生照,女孩的叩門聲彷彿一種香港新一代的叩問,然而小說沒有順應一般人的預期,西西可能根本是有意拒絕這預期,阿娥沒有和叩門的女孩發生任何連結,她只是很輕淡地,著女孩另找他店光顧:「小朋友,對不起,我們的師傅回鄉下去了,你到碼頭那邊的照相館去拍照吧」,就此結束了全篇小說,阿娥拒絕女孩的理由是「師傅回鄉下去了」,實際上是店主要移民、照相館要結束、阿娥一家都要搬,小說的重點在於阿娥的生命回憶和淡然態度,結束在對於叩門女孩的拒絕,同時也暗示著對於未來的拒絕。
整個「白髮阿娥系列」小說,結束在拒絕預期一幕,也等於拒絕溫情、繼承、感傷或感動等等的讀者喜好預期,可說是一個十分孤高、又是個十分「西西」的結束。西西畢生拒絕順世、拒絕順應世俗預期的唯一例外,可能是答應陳果紀錄片《我城》的拍攝吧,陳果的《我城》並非不好,只是西西置身各種鏡頭和拍攝程序的安排當中,大概感到愈來愈厭倦吧,西西始終是拒絕順世的,在她最後留下的《我的喬治亞》、《縫熊志》、《欽天監》幾部作品,還以她一種率性自由而難以逾越的文藝高度。
昔日我從報攤每隔兩週按期買回家的《大拇指半月刊》,慶幸仍有幾份保存至今,可說已是「白髮大拇指」了,它們與許多同樣已殘損、褪色的舊書刊一起,竟隨我身飄移,不過仍是那一道拒絕被設定的文藝生命路徑。但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最嚮往《我城》裡的麥快樂、悠悠、阿果、阿髮、阿游、阿北、阿探和阿傻,一個一個直面無根,特立獨行的青年,彷彿也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啟發過我的香港七〇年代青年,忘不了那飛揚的生命情調,他們一定活在那自由鮮活的、以文藝或信仰或一切的理想作護照、從容出入於無邊境、無國籍的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