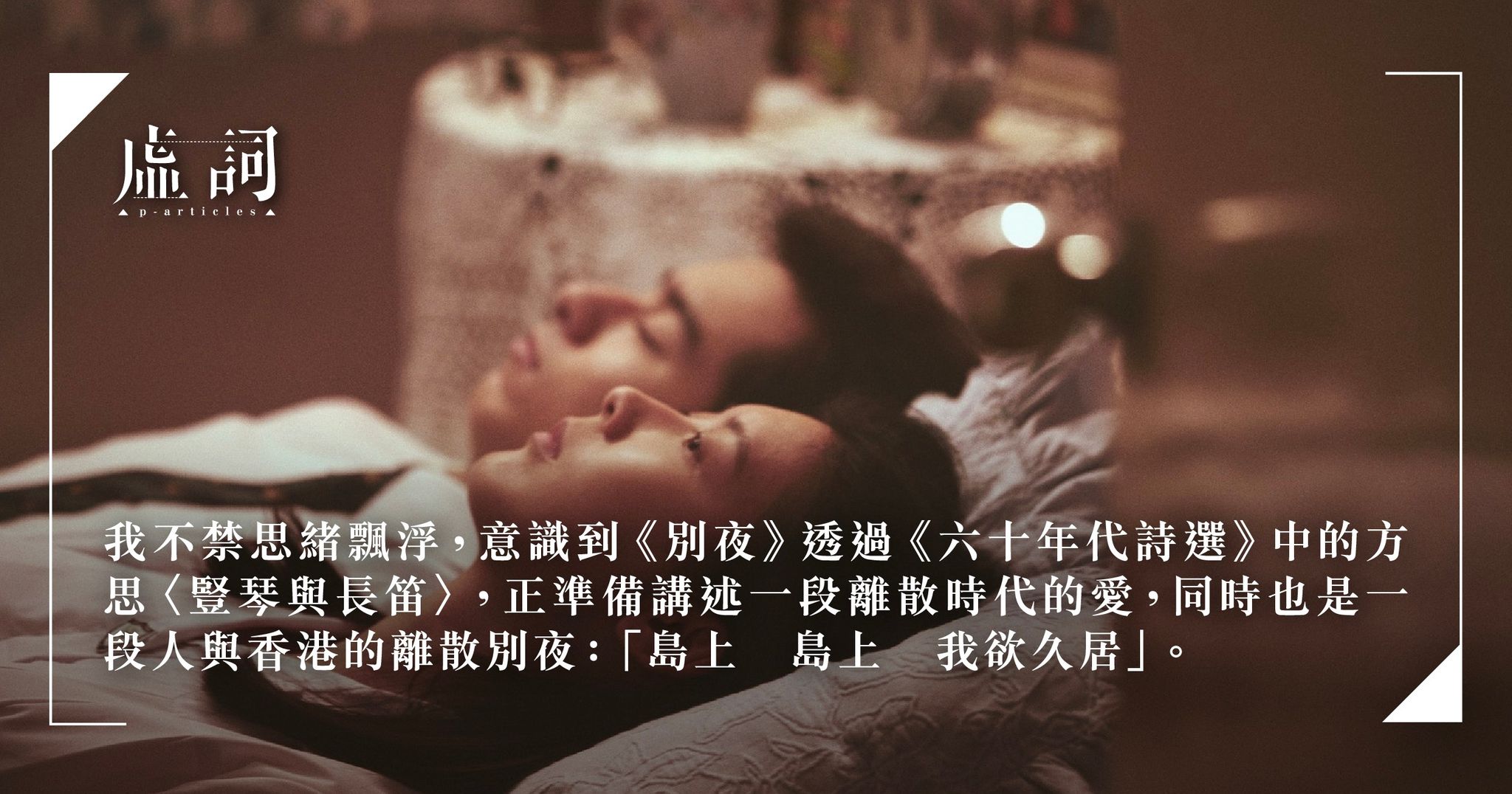離散時代的愛慾流瀉:《七人樂隊.別夜》期許的更生
炎夏的八月初旬午後在台北看電影《七人樂隊》,由徐克、許鞍華等等七位導演各自以菲林拍攝一段獨立短片,對應不同時代的故事,當中第四段短片,以八〇年代為背景的,譚家明的《別夜》,敘述一對青年情侶在女方移民前夕的情感掙扎,當那少女,余雁飛拿著一本《六十年代詩選》,以粵音讀出「島上 島上 我欲久居」這詩句,我馬上知道,來自該書收錄的方思的長詩〈豎琴與長笛〉。
約兩個月前,我才剛參加了一場由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的「臺灣新詩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前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這已經煙消雲散的身份,作為滿足大會記認所需的職銜,發表論文〈《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與五六〇年代臺港現代詩〉。
所以,在台北市中山區的一家影院,看到《七人樂隊》之《別夜》,少女翻開《六十年代詩選》朗讀的一幕,我不禁思緒飄浮,意識到《別夜》透過《六十年代詩選》中的方思〈豎琴與長笛〉,正準備講述一段離散時代的愛,同時也是一段人與香港的離散別夜:「島上 島上 我欲久居」。
《六十年代詩選》這書在余雁飛手中,不只是一本有字的道具,導演透過鏡頭安排,讓觀眾一再很明顯地看清楚余雁飛手上的,是一本名為《六十年代詩選》的書。許多時,文藝類型影片,特別是以愛情為核心故事的電影,片中如果出現書籍,往往作為道具一般的故事場景過渡,然而譚家明的《別夜》當中,《六十年代詩選》這書不是道具,而是整個故事的前景:一段離散時代的詩情流瀉,譚家明以之反照八〇年代,以至詩歌中的年代,與觀眾當下的二千二〇年代。
《六十年代詩選》由張默、瘂弦主編,洛夫撰序,一九六一年由台北大業書店出版,書名「六十年代」並非當今普遍理解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即「一九六○年代」(Sixties/ 1960s)之意,而是使用舊式算法,以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年稱為「六十年代」,推演之道猶如唐樓的二樓等於洋樓的一樓(1/F),或一九〇一年至二〇〇〇年被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詩選》既是一九六一年出版,內容主要收錄1950年代中至後期的台灣詩人,包括方思、林泠、瘂弦、洛夫、商禽等人的詩作,也收錄了香港詩人馬朗、葉維廉和崑南的作品;此外,洛夫在序文中,提出這詩選在紀年範圍以外的意義:「所謂『六十年代』,並非完全意味著一種紀年式的時間觀念,而是表示一種新的、革命的、超傳統的現代意義(註1)」。
所以,《六十年代詩選》這書不只是一般的年代佳作選集,更有那時代的「新的、革命的、超傳統的現代意義」的展示意味,而特別需要注意的,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是一個禁忌處處的「白色恐怖」時代,直至一九六〇年代以至較後時期,仍有「《自由中國》事件」、《聯合報》副刊的「船長事件」、「《文星》事件」等等,高壓政治撒下無所逃遁的文網,正如瘂弦所指:「那時候的詩人不能把話說得太明白,才把真正想說的話隱藏在意象的枝葉背後。像商禽的『逢單日的夜歌』、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社會的現實性很強,但是能不能像今天這樣用明朗的語言把它寫出來?不能。必須用象徵的手法,把自己對社會的抗議、人生的批判帶出來(註2)」,所以洛夫等人透過編選《六十年代詩選》,不只收錄佳作,洛夫文字上所指的「新的、革命的、超傳統的現代意義」,實在是尋求一種超越的政治、衝破文網的純美,以之期諸時代語言的更生,而語言一旦更生,亦即是實現對白色恐怖和主流政治語言的抗衡。
譚家明的《別夜》,在八〇年代香港的移民潮背景下,年輕情侶處身在大人世界做成的政治狂濤中,無法不各自分離,前景充滿未知和變動,少女在離港前夕邀約少年戀人到家中,二人在情侶一向常見的誤解和吵鬧以外,更由於移民處境及理念分歧而呈現難解的糾結,也許為了緩解衝突,同時想到日後二人再難會面,少女嘗試主動試探,深情地與戀人歡好,在那情慾流動的分秒中,二人卻因潛藏著長久的壓抑而未能真正舒張出愛,大廳忽然響起電話,少年提出暫停,少女只好起身,聽罷打錯的一通電話,少年發現房間有一本中文詩集、一本英文詩集,少女接過中文詩集,張默、瘂弦主編的《六十年代詩選》,翻開朗讀,是台灣詩人方思的長詩〈豎琴與長笛〉中的一段:
「我發現我在一座島上,以迴響為範圍
我欲久居
來罷,來罷,來到我身旁,依山偎海
——來,我來到你身旁,你是山,你是海……
依偎著你,我知道這不是夢,這是現在」(註3)
少年也揭開英文詩集,是艾略特(T. S. Eliot)的COLLECTED POEMS 1909-1935,朗讀了一段,這時二人的情感重新流動,彷彿是詩歌化去潛藏的政治狂濤的壓抑,又或許方思〈豎琴與長笛〉中反覆穿梭的「島」的意象,在這影片中化作另一種島嶼繾綣的關連,香港這島與半島的山海情懷、都市氣象,往復呼喚這對年輕情侶:如果這份相知確有情義便何妨繾綣,哪怕入夢才許再履舊約,二人再度依偎,終於實現了初次愛慾的流動,過程中,二人以一句中文詩一句英文詩交替朗讀,男女詩情讀韻化作星夜荒野下一雙交纏的樹,在這近乎超現實的一幕,方思〈豎琴與長笛〉中的詩句再次浮現出「島」的意象,更圍繞著年輕情侶的愛慾,詩與情周流不息,終於突破了時代的重重捆鎖:
「精神如何顯出形象
我想知道
我不要畫圖,我隨波浪浮去
我依偎著你,默默對著影子
來罷,你是山,你是海……
聲音像落葉,安卧在林間空地
……
島上
島上
我欲久居。
愛情自午寐醒來:今夜是一個動人的夜」(註4)
即使之後二人仍將分離,在那一刻,二人透過語言的更生,達致內在的真正更生,超越了現實世界極力的封鎖,成就出一種衝破文網時代的美。
方思〈豎琴與長笛〉一詩除了收錄於《六十年代詩選》,也見於台北洪範書店版的《方思詩集》,一般具資歷的文藝讀者或許都翻過這書,但譚家明拍攝時選用更為冷僻罕見的《六十年代詩選》,特別放置在一段以八〇年代為背景的故事處境中,相信是有意以之呼應他本人曾經歷的時代,亦即譚家明年輕時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哭泣!夜之城市〉、〈BONJOUR〉、〈風曜日〉等具前衛詩風作品的六〇年代,而在《六十年代詩選》當中,洛夫所標示的紀年範圍以外的意義:「一種新的、革命的、超傳統的現代意義」,也許同樣具有向當今這二十一世紀二〇年代喊話之意。
由此再看《別夜》所拍攝的一段離散時代的愛慾流瀉,既是同屬一段人與香港的離散別夜,也是以一段詩情的更生,尋求並期許著「一種新的、革命的、超傳統的」對政治狂濤的更生:「島上 島上 我欲久居」,處身離散時代的敏感目光,猶如菲林般的鏡頭,劃過一段一段莫能停息的香港別夜,詩情流瀉、愛慾如傾,救護車響號急行,迷霧遮蔽了路,這世界要取消我們,我們可以不取消自己嗎?
註:
1. 張默、瘂弦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頁VI。
2. 瘂弦〈現代詩之省思〉,《中國新詩研究》(台北:洪範書店,1987),頁29。
3. 張默、瘂弦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頁15。
4. 張默、瘂弦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