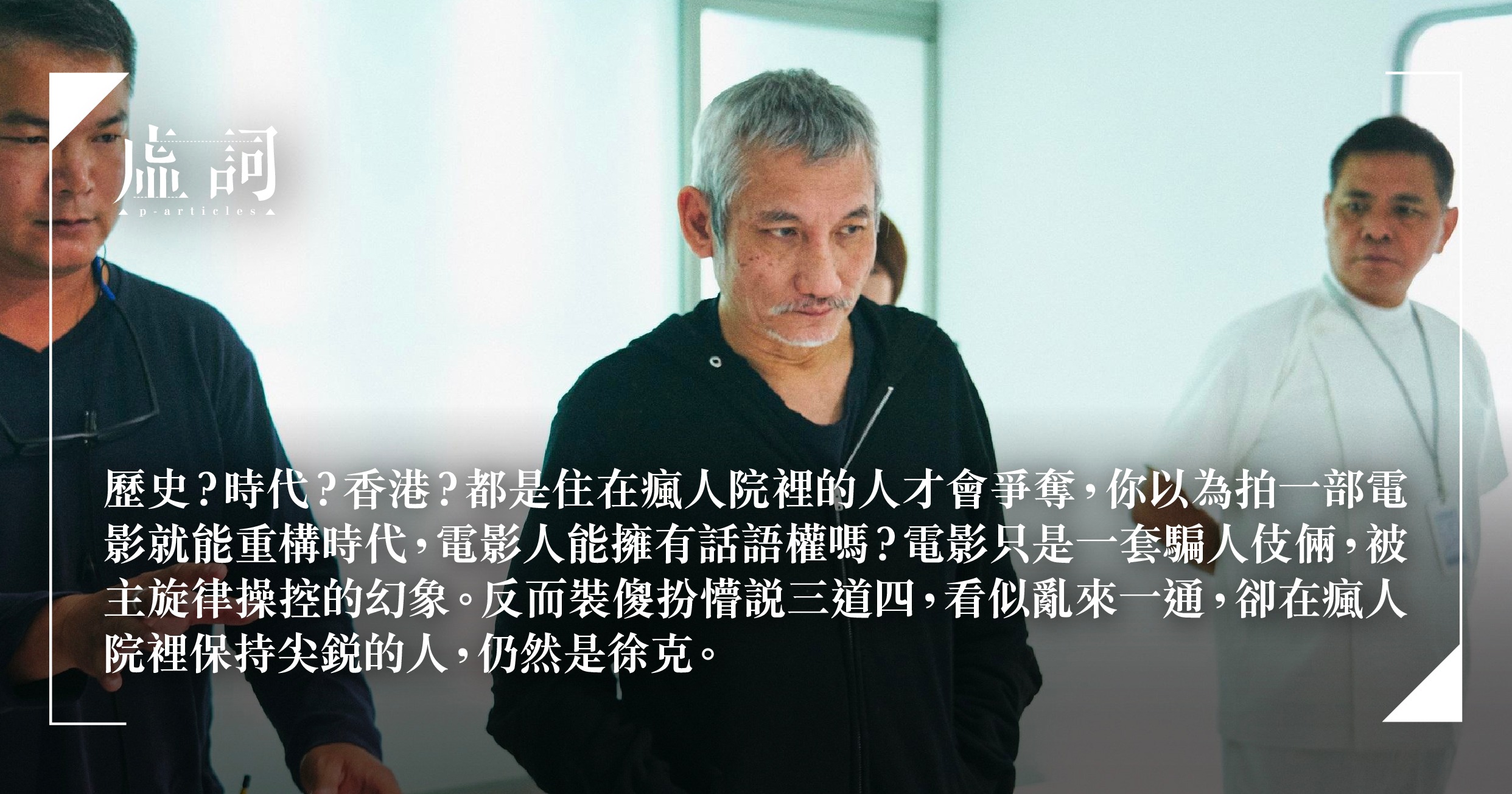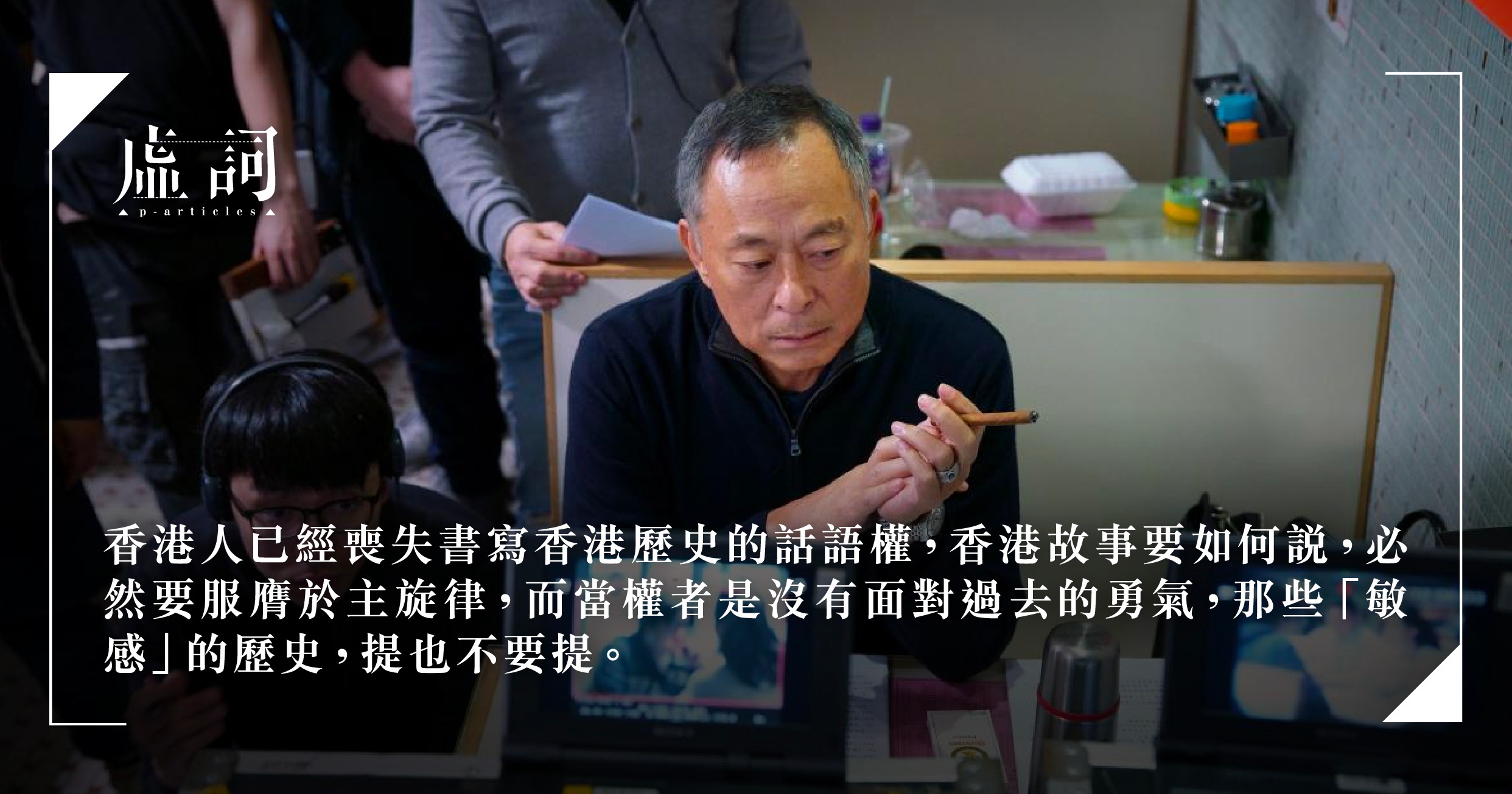【一眼關七】《七人樂隊》:奏不出的未來
影評 | by 葉七城 | 2022-08-10
建制派有很多支持者愛攪慶祝活動,普天同慶。回歸25年是件大事,尤其是經歷落實國安法,香港「由亂而治」的重要里程。建制派中不乏「叻唔切」的人,不少活動都加上「1997-2022」標示,驟眼看去以為香港已死,享壽25載。
大吉利是。這令我想起1997年主權回歸,旺角女人街的小販攤檔都在賣慶回歸的紀念T恤,款式繁多,不乏殖民地(現在要改口:殖民管治下的香港)色彩的icon,如紅色帆船、有英女皇頭像的鈔票,也有香港新的區旗區徽及青馬大橋新建設⋯⋯在衣服當眼處不約而同印有一個期限:1841-1997。這是「香港」作為英殖時代意義上的死亡。
1841年是香港「開埠」之年,1月26日英軍在上環水坑口慶祝,香港從此不一樣。2022年在很多人心中是香港另一次意義上的死亡,感到興奮的人會慶祝,失望的人選擇離開,出現移民潮。
述說香港故事,離不開「移民」這因素。導演杜琪峯在香港還相對風平浪靜的時候,牽頭拍攝一部抒發「香港情懷」,由香港導演講香港故事的電影,起初召集了8位導演(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吳宇森、袁和平、杜琪峯、林嶺東及徐克),從上世紀50年代,每10年為一分段,直到「未來」,電影名為《八部半》,以菲林拍攝,同時致敬電影這個媒介,後來導演吳宇森因為健康理由退出,他負責那段70年代留空了,電影變陣,成為現在的《七人樂隊》。
電影開拍至完成,林嶺東離世,杜琪峯也預料不到香港在2019年後的巨大變化,《七人樂隊》相信也絕非拍來慶祝(或悼念)「1997-2022」。
《七人樂隊》的七個故事中,有些富個人色彩,如洪金寶《練功》及許鞍華《校長》,同是懷念師徒/師生關係;另外有三段和「移民」有關:譚家明《別夜》講女生舉家移民在即,與男友的不捨之情;袁和平《回歸》中的爺爺面對兒子一家移民而選擇留港;林嶺東《迷路》講中年移民的香港人回歸。
導演們都很聰明,他們講移民的故事時,會避開談移民的原因。80年代的移民潮是因為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1997.7.1」成了一個限期,「1989.6.4」在北京發生的事又加速一些香港人離開的決心,90年代臨近回歸又走了一批人,這都是對未來缺乏信心。《七人樂隊》的取態很穩陣,確保可以通過內地的電檢(因為電影預定了在內地公映)。
2019年後,國安法重新界定了自由,包括收緊電檢尺度,香港人拍電影和看電影,再也不像過去那麼輕鬆,香港故事更難說下去,當權者也不容許在電影裡提及和回顧某些歷史,像曾經通過電檢的紀錄片《理大圍城》也突然被限制上映。
《七人樂隊》意外地誕生在一個「由亂而治」的年代,為「香港故事」劃了一條分界線,往後的香港故事要如何拍攝,需要由誰來批准——恐怕不能暢所欲言。曾經拍過關於佔中紀錄片《亂世備忘》的導演陳梓桓,新作《憂鬱之島》試圖更宏觀地整理香港歷史,當然,2019年社會運動是觸發點,令陳梓桓回首香港自「開埠」以來的變化,電影以大型社會運動為主軸,加入重現歷史的戲劇片段,但扮演者的身份有另一重意義:他們不少都因為參與反修例示威而被檢控,《憂》虛實交錯,以當下對照歷史。
紅眼形容《七人樂隊》是「過期的香港味道」,但它很安全,遠距離地懷緬過去,只有徐克的未來篇章《深度對話》不跟大隊,在玩諷刺(杜琪峯《遍地黃金》也有點警世意味)。
其實,由前輩級導演來講香港故事,難免老氣橫秋。把這個合作計劃看成導演們的輕鬆聚舊,也有它的趣味,重要的是可一不可再,香港人已經喪失書寫香港歷史的話語權,香港故事要如何說,必然要服膺於主旋律,而當權者是沒有面對過去的勇氣,那些「敏感」的歷史,提也不要提。像《憂鬱之島》面對香港抗爭歷史的電影必然成為「禁片」。(當然我們可以說,《憂》根本沒有送檢,何來被禁。)
但「香港故事」真的很吸引,至少提起口號式的「獅子山精神」仍然有人感動和振奮。乘著慶回歸25年推出的電影《一樣的天空》便是主旋律下的「四人樂隊」。由莊澄監製,四位新晉導演陳翊恆、潘梓然、侯楚峰、葉正恆執導,故事以大學生范成信(朱鑑然飾)由1997年這25年間認識不同朋友的故事貫穿,片首便道出香港這段時期「高速發展,欣欣向榮」,四段故事包括自閉人士發揮藝術天賦、年輕人實現網上賣遊艇的創業夢、西方音樂與傳統粵劇crossover 創出新意及南亞裔年輕人努力練習舞獅而成功奪標。正能量爆燈,宣揚的仍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和「努力總有出頭天」的香港精神。
香港,一邊被噤聲,另一邊忙於爭奪話語權,重新定義香港故事。《七人樂隊》有幸成為時代見證,見證將來還可以說什麼。
【一眼關七】《七人樂隊》:勝在還有不跟大隊的徐克